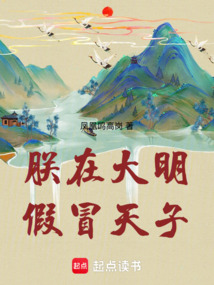
朕在大明假冒天子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穿越成了一個《明史》里沒有記載的小人物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六,深夜。
北京,英國公府。
朱漆銅釘大門前垂落的六丈素帛翻涌如浪,數百盞纏白麻素紗燈懸在廊廡下,被秋風吹成晃動的慘月。
青灰流蘇掃過蟠螭暗紋,將廊柱上猙獰的龍獸籠進飄忽的喪紗。
穿過三重垂花門,烏木靈床前赫然陳列著一方油杉朱漆棺,赤色如凝血,映得兩側六面云雷紋墻翣愈發森然,玄底金線的翣面上,夔龍在素帛間若隱若現。
三牲供品前的青銅仙鶴香爐歪斜著,鶴喙銜著的線香早已燃盡,青煙卻仍在空棺上方盤桓不散,恍若徘徊不去的幽魂。
一方牌位肅穆端踞于供案中央,赤金泥細細勾勒的柳葉篆體工整如列。
——“大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英國公張公諱輔之神位”。
橫如雕弓蓄勢,豎似寒劍出鞘,撇捺間猶見當年統帥三軍的風雷之勢。
香灰無聲飄落,在楠木紋理間織就銀絲蛛網,恍惚將自永樂至正統四朝的金戈鐵馬,都鎖進了這方寸之間。
-----------------
于謙端坐在紫檀螭紋官帽椅上,胸前的孔雀補子隨燭火明滅流轉華彩,三寸寬的金钑花革帶在腰間松松一束,緋色團領衫的廣袖垂落如赤霞疊云,與案頭半啟的塘報匣子投下的陰影糾纏成了不可名狀的凝重氛圍。
“姓名?”
一位青年伏在五步外的水磨磚上,粗麻斬衰裹著的身軀瑟瑟如秋蟬,他額角觸著青磚的涼意,聲若蚊吶地回道,“張祁,弓長張,是字旁的祁。”
“何年何月出生?”
穿堂風掠過松濤聲涌進正堂,燭火在問話人的袍角上投下細碎金斑,張祁看見自己的睫毛在磚面投下的顫影,“宣德元年八月。”
檐角鐵馬突然叮當作響,驚得長明燈爆出燈花,于謙的話尾在空中凝滯半息,目光掠過青年嶙峋的肩胛,“……真是巧了。”
他的嗓音陡然放輕,像雪粒子落進了滾燙的茶湯,“竟然正好是漢庶人謀逆的那當口兒。”
張祁默不作聲,他頭顱低垂,脊背微微彎曲,仿佛一朵被霜打蔫的殘花,隨時都會被這凜冽的秋風無情卷走。
燭影又是一跳,驚得塘報匣子上的螭紋銅鈕泛起冷光,于謙指尖凝在銅鈕上方三寸,接著盤問道,“你原就姓‘張’么?”
張祁用指節扣住水磨磚的縫隙,肩背在麻布下繃出褶皺,話音卻穩如古井,“奴才本是漢王府中的宮人所出,依照規矩,理應隨漢庶人姓‘朱’。”
“宣德元年漢庶人謀逆伏誅后,奴才被沒為官奴,發配到了英國公府,這才跟著國公爺改姓了‘張’。”
銅鈕突然被叩響,于謙傾下身,燭影在他眉弓處劈開陰晴不定的溝壑,“那你的生母如今人在何處?”
張祁小心翼翼地答道,“跑了,她生下奴才后就跑了。”
于謙聞言,眉頭驟然緊鎖,仿佛被一根無形的針刺中,手指無意識地在桌沿上輕輕一叩,下意識地重復道,“跑了?”
話音未落,他的身子陡然挺直,迅速掃向廳堂另一側同樣身披重孝的與張輗與張軏,目光如炬,“怎么跑的?什么時候跑的?”
英國公張輔生前膝下共有二子四女,四個女兒早已嫁為人婦,不在府中居住。
嫡長子張忠身患殘疾,常年纏綿病榻,庶長子張懋如今年僅八歲,還是個懵懂無知的孩童。
如今,張輔驟然離世,一應治喪事宜與英國公府的所有事務,便如同一座沉重的山岳,壓到了張輔的兩個弟弟——張輗與張軏的肩上。
張輗神色平靜,面上波瀾不驚,聞言只是輕輕抬了抬眼,語氣淡然道:“宣德元年九月,在發配的路上跑的。”
于謙眉梢微揚,追問道:“那英國公生前……”
張輗不待于謙問罷,便立刻接過話茬兒解釋道,“國公爺在世的時候就沒追究過這事兒,當年跟著漢庶人一起造反的可太多了,前前后后加起來可不止幾千人吶,要是再把武定州的軍民也算上,那得有十幾萬人。”
“按照《大明律》,凡謀逆者,于法全家男子當斬,婦女發配,好在先帝(指明宣宗朱瞻基)心善,不忍一概加刑,就只查辦了慫恿漢庶人造反的王斌、朱暄那幾個主犯,剩下的從犯和家屬都免了死罪——要么發配戍邊,要么被編入京衛匠籍,要么沒入功臣之家為奴。”
“誰曾想,到了半道兒上,那些被發配戍邊的罪人,竟然有不少設法害死了押送他們的衙役,跑了;那些被沒入功臣之家為奴的,也有許多想方設法地逃回了老家。”
“于是宣德二年的時候,先帝又下了一道旨,允許那些逃犯自己出來自首,但凡出來自首的,就免死罪,不過還得回原來的發配地,要是有窩藏逃犯的,查出來得一同治罪,要是有舉報逃犯的,則賞一千貫錢。”
“那一遭兒過后,零零總總地抓了有兩千多人戍邊,后來風頭過了,也就沒什么人再管這事兒了,再說了,一個年輕女人,真想藏起來可太容易了,隨便找個人改嫁,過幾年生了孩子,改名換姓,縱是錦衣衛也難再追索。”
燭火搖曳,光影斑駁,將座上三人的面容映照得時明時暗。
窗外夜色沉沉,秋風裹挾著枯葉,宛如千百只鬼手正在輕撫窗欞。
張輗穿著一身本色粗生麻布制成的齊衰服,腰系苴绖,頭纏孝帶,那孝帶從他的頭頂繞過,在腦后系結,帶尾垂在肩頭,正隨著他的話語緩緩晃動著。
他于正統十三年正月剛升任錦衣衛帶俸都指揮僉事,對追逃嫌犯方面的事倒是的確有話語權。
同款裝束的張軏跟著他二哥道,“我記得,先帝當年去武定州平息漢王之亂時,少司馬(兵部左侍郎的別稱)不但隨扈在側,還代先帝厲聲怒斥漢庶人數條謀逆之大罪,那叫一個言辭激烈,聲威凜然,直罵得漢庶人是伏地戰栗,連頭都不敢抬。”
他的聲音雖輕,卻字字清晰,語氣中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試探,“論起漢王府的舊事,少司馬理應比我們兄弟二人更清楚才是。”
于謙的目光探照燈似得在張輗和張軏之間來回掃了一掃,眼神銳利而深沉,仿佛要將兩人的心思徹底看穿,“漢庶人出降時,先帝當即便命我巡按江西,故而漢庶人出降后的事,我自是不知,不過漢庶人作亂時,你亦征討有功,你可曾記得……”
張軏搖了搖頭,斬釘截鐵地打斷道,“我只記得,當年漢庶人出降后,先帝便把漢庶人父子帶回了京師,連同整個漢王府一塊兒重新安置到了西安門內的逍遙城,吃穿用度仍跟從前一樣,沒怎么苛待他。”
“后來沒過多久,也不知是因著哪件事兒,漢庶人惹惱了先帝,先帝一怒之下,便將漢庶人烹殺于銅缸之內,漢庶人歿后,先漢王妃韋氏與漢庶人的幾個兒子也都跟著漢庶人去了。”
“漢王身死無嗣,就此除國,漢王府的舊宮人這才從逍遙城內被重新發配了出來,那時候亂糟糟的,大伙兒都忙著為漢庶人一家料理后事呢,誰還能注意一個小小王府宮人的去向?”
廳內一時陷入沉寂,昏黃的光影在墻壁上跳來跳去,將三人的影子拉得老長。
潮濕的氣息從磚縫中悄然滲出,絲絲縷縷地蔓延開來,寒意順著張祁的指尖緩緩爬升,直至浸透了他的指節。
昨夜穿越時的眩暈感仍殘留在顱骨深處,像是某種無形的枷鎖,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而更令他窒息的,則是涌入腦海的記憶。
明朝正統十四年,即公元1449年,北方蒙古瓦剌部大舉南下,鐵蹄踏破邊境,直逼中原腹地。
明英宗朱祁鎮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不顧群臣反對,執意御駕親征,命郕王朱祁鈺留守京師,監國理政。
同年八月十五日,明軍行至土木堡時,因遭遇瓦剌大軍突襲,潰不成軍,死傷慘重。
明英宗朱祁鎮被瓦剌俘虜,隨行的數十名文武大臣戰死,王振也在亂軍中被殺。
消息傳回京師,朝野震動,舉國嘩然,瓦剌大軍乘勝追擊,兵鋒直指北京,史稱“土木堡之變”。
而張祁便是在這一充滿血腥味的歷史轉折點上,從在圖書館里翻查《明史》的大學生,穿越成了英國公府中最卑微的家奴。
因宣德元年的漢王之亂,他靈魂所在的這具軀體成了被沒入功臣之家的賤籍罪人,不能科舉,不能經商,不能與良人通婚,世代為奴,不得更改。
在穿越之初,熟悉網文套路的張祁并沒有驚慌失措,他幾乎是本能地開始嘗試召喚系統、金手指、穿越大神,乃至所有他曾經在無數小說中讀到過的、能夠逆轉命運的外掛。
然而,無論他如何嘗試,回應他的只有一片死寂。
沒有冰冷的機械音提示他綁定系統,沒有神秘的老者聲音在耳邊低語,更沒有憑空出現的空間戒指或屬性面板。
這種緘默讓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無力感,那些在網文中被主角們輕易獲得的力量與機遇,換到了他身上卻變成了一場遙不可及的幻夢。
好在這種無力感并未持續太久。
就在他穿越的第二日深夜,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人物主動找上了門來。
那位在史書中力挽狂瀾、拯救大明于危難之間的鐵骨忠臣于謙,竟打著為英國公張輔吊唁的旗號,指名道姓地要見他。
于謙的名字,張祁再熟悉不過。
那是《明史》中濃墨重彩的一筆,是在“土木堡之變”后力主堅守京師、擊退瓦剌大軍的國之柱石。
可這樣一位位高權重、名垂青史的人物,為何會在這深更半夜之時,親自來找一個勛貴府中的家奴?
張祁思來想去,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清楚地記得,《明史》中并沒有“張祁”這個人物,甚至都沒有“于謙夤夜吊唁英國公”的記載。
英國公張輔以及張輔一家倒都是歷史名人,只是張輔的確是死在了土木堡,埋骨塞外,成為了那場慘敗的犧牲品之一。
他來得太晚,已然錯過了改寫張輔命運的最佳時機。
因此即便他來自現代,知曉大明的歷史走向,也不可能僅僅在穿越過來的一天之內,就打出“未卜先知”的響亮名號,更遑論驚動于謙這般人物。
顯然,于謙的出現,并非是因為他展現出了什么穿越者獨有的驚人才能,而是另有緣由。
那究竟是什么緣由呢?
張祁垂首的姿勢已維持半炷香光景,此刻只覺得后頸針刺般發麻,喉結在領口間滑動兩遭,終是抬起半寸下頜,緩解僵硬的脖頸。
視線自磚地蜿蜒而上,堪堪停在了于謙的腳尖兒前。
皂靴外罩的玄色皮札鞵上,犀皮軟底早已磨出了毛邊。
張祁的神經驟然緊繃。
這是洪武六年定下來的規矩,百官凡常朝視事,一律須穿公服禮靴。
然而彼時的大明尚未遷都北京,南京那地方又多雨,百官穿著釘靴上朝,腳步聲震得殿陛咚咚作響,十分得不成體統。
太祖皇帝朱元璋為了整頓朝堂秩序,便下令讓官員們自己準備一雙軟底皮鞋,上朝時套在靴子外面,待退朝后再脫下。
這樣一來,既保持了朝堂的肅靜,又顯得體面莊重。
如今于謙深夜來訪,連這靴子外面的軟底鞋都沒來得及換,必定是前腳剛出了紫禁城,后腳便急急忙忙地來英國公府了。
什么事能教他這樣急?
張祁擰眉思索了一刻,仍然沒想通其中關節。
在張祁所繼承的記憶里,他這具軀體的一生如同一卷泛黃的舊書,字跡模糊不清,內容平淡無奇。
每日的日常無非是晨起灑掃、端茶遞水、整理書案,偶爾在廊下聽候差遣,或是站在院中,望著天井上方那一處狹窄的天空發呆。
其余諸如吃喝拉撒、讀書寫字之類的凡俗小事,也是瑣碎得幾乎讓人提不起興致去細究。
他與張輔的交集更是少得可憐,記憶中僅有的幾次照面,也不過是遠遠地站在廊下,看著那位威嚴的英國公在眾人的簇擁下匆匆而過。
張輔的目光從未在他身上停留,那漠然的姿態,仿若他不過是府邸中數百名家奴里,一抹稀薄到近乎透明的影子,連名字都不值得記住。
這些記憶單調得近乎乏味,像一杯寡淡的溫開水,既無醇厚的滋味,也無刺喉的烈性。
沒有驚心動魄的瞬間,沒有刻骨銘心的經歷,甚至連一點兒值得回味紀念的片段都不曾留下。
-----------------
于謙仍然與張輗、張軏兄弟打著機鋒,若不是他腳上的軟底鞋早早地出賣了他內心的焦灼,一點兒都看不出來他實際上比誰都著急,“那這可真成了一段無頭公案了,當年扈從先帝征討漢庶人的舊臣——”
他屈指數道,“蹇忠定(蹇義)、楊文貞(楊士奇)、楊文敏(楊榮)、楊文定(楊溥)、夏忠靖(夏原吉)、吳榮襄(吳中)、張恭肅(張本)、顧端肅(顧佐),乃至陽武侯薛忠武(薛祿)、清平伯吳壯勇(吳成),皆已作古。”
“只剩我與大宗伯(指禮部尚書胡濙)尚在,今日我來之前,已去問過大宗伯此事,可巧了,大宗伯回我說,他也不記得當年漢王府中有這么一個宮人了,還反叫我來英國公府問問你們呢。”
“咚——咚!咚!”
三記梆子破開夜色。
更夫沙啞的“子時三刻,天干物燥——”裹著霜氣,在街巷間游蕩,仿佛從永樂年間的北平城頭飄來,帶著幾分肅殺與蒼涼。
尾音未散,鐘鼓樓上的銅壺滴漏聲驟然尖銳,滴答、滴答,仿佛每一滴水珠都在階前石磚上砸出火星,激得人心神不寧。
張輗眉頭微蹙,似乎在細細揣摩于謙每一句話的份量,張軏則微微側首,目光閃爍不定,似在權衡利弊,又似在揣測于謙的用意。
三人端坐如松,宛如三尊靜默的雕像,彼此對峙,卻又彼此試探。
報更聲罷,張輗開口道,“大宗伯乃是先帝托孤五大臣之一,德高望重,他說不記得,那必定不會是謊話。”
張軏附和道,“何況大宗伯如今已七十有四,正統九年時便已請求致仕,只是陛下念其勞苦功高,執意挽留至今。”
“這人一上了年紀,記性自然是不大好了,若說不記得宣德朝舊事,也是情理之中。”
張祁聽得云里霧里,耳邊的對話如一陣裹挾著沙塵的風,雖帶著幾分重量,卻抓不住半點實質。
他隱約覺得這三人在你來我往間似在博弈什么驚天大事,可細細回味,卻又如鏡中花、水中月,字字飄渺,句句虛幻。
方才那些言辭,恰似河上的浮萍,看似清晰可辨,卻一觸即散,徒留滿池漣漪。
正當他暗自疑惑時,忽聽得座上的于謙聲音一轉,語氣陡然凌厲,竟直直沖著自己而來:“既然你們都說不記得,我便親自來看看。”
話音落下,驟然一靜,連滴漏的聲響都仿佛停滯了一瞬。
緊接著,于謙倏地站起身來,袍袖帶起一陣微風,他往前邁了兩步,那雙毛了邊的軟底鞋便無聲無息地停在了張祁的鼻尖兒底下。
張祁低垂著頭,視線所及只有那雙軟底鞋的邊沿,他身子壓得太低,鞋面上細密的紋路如刀刻般清晰,每一道褶皺都仿佛在無聲地壓迫著他的神經。
“抬起頭來!”
一道不容置疑的威嚴聲音從他的頭頂上沉沉壓下,如同雷霆般震得他耳膜發顫。
張祁下意識地抬起頭,目光順著那雙軟底鞋往上移,掠過緋袍的下擺,越過腰間的玉帶,最終對上了于謙的眼睛。
于謙年已五十有一,鬢角微霜,眉宇間刻著歲月的溝壑,深淺交錯,似是記錄著無數風雨飄搖的日夜。
他面容清瘦,顴骨略高,鼻梁挺直如刀削,唇線緊抿,唇角微微下垂,仿佛常年壓抑著某種情緒。
那雙眼睛更是如同深不見底的寒潭,幽深而冷冽,仿佛能洞穿一切偽裝,直抵人心最深處的秘密,卻又帶著一絲難以言喻的疲憊。
張祁的心跳陡然加快,仿佛擂鼓般在胸腔內轟鳴,他的掌心微微滲出汗珠,濕冷黏膩,指尖不自覺地蜷縮起來。
他感覺自己正站在一座無形的懸崖邊緣,腳下是深不見底的黑暗,稍有不慎便會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張輗、張軏兄弟的目光如影隨形,亦跟著齊齊落在了張祁身上。
張祁努力穩住心神,試圖從于謙的目光中讀出些什么。
兩人對視半晌后,于謙的那雙眼睛依舊如同一潭深水,平靜得沒有一絲波瀾。
那平靜并非溫和,而是一種令人心悸的沉寂,像是暴風雨來臨前的海面一般暗藏洶涌。
燭火的光影在他眸中跳躍,卻映不出半分情緒,仿佛所有的喜怒哀樂都被那深不見底的幽暗吞噬殆盡。
銅壺滴漏突然墜下一顆碩大的水珠,“咚”地砸碎了廳中死寂。
于謙的嘆息聲恰在此時響起,低沉得像是從地底滲出的寒泉,“像!像!”
他前傾身軀,影子自動拉長成了一座山岳,重重壓在張祁肩頭,“太像了!”
張祁下意識地移開視線,喉結滾動間咽下一口腥甜的冷汗,后頸的涼意順著脊骨蜿蜒而下,仿佛有神魔的爪子正摩挲著他的命門。
張輗的聲音恰在此時切入,“少司馬覺得他有幾分像?”
“若觀之以形——”
于謙的視線一寸寸地刮過張祁臉上的每一根毫毛,自他眉間懸針紋起,掠過山根凹陷處,最后停在唇畔那道天生微翹的弧線上。
“起碼九分像。”
張軏似笑非笑地追問道,“那還有一分缺在哪里呢?”
于謙忽地伸出一只手,指尖如鐵鉗般挑起張祁下頜,力道大得在肌膚上掐出了一道淺淺的月牙痕,“形似神不似,缺的這一分,便是‘神形’。”
“不過神形兼備本就難得,他能長得與郕王殿下有九分相似,便已足堪大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