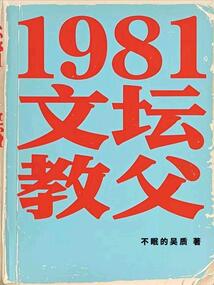
1981文壇教父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黃金時代
“呃……”
楊百川感覺腦殼像是被人拿棒槌狠敲了幾下,痛得要炸。
他使勁地眨了好幾下眼睛,才慢慢看清眼前的景象。
他躺在一間灰蒙蒙的土墻屋子里。
屋外大雨傾盆,打在瓦片上,噼啪亂響。
屋內四處漏風,房梁上掛著的苞谷串和老臘肉隨風晃蕩。
“你醒啦。”
說話的是個女人。她原本趴在床沿打瞌睡,這會兒直起腰來。
借著昏黃的煤油燈光,楊百川看清了她的容貌。
二十二三歲,大眼睛,塌鼻子,皮膚有點黑,臉上長著粉刺。穿了件泛白的藍布衫,領口磨得起了毛邊。兩條麻花辮垂在胸前。
楊百川抬手摸到額頭上纏著的紗布,手指頭剛碰著就火辣辣地疼:“我……這是怎么了?”
“你命大哦。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砸到了,還好被人發現得及時。”
但在楊百川的記憶里,他正伏在電腦桌前碼字,閃爍的電腦屏幕光刺過他酸澀的眼皮,耳邊回蕩著座鐘的響聲。
鐺、鐺、鐺……
然后他就什么也不記得了。
女人遞過一只缺了一角的瓷碗,碗身上印著偉人的側臉像,旁邊環繞著“東方紅太陽升”的字樣。
這碗也太復古了……
楊百川接過碗,手還有點抖。他喝了口水,感覺舒服了些,摸了摸自己的褲兜,什么都沒有。
“我手機,手機丟了。”
他感覺喉嚨像被刀片割過,生疼又漏風。
“什么手機?”女人滿臉困惑,仿佛從沒聽過這個詞,“只聽說過公雞母雞,什么是手機?”
楊百川猛地起身,竹板床吱呀響了一聲。他感到腦袋一陣暈眩,連忙扶住額頭。
閉眼前的最后一束目光,落到掛在門邊的日歷上。
1981年7月5日,辛酉年甲午月癸未日。
記憶如老舊的放映機開始運轉,暴雨中的閃電、積水的鄉間小道、掉鏈子的永久牌自行車,畫面一幀幀在他腦海里閃過。
穿越這種小說里的情節,竟真的發生了……
原身的所有記憶,也在這一刻悄然融入他的意識。
楊百川,男,臨江縣城關鎮人,生于1956年臘月間,屬猴。
父母均為臨江縣酒廠職工。
楊百川中專讀的釀造專業,畢業后,順理成章進了縣屬酒廠,卻因父親脾氣乖戾,好得罪人,被連累發配去當了酒曲采購員。
說是采購員,其實就是蹬著輛銹跡斑斑的永久牌二八大杠,到鄉下收購糧食。
這趟往柏林壩去,半道卻撞上了偏東雨。
楊百川本想頂著風雨,一口氣騎到大隊上,卻遭遇山上飛石,擊中了額頭,一命嗚呼。
眼前這女人只當他命大活了下來,哪里知道如今這副軀殼里,早已換了個來自四十年后的靈魂。
“同志,莫亂動!”
這聲“同志”使他內心微動。
二十一世紀的楊百川從雙非理工大學的中文系畢業,正趕上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年月。
他擠破頭才找到個月薪2500的工作,吃盡了福報,夜里偷摸寫網文補貼家用。
可寫網文哪有那么容易,他接連寫了三四部,全都撲街,最終決定三開,竟猝死在熬夜碼字之時。
在那個時代,滿大街都是兄弟、老鄉、朋友、老師,可再沒人喊一聲“同志”。
人們都在為生活步履匆匆,將生命耗費在生產剩余價值上。好不容易下了班,擠著沙丁魚罐頭一樣的公共交通,縮回狹窄的出租屋里。就在這日復一日中磨掉了共同的志向。
楊百川聽話地躺了下來,聞到枕邊飄來一股香風。他不知道那是屬于那個年代的雪花膏。
這時他才發覺,女人說的是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
在這個年代的渝西地區,農村里說普通話的人,大概只有知青吧。
在楊百川這個00后的印象里,知青應該是挽著褲腿挑糞的土氣模樣,可面前這女子有一種樸素的美感。
楊百川瞇眼望向四周,瞥見墻角的五斗櫥上有一個鐵皮醫藥箱,中間畫著一個紅漆斑駁的十字,心下了然:這女知青大概是個醫生。村民發現了昏厥的楊百川,把他帶給女人治療。
又一段記憶忽然涌來……原身一年前來這柏林壩收酒曲,曾在村口見過這個女知青。
那天日頭毒得很,原身滿臉油汗,騎車駛進村子,掠過路邊步行的女知青。
村口鬧哄哄的。黃桷樹下,幾個婦女縮在樹蔭里納鞋底。穿紅牡丹汗衫的那個突然撂下錐子:“破鞋來咯!”
另一個婦女象征性地拿鞋底去打她的同伴:“你小聲點!吼恁個(這么)大聲,生怕別個聽不到?”
“都敢做,還怕人說!”
女知青斜挎著醫藥箱,滿臉通紅地走過去,狠狠地瞪了幾個婆娘一眼,扯身走了。
她走出去幾步,一個胖婆娘突然躥起來,對著天講:“瞪啥子瞪,想打架嗎?!”
那時楊百川沒太看清女人的臉,只記得那雙薄薄的耳朵在太陽底下像透明的樹葉。
后來他又來了幾次柏林壩,閑話像麥芒似的往耳朵里鉆。
“就她龜兒妖不到臺(了不起),說普通話,裝城頭人!”
“這就叫做,南瓜把把(南瓜柄)裝大腦殼章(紅色的印章)!”
“你懂個鏟鏟!不扭起個勾子說話,怎么哄得到那些男的嘛……”
……
這些使他想到王小波的《黃金時代》。
他知道鄉下婆娘最愛扯這些閑篇。特別是到了八十年代,生產隊越來越松散,瀕臨解散,人們聚在一起說閑話的時間就多了起來。
楊百川知道,關于女人的事實不是這樣的。
“您貴姓?”他也用一口純正的普通話問女人。
女人一怔。她來臨江插隊后,大概除了別的知青,就沒聽誰說過普通話了:“姓陳,陳秀芳,秀麗的秀,芬芳的芳。”
聽到“陳”字的時候,楊百川心里咯噔了一下,但隨后出口的兩個字又讓他失望。在鄉下隨便拎出一個婦女,都可能叫這個名字。
怎么就不是陳清揚呢?
他突然想到,王小波此時還在人大念書,發表《黃金時代》是十年后的事。
在王小波的腦海里,“陳清揚”也許還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而在楊百川這里,她早已是一個血肉飽滿的女人。
他心里閃過一個念頭:要是我先一步寫出《黃金時代》,“中國的卡夫卡”豈不就成我了……
即便夠不上卡夫卡的高度,在文壇謀個立足之地,當個三流作家也未嘗不可。
想當年,他也是個懷揣著作家夢的文青。
大學那陣他嘗試寫過幾篇“純”文學小說,投給幾個雜志,都石沉大海。在小藍書、豆花逛了幾圈,看到有人罵文伐什么的,也跟著罵了幾句。那些稿子就一直躺在電腦的新建文件夾里吃灰。
但這是1981年啊,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徹神州大地,春來潮涌,萬物競發。
文壇不像四十年后那般死水一潭,而是一條化凍的春江,浪頭一個攆一個。
文學雜志相繼復刊,也有新的雜志紛紛涌現。
大佬也沒那么多。健在的像曹禺、巴金,都年事已高,日后稱雄文壇的如余華、莫言,都還沒成名。
此時的文壇就像是一片無人管轄的區域,想象力如野草般肆意生長。
新人作者有著廣闊的天地,可以大有作為!
腦子突然一嗡,又涌來了一段記憶。
原來原身也是個文學青年,出事前不久才給酒廠的廠報投了一篇小說。
那是個新華書店門口大排長龍的年代,滿大街都是文學青年。
他向陳秀芳說了自己名字,轉頭看見床頭柜上壘著幾摞書。
有《吶喊》《安娜卡列尼娜》《罪與罰》等中外名著,也有像《收獲》《紅巖》這類國內文學雜志。
他隨手抽了一本《收獲》,竟是1979年第1期。
《收獲》復刊號,這在四十年后的孟夫子舊書網上,怕是能賣個一千塊錢。
“同志,你也喜歡文學嗎?”
陳秀芳這句話愣生生的,像吃了一顆青胡豆。這個年代的人,樸實得讓人不習慣。
“喜歡,也寫過些。”
他的腦海里忽地晃過個印著酒廠徽章的筆記本,封面上歪歪扭扭寫著《遙遠的海島》。
這就是原身投給廠報社的那篇小說,講的是四九年我軍打舟山群島果軍殘部的故事。
這是十七年文學的老路子。看來原身這小子還沒跟上時代潮流。
楊百川是中文系出身的,對此時文壇的風向了如指掌。
隨著1977年劉心武《班主任》、1978年盧新華《傷痕》的發表,中國文學進入了傷痕文學的階段,時興的是揭露前十年給人們帶來的心靈創傷。
在后世看來傷痕文學有點哭哭啼啼的意味。
80年代初,傷痕文學又演變為反思文學,不再停留于揭露表面的創傷,而試圖深入歷史,探尋造成前十年路線的歷史淵源,代表作有高曉聲的《李順大造屋》、茹志娟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等。
改革、尋根、先鋒、現代派、新歷史主義、新寫實主義……
這些大學背過的名詞解釋,在他心里成了一張藏寶圖。
他完全可以緊扣時代的文**流,闖出自己的一片文學天地。
而且比起倒騰商品、走深圳闖碼頭的營生,這條路穩當得多,不用沾染黑白兩道,只消一頭扎進紙堆里。
他翻開雜志,動作不疾不徐,陳秀芳瞧不出他眼底暗涌的盤算。
這時代,終會有我楊百川的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