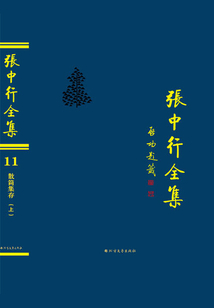
散簡集存(上)(張中行全集)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自序
編印這樣一本雜燴菜式的書,更應該自己在書前寫幾句,告訴肯翻翻的讀者,為什么要來一本雜燴,以及這個雜燴菜是如何配料、如何出鍋的。起因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愿意,我隨著愿意,從把我的已災梨棗的作品合印一次,成為“作品集”。不稱“全集”,推想原因之主要者是他們想,閻王老爺還沒來請,書呆子更是舊習難改,我還會拿筆;我還可以加個次要的,是早年所寫,幾乎都已灰飛煙滅,僅存的一點點,如《非主謂句》《緊縮句》之類,一般讀者必不看,也就不應該再浪費紙張。總之,這只是“作品”而不是“全”。但就說是不求全吧,有些分明是作品,而且,至少主觀愿望是一般讀者(或一些讀者)也會有興趣看看的,前幾卷里沒收,缺者應補之,所以作為尾聲,就編印這樣一本。
所收之作,由時間的角度看可以分為兩大類,新近寫的和舊日寫的。新近,時間的上限大致是1995年年底,換句話說,是1995年之后所作的零篇,還沒編入前幾卷所收的本本里的。也要定個下限,理由仍是由閻王老爺那里來,活著就難免拿筆,編為集,總不能一再等尚是未知數的明天。下限定為1997年的上半年,所以除了這篇序文是例外,1997年6月30日以后成篇的就不收了。輯上限、下限間的零篇,共得將近百篇,刪去少數認為可有可無的,都收了。入集,要給個位置,依“新人從‘門’入”的舊例,排在前面。“前”之中也要有個次序,大致是以文的內容為歸類標準,這樣排列:議論,雜感,談人,談地,談雜事,談私情,散文,談書。
再說舊日寫的。這舊也只是舊到八十年代初,只有《關于‘給’的詞性》(1960年)和《單句復句的劃界問題》(1957年)是例外。這兩篇,以及《言意的親疏種種》,所以收,理由有私的,是費力較多,難免有珍惜之情;有公的,是可以供關心語言問題的人參考。然后說大多數,也可以分作兩類,選文的導讀和講讀文言的知識介紹。兩類的寫作因緣不同,大致說,前者是應書、刊、電臺之約,自留地的產物;后者是七十年代末回出版社,參加編輯文言讀物的工作,在生產隊早出晚歸的產物。決定收,理由仍是:私,自信費力不小;公,比如說,學文,尤其文言,看看,比自己摸索也許能省些力。兩類的編排,用的是戲劇演出排戲碼的原則,先輕后重。大軸的一篇尤其重,今日回顧,收文大大小小整整三百篇(有的幾篇合為一題),由海里撈針的選用到解說的評介,時間斷斷續續用了三四年,古詩說“生年不滿百”,想到不少血汗,借這本雜燴之光可以不與草木同腐,心里真是有點既高興又感傷。
順著感傷再說幾句。這本雜燴的書編成,心也有所想,是“完了”兩個字。字兩個,涵義卻不簡單。一種是這本書完了,另一種是這八卷的作品集完了。還有一種,情況不如此清清楚楚,是拿筆的精力是否也隨著完了?有些寬厚的讀者希望我還能繼續寫,這使我既感激又振奮,可是就是在頗想吟誦“老驥伏櫪”之時,已故的世五大哥常說的“人不服老不成”的聲音又在耳邊響起來。今后我還能寫點什么嗎?未然者不可知,也就只能從孔老夫子之后,“畏天命”了。
1997年10月11日于京華之留夢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