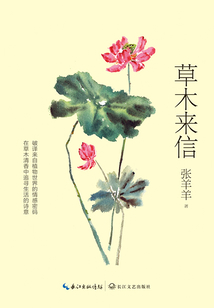
草木來信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自序
伯勞,烏桕,采蓮,飛鴻……南朝樂府《西洲曲》越讀越美。一頁即可翻過許多往事。“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好一個“吹夢”。
一直有個夢,給故鄉寫一本書,寫那些草木,仿佛故鄉美麗大眼睛上的睫毛。快十年了,才寫了這樣薄薄的一本。正如我在一篇短文里寫孩子在妻子肚子里快兩個月,到寫完時孩子已經出生了快十個月。
其實,我挺討厭別人說,一本書寫了多少多少年,說得有點嘔心瀝血。十年前,我寫了第一篇植物《葵花》,人呢有點懶散,十年下來慢慢積攢了五六十篇文字。一直打算結集出版,可總覺得還有什么沒寫到,似乎對不住它。寫完《苦楝》,覺得《木槿》也要寫寫,所以在寫完《蘿卜》以后,我就暫停了。
這十年里,寫植物的人越來越多,書也一本一本地出來,其中還有好幾個我熟識的朋友。有的只寫兩三個月就夠了,有的寫了半年。我的節奏,似乎與對故鄉的愛不成正比,我也猶豫過,我的這一本是不是有點多余。有段時間里,我甚至不敢提及“草木”兩個字,像不敢提起“村莊”一樣,我怕別人會厭煩。
想起《詩經》里第一個出場的植物:荇菜,多少年來人們還在反復書寫,我就安慰自己,我所寫下的草木有我個人的符號,我寫它們時充滿了感情,所以應該讓它們住在我的“庭院”里,美好地生活下去。
每一種草木,會讓我想起媽媽的面容。誠如我在《蒲公英》的結尾里寫下的“蒲公英飄絮的時候,我就想起了祖先,毛茸茸的祖先”。因為年齡、心境的緣故,我對文字的表述有了明顯的變化。但十年對草木的書寫,它們讓我學會了更加誠實。
有時候我覺得不是我在寫它們,是它們在一一給我寫信。這樣的一本書,裝滿了我溫情的記憶,我還有一個美好的心愿,我的孩子和他的小伙伴們可以去多認識一種植物,那意味著多了一個好朋友,從草木那里,我們可以辨識媽媽永恒的面容。
讓—瑪麗·佩爾特在《植物之美》里說,“生命的形式多種多樣,沒有它們,人類的生命也不會有什么前途”,我特別喜歡這句話。
寫完《蘿卜》以為可以定稿了,一年后又寫了篇《蘑菇》。就像二〇一六年冬至日寫好的序,直到二〇二〇年立夏時節加上了這最后一段。
二〇二〇年立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