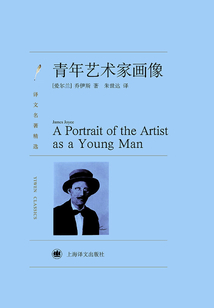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藝術家的心靈歷程——譯者序(1)
愛爾蘭著名作家詹姆斯·喬伊斯1904年在都柏林開始創作長篇小說《青年藝術家畫像》,1914年完稿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歷時10年。他于1904年1月7日,在他母親逝世之后4個月起意寫一個自我畫像。在都柏林剛籌建的雜志《達那》編輯們的慫恿之下,他在妹妹梅布爾的筆記本里急就了一篇敘述性的散文,題為《藝術家畫像》。在這篇散文作品中,喬伊斯采用了他原先寫成的所謂的“穎悟性速寫”(epiphany),大致勾勒了一個故事,并聲言要在散文中用“流動的現在時”表述過去,以充分體現“情感的跌宕”。
他將書稿寄給《達那》雜志,遭拒絕。不久,他便開始重寫一部自然主義的長篇小說,題為《斯蒂芬英雄》。喬伊斯是在1904年2月2日22歲生日那天開始寫作《斯蒂芬英雄》的。他想以此向《達那》雜志編輯們表明,“在描寫我自己的作品中,我有一個比他們漫無目的的討論更有興趣的題材”。他對弟弟斯坦尼斯拉斯·喬伊斯說,這部小說將是自傳性的,諷喻性的。在小說中,喬伊斯描寫了許多熟識的朋友和天主教耶穌會修士。書名《斯蒂芬英雄》本身就含有諷刺的意義。1904年4月,他完成了11章,一年多以后,他寫到25章時(差不多是他計劃創作的一半),感到文思枯竭,轉而寫作《都柏林人》和準備《室內音樂》的出版事宜。現在在哈佛大學圖書館保存的手稿始于16章中間部分而在第26章中間部分戛然中止。在《斯蒂芬英雄》中,喬伊斯對他的技巧“穎悟性速寫”作了一個界定,認為它是一種“無論是在語言或是在手勢的粗俗性中還是在心靈本身一個值得銘記的閃念中突發性的精神的表現”。文藝評論家西奧多·斯潘塞認為,與其說喬伊斯的穎悟性的速寫,是戲劇性的,還不如說是抒情性的,這與作品主人公關于文學形式的觀點是一致的。哈佛大學教授哈利·萊文認為,喬伊斯運用令人頭暈目眩的轉換場景和思維的流動的手法實質上是試圖創造一種宗教式啟示的替代物。
1904年,喬伊斯出國遠游巴黎、蘇黎世和的里雅斯特等地。在這期間,他將《斯蒂芬英雄》改寫為《青年藝術家畫像》,在《青年藝術家畫像》中保留了許多前者的人物和事件。《青年藝術家畫像》自1914年2月至1915年9月在倫敦《利己主義者》雜志上連載,1916年在紐約首次出版。
意象派詩歌創始人埃茲拉·龐德在1915年9月讀了《青年藝術家畫像》之后給詹姆斯·喬伊斯寫信說:“我認為這本書與福樓拜、司湯達的作品一樣具有一種永恒的價值。”他認為,喬伊斯的文體清澈而簡約,沒有堆砌無用的詞匯和句子。在另一篇發表在《利己主義者》雜志1917年2月號的文章中,他指出,喬伊斯的小說將永遠成為英語文學的一部分。他說,他不可能就喬伊斯和任何英國或愛爾蘭作家做一比較,因為他與其他的英國或愛爾蘭作家太不同了。
雖然H·G·威爾士并不贊同喬伊斯在小說創作中的試驗,但他還是認為《青年藝術家畫像》將與《格列佛游記》一樣成為文學的一大成就。他說,和世界上其他最好的文學作品一樣,這是一部教育的小說;它是迄今為止所有作品中最生動、最令人信服地描述了愛爾蘭天主教家庭孩子成長的故事。
一
喬伊斯在《青年藝術家畫像》扉頁引用了古羅馬詩人奧維德《變形記》里的話:Etignotas animum dimittit in artes(用心靈以使藝術黯然失色)。在這里,喬伊斯試圖用新柏拉圖主義的理念,創造一顆超越藝術的藝術家靈魂。青年藝術家斯蒂芬·德達羅斯采用了希臘發明之神德達羅斯的名字。斯蒂芬在成長的青春歲月與愛爾蘭祖國、家庭、天主教傳統始終處于格格不入的境地。德達羅斯的兒子伊卡洛斯乘上他父親發明的一對翅膀,因飛離太陽太近而墜落。這是斯蒂芬生來就要為之服務的目的的一種預言,這是藝術家在他的工作室里用大地的沒有生命的東西制造出一個新的生命的象征。他的飛翔是他的起點,終以墜落而告終。斯蒂芬終因“不想再侍候上帝”而走上自我流放的道路。他決心沖出民族、語言、宗教的牢籠。小說本身賦有一種戲劇性的悲劇色彩。希臘神德達羅斯之所以想全心致力于藝術,根據奧維德的解釋,他是希冀躲開大地和海洋的統治者,是因為:
…longumque perosus
exsilium,tractusque soli natalis amore…
(在太漫長的流放中
德達羅斯思念故土。)
藝術家的自我流放和對精神家園的思念更增加了這種喬伊斯式的悲劇效果。喬伊斯式的悲劇風格每每讓人想起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為生與死所困擾,而斯蒂芬則在嚴峻的天主教教規與世俗的享樂和藝術之間猶豫不決。他最終發出:
老父,你這老巧匠,給我以幫助吧。
這一吁請讓人想起十字架上的耶穌的呼吁:“父啊,你為什么這般遺棄我!”
伊卡洛斯的墜落(fall)在《青年藝術家畫像》中幾乎具有一種預言的威力。fall既預示亞當夏娃的墜落,又預示不想再侍候上帝的早晨之星路濟弗爾墮落成撒旦——天使的墮落;既預示伊卡洛斯的墮落,又預言斯蒂芬的墮落和對天主教的反叛,又預言雪萊的“形單影只,成年漂泊”和納什的“光明從空中墜落”。“星星隕滅了,細膩的星塵塵埃在宇宙間掉墜下來。”這《舊約·以賽亞書》中的fall的形象貫穿在《青年藝術家畫像》之中。
另一貫穿整部小說的形象便是metamorphoses(變形)。從斯蒂芬到伊卡洛斯,從路濟弗爾到撒旦,從象牙塔到E—C到海鳥姑娘,從E—C到貧民區妓女的變形,其主調都是墮落。
喬伊斯在fall和metamorphoses之間描寫了一個從小經受天主教傳統教育、在冷峻的天主教耶穌會修士們布道中成長起來的青年的心靈歷程。《青年藝術家畫像》是一部藝術小說(Kunstlerroman),又是一部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它和福樓拜的《情感教育》、勃特勒的《眾生之路》、吉辛的《新格魯勃街》、托馬斯·哈代的《心愛的》、德萊塞的《天才》、諾里斯的《范多弗與獸性》、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習時代》、司湯達的《亨利·勃呂拉傳》一樣,是描寫青年、描寫藝術家成長的小說。在小說中,多愁善感的、內向的、以個人為中心的藝術家是主角,是堂吉訶德式的英雄。藝術家青春時期的憂郁、感傷、困惑和感悟便是小說的主題。斯蒂芬關注的是純美學和阿奎那的論述。他的心靈在與都柏林社會、天主教、式微的家庭的沖突中成熟起來。可以這么說,這部關于藝術家成長故事的藝術小說就是一部描述宗教與世俗、自我抑制與激情、肉欲與理智、藝術與生活沖突的作品。喬伊斯在這部小說中描寫的不是“一位藝術家”,而是帶有定冠詞的“藝術家”,正如W·Y·廷德爾所指出的,這表明喬伊斯描寫的是一個特別的、也許含有諷刺含義的一類人的畫像。這個藝術家就是斯蒂芬英雄類的人,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一個人。斯蒂芬意味著殉道者、巧匠、流放者、希伯來、基督教、希臘和傲慢的罪人。
二
無論斯蒂芬在家時,還是在克朗哥斯公學、貝爾維迪爾公學或在都柏林大學學院,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時而明確時而朦朧地尋覓真正的自我,尋覓自己的歸屬。斯蒂芬摒棄了污穢的、愚蠢的、爾虞我詐的環境,飛越出式微的家庭、虛榮的父親、呆板信教的母親、“吞食自己生養的小豬的”民族、嚴峻的冷漠的天主教教會的網去尋找自我的。斯蒂芬懷疑自己與父母、兄弟姐妹的關系是一種神秘的領養的關系,而不是一種血緣的關系,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兄弟姐妹的確切數字。
他是一個學究式的、自戀的唯我主義者,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叛逆者。他與都柏林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有一種彌漫整個身心的孤獨感。孤獨感正是敏感的藝術家的顯著特征之一。喬伊斯在小說開首就寫道:
從前,在一個很美妙的時刻,有一頭哞哞母牛在路上踽踽而行,這頭哞哞母牛在路上彳亍而行時遇見了一個名叫小杜鵑的可愛的孩子。
斯蒂芬一降生就生活在異類的環境里。小杜鵑這稱呼,對斯蒂芬來說是再適合不過的了。雌杜鵑每每將蛋下在別類鳥的巢里。這注定了斯蒂芬作為藝術家的孤獨的人生。
斯蒂芬在克朗哥斯公學遭受教導主任多蘭神父的鞭笞是藝術家的自我第一次與權威發生了沖突。他打碎了眼鏡,阿納爾神父允許他可以不用讀書,而多蘭神父卻誣蔑他為“懶惰的小騙子”。這是不公正而殘酷的。藝術家要去跟院長說,他被錯誤地體罰了。他想,像這樣告發冤枉的事在歷史上有人干過,那是偉人。他于是飯后散步時不是踅向走廊,而是爬上右邊通向城堡的樓梯,鼓足了勇氣去找教區長。于是,藝術家成了偉人,成了喬伊斯式的孤獨的英雄。他認為,他的命運是要躲避任何社會性的或宗教性的派別。他注定要與眾不同地領會他自己的智慧,或者在世界的各種陷阱中周旋,自己來領會別人的智慧。
甚至當他16歲躺在妓女的懷中,他仍然是孤傲的,緊緊抓住他的自我不放。在喬伊斯的自然主義的描述中給人一種疏離感,在男女的接觸中似乎有一種巨大的不可逾越的藩籬橫亙在他們之間。
他默默地呆立在房間中央,她走上前來快活地正經八百地一把抱住他。她那滾圓的手臂將他摟在懷里,他一見她的正經而嫻靜的臉龐貼向他,一感受到她溫熱的乳房平靜地在身上摩挲,他遽然歇斯底里地啜泣起來。愉悅和釋然的眼淚在他的快樂的眼睛里閃爍,他張開了嘴唇,但并不想說話。
她用她那玎玲當啷的手撫摸他的頭發,叫他小無賴。
吻我,她說。
他不愿躬身去吻她。他只想緊緊地偎在她的懷中,被輕輕地、輕輕地、輕輕地撫摩。在她的懷抱之中他突然變得強大、無畏而充滿自信。但他不愿躬下身子去吻她。
她霍地一伸手將他的頭壓下來,她的嘴唇與他的嘴唇緊緊貼在了一起,從她那畢露的抬起的眼睛里他穎悟到她所有動作的含意。這對于他太過分了。
桀驁不馴的藝術家孤獨的自我的另一面就是異端。他所信奉的思想與世俗迥異。他崇尚的是浪漫主義詩人拜倫,認為丁尼生只是一位韻律家,而最偉大的詩人是拜倫。但在都柏林庸俗的“有教養的”中產階級看來,拜倫純粹是個異端,“一個不道德的人”。斯蒂芬第一次因為堅信自己的異端思想而挨了一頓揍。即使斯蒂芬雙手被反綁在身后,同學從溝里操起一根長長的白菜幫子扔在他身上,用手杖猛揍他的腿,赫倫嚴詞要求他承認拜倫不好,藝術家仍然是一個斷然的“不”。
由于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斯蒂芬在同學的眼中無異是一個“魔鬼”。同學達文對斯蒂芬說:“你真是一個可怕的人,總是孤獨一個人。你完全脫離了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你是一個生來就對一切冷嘲熱諷的人。”但藝術家卻認為,“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這人生創造了我,我只是說出了一個真實的我而已。”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斯蒂芬作為藝術家的最后歸屬是由一位無知的教導主任肯定的。
教導主任問:“你是一位藝術家,是嗎,德達羅斯先生?藝術家的目標就是創造美。”
斯蒂芬說:“只要視覺能理解它——我是指美學理解——那它就是美的。”
斯蒂芬對同樣無知的同學林奇闡述美與藝術時,藝術家的自我達到最高峰,一個完整的新柏拉圖主義、阿奎那思想的信徒便塑造完成了。斯蒂芬認為:
“藝術是人為了審美目的對可覺察的或可理解的事物的處置。根據阿奎那,對令人愉悅的東西的穎悟就是美。美需要三樣特性:完整性、和諧和光彩。……”
關于藝術形式,他認為:
“你會發現藝術分為三種形式:抒情形式,在這種形式中,藝術家以與自己最直接的關系來創造形象;史詩形式,在這種形式中,藝術家以與自己和其他人間接的關系來創造形象;戲劇形式,在這種形式中,藝術家以與其他人最直接的關系來創造形象。”
喬伊斯有意安排藝術家在闡釋自己關于美與藝術的觀點時,他的聽者是無知之徒,這使藝術家英雄的孤獨感達到了極致。于是,在我們面前呈現出一個完整的作為異端分子、作為英雄、作為流放者的英雄的藝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