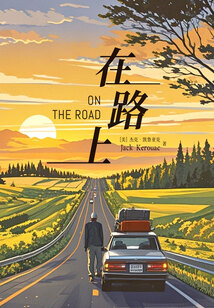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第一次遇見迪恩的時候,我與妻子才分手不久,剛剛大病初愈,我只能說這場病確實跟那令人不勝疲憊的離婚有關,而且,我對當時的一切都心灰意冷。隨著迪恩·莫里亞蒂一起到來的,還有我生命中“在路上”的那部分。在那之前,我曾經幻想過多次去西部看看,然而也就是隨便含糊地計劃一下,從沒有啟程過。而迪恩這家伙可以說是此出行計劃中最完美的伙伴,因為他其實上就是出生在路上的。那會兒是1926年,他父母正開著一輛破車,途經鹽湖城前往洛杉磯去。最初我是從查德·金那兒知道他的,查德帶給我幾封來自新墨西哥少年管教所的信,寫信人正是迪恩。我隨即對那些信件產生了相當的興趣,因為他在信里要查德把關于尼采的一切,以及查德所知道的所有奇妙的事都講給他,態度天真而誠懇。我曾經跟卡羅聊起這幾封信,還想著將來有沒有機會見見這位奇怪的迪恩·莫里亞蒂。這些事都已經是舊談,而迪恩早已今非昔比,那時的他還只是神秘重重的小勞改犯。然后,忽然某一天就傳來一個消息,說迪恩離開了少管所,打算第一次來紐約了;當然還有一個消息,是他與一位叫瑪麗露的姑娘結了婚。
一天,我正在校園晃蕩,查德和蒂姆·格雷找到我,說迪恩現正待在東哈萊姆區一個沒有熱水的舊公寓里,那里也還有他那位漂亮生動的小妞,兩人搭乘灰狗長途巴士,在第五十大街下了車,想在街角隨便找個地方吃飯,就拐進了赫克托。從那以后,赫克托咖啡館就成了迪恩心中紐約的地標。兩人在那里消費了不少光鮮滑嫩的蛋糕和奶油泡芙。
剛開始的那段時間,迪恩總是對瑪麗露說:“親愛的,我們現在終于到紐約了。盡管我們過密蘇里河的時候我沒把我的想法全都告訴你,尤其是經過波恩維亞勞改所的時候我想起了我的牢獄生涯,但我覺得現在我們非常有必要把余下的那些個人愛好全部放到一邊,立刻開始計劃具體的工作生涯……”總之,他早期的說法都是類似如此。
我們一伙人去了迪恩住的那個沒有熱水的公寓,他穿著短褲來開門,瑪麗露正從長沙發跳起身來;接著,迪恩打發公寓的主人去廚房了,也許是讓她煮咖啡,他則繼續談論他的愛情問題。因為在他看來,生活中唯一神圣的頭等大事只有性,盡管為了生存他不得不罵罵咧咧地打工。他就站在那里,目光朝著地面,飛快地晃著腦袋,點點頭,就像一個年輕拳擊手聆聽教官的指示一般,讓你感覺他是在用心諦聽每一個字,并千萬遍回應道“是,是,是”或“明白,明白”。迪恩給我的最初印象,是年輕時的吉恩·奧特里——瘦長,一雙眼睛碧藍,一口地道的俄克拉荷馬方言,蓄著大鬢角,活脫脫一個來自西部雪國的漢子。事實上,他之前一直在科羅拉多州的艾德·華爾農場里干活,直到同瑪麗露結婚,之后一起來到東部。瑪麗露十分漂亮,一頭長長的金色卷發披在肩上,就像是驚濤駭浪的金色海洋。她坐在長沙發的邊沿,兩只手垂放在腿上,一雙迷蒙的藍眼睛帶著鄉野氣息,不安地注視著周圍的一切,因為她正待在一個早在西部時就有所耳聞的地方,這樣一座黑暗又充斥著罪惡的紐約破舊公寓。此時的她仿佛是莫迪里阿尼筆下,一位頎長而消瘦的超現實主義女子,正等待在不妙的房間里。盡管瑪麗露外表看起來漂亮又可愛,其實她真的笨透了,能做出一些駭人的事情。那個夜晚,我們喝啤酒、扳腕子、侃大山,一直到天亮。早晨,我們圍坐在昏暗的晨光里默默地抽著煙蒂,那種從煙灰缸揀出稍長一點的。迪恩突然緊張地站起來,來回地踱步,一邊認真地思考著,接著打算讓瑪麗露準備早餐,打掃地板。“就是說,我們必須得腳踏實地,親愛的,不然我們就是舉棋不定,弄得我們的計劃既沒有真憑實據也不明確。”然后,我便離開了。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他對查德·金說,一定要跟查德學習寫作;查德讓他來問問我的意見,說我是作家。在這段時間里,迪恩找到一份露天停車場的工作,并且與瑪麗露住到了哈波肯公寓里——鬼曉得他們怎么會去那里住!他倆大吵了一架,瑪麗露完全氣瘋了,竟然想到要報復他,所以她歇斯底里地跑到警察局,編造了一些莫名的罪行指控迪恩,最終迪恩不得不從哈波肯公寓倉皇出走,無處可去,于是直接跑來了新澤西州的帕特遜,那是我和姨媽的住處。那晚,我正在看書,忽然聽到一陣敲門聲,來人正是迪恩。他弓著腰站在漆黑的樓廳里,臉上堆著笑,跟我打招呼說:“嗨,你還想得起我——迪恩·莫里亞蒂嗎?我來這兒是想請教你怎么寫東西。”“瑪麗露呢?”我問他,“那個婊子!”按照迪恩的說法,她顯然是當婊子搞了點錢回丹佛了。我帶他去外面喝了點啤酒,因為我們無法在家里暢所欲言——我姨媽正在客廳看報,她只瞟了一眼迪恩,就斷定他是個瘋子。
到了酒吧,我對迪恩說:“喂,伙計,我對你來找我的真實意圖非常清楚,你并不是想成為一名作家才來投奔我,你也別拿出吸安非他命的勁兒來同我爭辯。”他說:“是啊,你說得對,我當然明白你的意思,事實上這些問題發生在我身上,而我現在需要領會這些因素,從叔本華的主客二分哲學出發,弄清這些事物的本質……”。他對這樣的話題總是沒完沒了,而他所說的我完全聽不懂,估計他本人也不怎么清楚。那段時間里,他實在不清楚自己在說些什么,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年少的囚徒,一心沉浸于成為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的美妙可能之中。他喜歡運用那些從“真正的知識分子”那里聽來的語調和某些詞語,卻搞得混亂不堪。不過要知道,他在其他事情上并不會如此幼稚。后來他跟卡洛·馬克斯一起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便弄懂了所有專業術語,成了行家。盡管如此,我們在一些瘋狂的層面卻能夠默契十足。我同意他住在我這里,直到他找到工作,而且我們還說好一起去西部看看。這些都發生在1947年的冬天。
有一天晚上,迪恩在我家吃晚飯,他已經找到一份紐約停車場的工作。當時,我正在飛快地打字,他俯下身子,在我背后叫道:“快點,伙計,姑娘們可不會多等的,快點啊。”我說:“等一下,馬上就寫完這一章了。”這可是我書中最出彩的一章!
然后我換了衣服,與迪恩一起飛快趕往紐約,去跟那些姑娘約會。當公交巴士穿過磷光像鬼影一般閃爍的林肯隧道,我和迪恩靠在一起,揮舞著手指,大聲嚷著,興奮地說著話,我也開始變得有勁頭了,就像迪恩一樣。他是那種滿腦子激情的青年人,雖然他還是一位自信滿滿的騙子,這只因為他太想活下去,太希望能獲得人們的關注,如果不這樣,人們便不會理睬他。我知道他在騙我(包括食宿和“寫作”之類),而他也知道我對此心知肚明(這正是我們關系建立的基礎),不過我并不介意,也不會影響我們相處的狀態——既不彼此討好,也不相互干擾。我們彼此鼓勵,仿佛一對傷心的友人。我開始向他學習,就像他也向我學習一樣。每當我有關注的事情,他就會說:“放手干吧,你做的事都是很棒的。”當我寫作之時,他就站在我身后,邊看邊叫道:“是的,非常好!噢!哥們兒,太棒啦!”或者“喲!”的一聲后,用手帕擦擦臉。“噢,哥們兒,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東西可寫!即使可以統統把這一切記錄下來,不受任何限制,沒有文學上的禁錮,也不顧及語法上的禁忌,那……”
“對呀,哥們兒,你講得太棒了。”我可以從他充滿激情的夢幻里捕捉到閃光的火花,他講得如此熱情奔放,滔滔不絕。以至于公交巴士上的人們都轉過頭來張望他這個“興奮過度的怪人”。過去在西部的時候,他把時間分成三份,一份在臺球房,一份在監獄,一份在公共圖書館。人們可以看到,他經常冬天帽子也不戴,就抱著書沖向臺球房,或者爬樹進到同伴家的閣樓上,在那里待上幾天讀書,或者避開法律的束縛。
我們到了紐約——我記不清具體情況了,只記得約了兩位黑人女孩——跟迪恩在用餐的地方碰面……但她們不在那兒。我們前往他上班的停車場,他卻有些事情需要耽擱——在車場后面的小木房里換衣服,面對一塊已經出現裂紋的鏡子稍微打扮一下,才跟我一起出發。那天晚上,迪恩和卡洛·馬克斯見了面,二人的會面真的是重大事件。兩人的腦瓜子都非常聰明,才打了一下招呼,彼此就產生了好感。兩只敏銳的眼睛穿透了那兩只有同樣敏銳目光的眼睛;兩個人都是騙子,不過,一個人的心地光明而圣潔,另一個則心地陰暗還帶有一些傷感的詩意,后者是卡洛·馬克斯。從那以后,我就很難見到迪恩了,我有點傷心。他們雙雙迸發出青春活力,比較之下,我簡直就是鄉巴佬,跟不上他們的趟兒。
整個好戲就要開場了,它熱鬧、繁雜,近乎瘋狂,即將把我所有的朋友和我剩下的家人一并攪起來,成為一塊龐大的云幔,籠罩在美國的夜空上。卡洛對他講起“老蠻牛”李、埃爾默·哈塞爾以及簡的境況:李干著種植大麻的營生,在得克薩斯,哈塞爾生活在賴克斯島,簡吸安非他命吸出幻覺,抱著自己的女嬰在時報廣場瞎逛,終于逛到貝爾維尤精神病院去了。迪恩給卡洛講他不知道的西部人物,比如湯米·斯納克,那位腳部畸形的臺球室殺手,玩紙牌的高手,還是個奇怪的圣徒。他還講起羅伊·約翰遜、大埃德·鄧克爾,包括他的發小、街區的哥們兒,還有那數不清的女孩子、性派對和色情電影,還有他心目中的須眉好漢和巾幗英雄的種種奇遇。他們在大街上一路跑過,一開始對什么都興趣盎然,后來漸漸地變得憂郁,遇事會思考多一些,沖動減少了。不過當時,他們在街道上跑跑跳跳,我則搖搖晃晃地跟在后面,我一生都喜歡跟隨那些讓我覺得有興趣的人。在我看來,只有瘋狂的人才算是活人,他們對生活癡狂,滿嘴瘋話,渴望救贖,渴望擁有一切;他們一貫不知疲倦,從來不談論那些俗事,而是燃燒著,像好似奇妙無比的黃色羅馬煙火筒,持續不斷地噴出火球和火花,仿佛巨大的蜘蛛在夜空里垂下八條腿,其中閃耀著藍光,人們隨之發出“啊!”的贊嘆。在歌德時代的德國,人們是怎么稱呼這種年輕人的呢?首先,你知道的,迪恩打心眼里希望能掌握卡洛那樣的寫作技能,因而他才帶著唯有騙子才具備的含情脈脈向卡洛發動語言攻勢。“嗨,卡洛,聽我說——我要說的是……”我有陣子沒見過他們了,大約兩個星期吧,兩人就在那期間沒日沒夜地神侃,成了鐵得不能再鐵的哥們兒。
春天來了,這是旅行的最佳季節,我們這幫人個個都在準備屬于自己的旅行。我手頭的那部小說一時丟不開,在完成計劃的一半時,我得陪同姨媽去南方看望兄弟羅科;接下來,才著手開始我一生中的首次西部旅行。
迪恩已經出發了。卡洛與我來到第三十四街,在灰狗長途汽車站為他送行。汽車站樓上有一處地方可以拍快照,只需要花費兩毛五。卡洛取了眼鏡,做出一副兇惡的模樣;迪恩拍的是側面像,故意忸怩作態;我照的是正面像,仿佛是一位三十歲的意大利人,模樣兇狠蠻橫,似乎就要把任何侮辱了他母親的人殺掉一樣。卡洛和迪恩小心而仔細地用刀片把這張照片一裁兩半,各自拿了一半,裝在皮夾里。這一次迪恩榮歸丹佛,為此他穿了一套真正的西部人的服裝;他已經完成了在紐約的第一次‘嘗試’。說是嘗試,實際上他僅僅是在停車場里像狗一樣累死累活。作為停車場工作人員,他稱得上是全世界最好的,他能把汽車以四十邁的時速退入一個狹窄的車位,在停穩墻腳前之時跳出來,快速跑過防護板,跳進另一輛汽車,在逼仄的空間讓汽車保持五十邁的時速轉個圈子,快速地倒退回車位,猛地踩下緊急剎車,在下車時還能看見汽車在抖動;然后他像田徑健將一樣朝售票室沖刺,交上一張票,一輛汽車剛停下,車主人尚未下車,他就向車主身子下面鉆進去,不等車門關好,就將引擎發動,在轟鳴聲中將汽車開到可以停放的車位,汽車甩出一道弧線,砰的一聲停到位,剎車,下車,奔跑;就這樣每晚不停地干八個小時,無論晚高峰,還是晚上劇院散場,只要是交通擁擠時間他就得忙個不停,他穿著一條油膩的粗布褲子、套一件磨損的毛皮內襯夾克,腳上的破鞋走起路來啪嗒啪嗒作響。現在他為了回家,買了一套新衣服;藍色料子上有細長的條紋,坎肩等等,都置辦齊全——他為這些在第三大道上花了十一元,還買了懷表加上表鏈,還有一臺手提打字機,如果在丹佛找到工作,他就準備在寄宿所里寫東西了。我們去第七大道的賴克餐館,點了法蘭克福香腸還有豆子,算是吃了一頓告別餐,迪恩上了標有前往芝加哥的公共汽車,隨著一聲轟響消失在黑夜。我們的西部牛仔就這樣上路了。我決定在春暖花開、大地復蘇之時,也走這條路。
的確,這就是我所有公路旅行經歷的開端,接下來的事情太精彩了,必須要談一談。
是的,我要對迪恩進行更深入的了解,一方面因為我需要新的生活閱歷作為寫作素材;另一方面由于我已經結束在校園里的游蕩,再待下去已經失去意義,另外就是雖然我和他性格不大一樣,但他讓我感覺到似乎是失散很久的兄弟;每當他那張蓄著長連鬢胡、消瘦而苦惱的臉以及那條肌肉緊繃而汗漬漬的脖頸映入眼簾,我就回憶起兒童時代在帕特森與帕塞伊克的垃圾堆、游泳場和河邊嬉戲的情形。在他的身上,那件骯臟的工作服顯得非常帥氣,你讓專門定制的裁縫都做不出比它更合身的衣服,但是迪恩可以在艱苦的條件下師法自然獲得取得天然的樂趣。從他樂不可支的談話方式里,我仿佛又聽到那些舊時的伙伴和哥們兒的聲音,來自橋洞下,或摩托車之間,或居民區的晾衣繩下面,在讓人懨懨欲睡的午后門前的臺階上,那些男孩彈奏吉他,兄長們則在工廠勞動。我現時的其他那些朋友全是“知識分子”——查德,人類學家、尼采派的,用低嗓門說話,會以嚴肅的表情盯著你;性情古怪的卡洛·馬克斯,超現實主義者,說話會拖長聲音;“老蠻牛”李,對任何事物都要批判一番——要不就是那些藏頭露尾的犯罪分子,比如目中無人的埃爾默·哈塞爾,還有簡·李,會趴在沙發上的東方毯子上,滿不在乎地看《紐約客》。但是迪恩的智力一點毛病沒有,飽滿而煥發光彩,沒有令人生厭的知識分子作派。他的“犯罪行為”帶給人們的往往不是慍怒和嗤笑,而是引發一陣粗獷的美國式叫好;它帶著西部情調、西部味道,是平原吹來的頌歌,一些事情(他偷汽車的原因只是為了兜風)也早有預兆、正在實現,還包含新意。另外,我的全部紐約朋友都處在頹唐的、夢魘似的境地,整日貶損社會,擺弄他們那套陳腐的、書齋氣的、政治學的抑或心理方面的理由,但迪恩不是這樣,他要獲得面包和性愛,不得不在社會上努力拼搏;“只要我能搞定那個靚妹兒,哥們兒!”“只要大伙有吃的,兄弟,你明白了嗎?我餓了,餓得前胸貼后背了,咱們馬上去搞點吃的吧!”——我們就趕出去找東西吃了,恰似《傳道書》上所說:“太陽底下,人各有分。”
迪恩是一位充滿陽光的西部親屬。雖然姨媽不時提醒我,他會給我招來麻煩,但我耳邊響起新的召喚,眼前浮現出新的地平線,我青春的心對之堅信不疑;盡管他可能為我招來一點麻煩,抑或他最終不和我做朋友,讓我眼巴巴地在路邊餓死或者病死在床上——又有什么關系?我是一位年輕的作家,我渴望啟程。
在這條路上一直往下走,我知道那里會有女人,會有未來,一切都會有的;沿著這條路往下走,那顆明珠會交與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