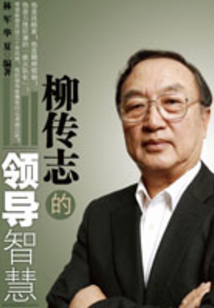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36章 后記 在路上
- 第35章 偉大在于管理自己 成功源于自我管理 (3)
- 第34章 偉大在于管理自己 成功源于自我管理 (2)
- 第33章 偉大在于管理自己 成功源于自我管理 (1)
- 第32章 愛事業就像愛生命 堅定信念身先士卒 (3)
- 第31章 愛事業就像愛生命 堅定信念身先士卒 (2)
第1章 前言
杰克·韋爾奇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別沉溺于管理了,趕緊領導吧!”
到底是不是他的這句話讓領導力成為了企業家們新的“三字經”已經無法考證了。但是,“領導力”在21世紀的中國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卻是不爭的事實。
國外關于領導力的研究已經開展了多年,學派紛呈,成果斐然。然而遺憾的是,因受傳統歷史文化的影響,國內對領導力的理解依然停留在權謀與厚黑學層面。從歷代帝王將相那里繼承來的武斷專橫的領導風格依然大行其道,“領導”就是真理、權威、等級,“領導力”就是管理、控制下屬的能力,諸如此類的錯誤觀念比比皆是。尤其在一些政府機關和國企中,對權力的瘋狂追逐更是直接導致了腐敗和衰敗。一些民營企業也將“經營市場不如經營市長”奉為企業發展的“圣經”。
值得慶幸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家已經走出誤區,開始了中國式領導的探索和實踐。聯想的柳傳志、海爾的張瑞敏、華為的任正非、萬科的王石、TCL的李東生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們以卓越的領導力,感召和帶領下屬積極奔赴愿景,不懼挑戰,百折不撓,最終創造了輝煌的事業。
此外,楊壯、劉瀾等一批專家學者也在不遺余力地介紹國外的領導力學說、翻譯大師們的相關著作,為國內企業家的領導實踐提供了理論武器。然而,在對中西方領導力進行深入研究后,翰威特大中華區首席領導力顧問弗蘭克卻提出:“如果你直接把西方領導力理論拿到中國用,一定會失敗;但是如果你借鑒了西方的理論框架,同時又考慮到了中國的文化和國情,把兩者結合了,你就能夠成功。”他的話無疑對我們學習和引進西方領導力理論提了個醒。
綜觀西方領導力大師的理論,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共識: 實際上,領導力并不是為那些身處高位的人而保留的。在生活中的各個領域,我們都可以發現領導力,而具備領導力的人就是領導者。同時,幾乎所有的領導力大師都認同“領導力與職位無關”這個觀點。但是,在一個商業組織中,如果一名員工在工作中表現出了足夠的領導力,他往往很快會被組織提升到更高的位置上,以發揮更大的作用。而如果一個領導者已經宣布退居二線,并不在組織中擔任某一職位,卻仍然能對企業和繼任者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毫無疑問,這是領導力在更高層次上的體現。
柳傳志就是這樣的一位領導者。2005年,柳傳志宣布退居二線,不再擔任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但是,在往后直到2008年底柳傳志復出的那段時間,全世界都認為,為聯想集團制定戰略的是柳傳志而不是楊元慶,在柳傳志不參與聯想集團具體事務的“后柳傳志時代”,柳傳志仍然是聯想的靈魂。
在更多方面,聯想集團仍然表現出了與柳傳志時代一脈相承的風格,以至于人們會有這樣一個印象: 柳傳志其實并沒有離開。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過去20年中柳傳志為聯想打下的烙印:“搭班子、定戰略、帶隊伍”的管理三原則和充滿中國智慧的商業理論,以及在聯想發展壯大的各個階段所表現出的領導力。
可以說,柳傳志就是聯想的核心競爭力。國內有很多企業早就提出“學習聯想”,在關于聯想和柳傳志的報道中,如“搭班子、定戰略、帶隊伍”、“入模子”、“退出畫面看畫”、“拐大彎”、“別拿長跑當短跑”、“鴕鳥理論”、“把5%的希望變為100%的現實”等反映聯想管理精髓的詞匯和相關的故事隨處可見,這讓聯想至少在方法論上成為了一家并無秘密可言的公司。但同樣的東西,卻是柳傳志一用就靈,任何人都難以復制!說到底,還是人的因素在起決定作用。
在一次接受采訪中,柳傳志稱,他并不愿承認聯想“偉大”,他只將自己的成績歸為兩點: 持續和發展。前者指聯想基業未絕,后者指它仍能不停壯大。這是典型的柳傳志風格: 在聯想2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雖然柳傳志的角色在不斷發生變化,但他卻始終能堅持追求一些樸素的目標,達成外界難以想象的成就。
既然柳傳志的領導如此卓有成效,那么,我們可以將其作為一個典型,從他開始創業到再度復出的過程中提煉出最具代表性的領導力時刻。尤其是在聯想并購IBM個人電腦事業部后,柳傳志在國際化領導上的突出表現,也許能給更多正在進行或準備進行國際化嘗試的企業家們帶來一些啟示。我們認為,這個工作應該是有意義的。
正是基于這樣的想法,我們開始梳理柳傳志領導力形成和發展的脈絡,并將其置于相關領導力理論中進行考察。我們發現,西方的領導力學說中有很多普遍適用的真理,但是也存在一些文化方面的細微差異。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西方領導力大師強調“領導者要隨時公開表揚屬下個人的成績”,而柳傳志為了讓年輕氣盛的楊元慶學會妥協,絲毫不顧及楊元慶在微機事業部取得的成績,而對他的傲慢大加批判。后來的事實證明,柳傳志這樣做是為了更好地培養楊元慶,策略性的壓制反而促使楊元慶更快地成熟起來,也逐漸贏得了公司元老的支持,為其日后的接班鋪平道路。
本著求同存異的“拿來主義”精神,我們一方面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有關領導力的寶藏,一方面繼續從西方領導力學說中汲取營養。最終,著名領導力研究專家庫澤斯與波斯納共同提出的領導力五大實踐被我們選定為本書的框架模型。
自1983年開始,美國加州大學圣克拉拉分校的吉姆·庫澤斯和巴里·波斯納進行了一項長達20多年的持續研究。在此過程中,他們根據成千上萬個案例,總結出了卓越領導者的五大實踐: 以身作則,共啟愿景,挑戰現狀,使眾人行,激勵人心。
在2007出版的《領導力》第四版的前言中,庫澤斯和波斯納寫道:“我們持續的研究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說有一個神奇的第六大實踐,會對領導者的行為來一次革命。我們的研究也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說這五大實踐中的任何一個失去意義。”
他們是有底氣這么說的。盡管領導力學派眾多,但是這五大實踐得到了廣泛認可。
按照這個框架,我們把全書分為五大部分,每個部分對應一個實踐。在柳傳志對聯想長達近30年的領導過程中,我們以這五大實踐為切入點,挑選不同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來探究柳傳志領導力的形成和發展。其中也結合了其他領導力學說和中國本土的領導智慧,希望給讀者學習和研究領導力提供一個參考樣本。
南懷瑾大師曾經說過:“企業這個定義,以中文來講,做一件事業,做一個工作,前途有無限的希望,對社會是有貢獻的,而且是永久的,不是做了幾十年就沒有了,是一代一代相傳的,那個才叫企業。現在沒有這個企業的觀念,只要開個公司,做個生意,怎么去賺錢,就叫做企業,根本就是錯誤。”
在《激蕩三十年》中,吳曉波先生用生動理性的筆法再現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的企業史,其中的風云變幻、興衰沉浮,總讓人不由自主地掩卷沉思。看著一個個曾經風光無限最終卻走向沒落的企業,就能更好地理解南懷瑾大師的感嘆: 中國多的是生意人,缺少的是企業家。
作為早期創業者的代表,柳傳志不僅沒有成為改革的犧牲品,而且能在大浪淘沙之后成為中國企業家的標桿,其核心競爭力就在于,高遠的立意和長遠的眼光。也就是說,他并沒有把自己簡單定位為一個生意人,而是想做一個能促進社會進步的企業家。他提出要把聯想打造成“沒有家族的家族企業”,很顯然,這個目標直接指向了基業長青。
最后我想要說明的是,閱讀再多的領導力書籍也不能保證你一定會成為卓越的領導者,就像熟讀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和葛拉西安的《英雄書》的人不一定能成為領袖和英雄。想要提升自己的領導力,實踐才是王道!
100多年前,當亨利·福特說他的愿景是“讓每一個人都擁有一輛汽車”時,很多人都覺得他是個瘋子。但是歷史最后證明,他是個偉大的企業家和夢想家。
愿景是一個組織的夢想,而夢想通常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但又會情不自禁地被感染。原因顯而易見,如果愿景是那么容易被把握和實現,那么它只能算是一個戰略目標,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愿景。
愿景這個詞在中國原來的詞典里是沒有的。愿就是心愿,景就是景象,對組織來說,它是一種意愿的表達。愿景概括了組織的未來目標、使命及核心價值,是組織哲學中最核心的內容,是組織最終希望實現的圖景。簡單地說,愿景是一個預見未來的美景,這個美景會給人動力去做一件事情。
讓“愿景”這個詞廣為流傳的是世界著名的領導力權威沃倫·本尼斯的《領導者》一書。在2008年的一次訪問中,本尼斯這樣說道:“偉大的團隊包含許多因素,但是首先是一小群人共享的一個強大的愿景。”
吉姆·柯林斯和他的搭檔在寫作《基業長青》時也重點研究探討了“愿景式領導”和“愿景式公司”。愿景的重要性早已成為企業和組織的普遍共識。
本尼斯對領導力有很多極為深刻的見解,但是,“說到根本,領導力只涉及三樣東西——領導者、追隨者以及一個共同的目標”。很顯然,這個共同的目標就是愿景。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個組織中,愿景不能僅僅是領導者個人的,而必須是共享的。正如本尼斯所說:“一個共享的愿景是人們感覺自己在做至關重要的事情,他們感覺自己在宇宙中留下印記。是這樣一種感覺: 盡管我們可能各不相同,但是我們是在一起做這個,而且我們是在做一些可能是改變生命、甚至是改變世界的事情。在這些團隊中,領導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創造一個舞臺,團隊成員可以在上面‘做他們的事情’。”
通俗來講,愿景更類似于我們常說的理想,是企業更高層次的追求,介于信仰與追求之間。愿景不會像信仰那樣永恒不變,也不會像追求那樣是一種短期行為。
加里·胡佛在研究了成千上萬個企業案例之后,總結出了一個成功愿景應該具有的四大特征: 清晰,持久,獨特,服務。
要想讓愿景真正成為企業的核心動力,這四大特征必須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而“持久”更像一股源源不斷的活水,滋潤著事業之樹,使之長青不老。加里·胡佛在《愿景》一書中說道:“你對自己的愿景充滿了信心,而這份信心源自你對下面這些關鍵因素的了解——你知道自己擅長什么、知道哪些因素對你是重要的、知道該如何去經營企業,然后你不畏艱難地堅持著自己的愿景,不管是在繁榮時期還是在蕭條時期,不管是在順利的時候還是在困難的時候。”
實事求是地講,聯想成立伊始更多的是在思考如何生存下去。在特殊的歷史環境和條件下,聯想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有一個能明確代表企業精髓的愿景。這就如同一個人的成長一樣,一個尚處于孩童時期的人通常都不可能樹立清晰、遠大的理想。在人生的開始階段,我們必須通過與外部世界的接觸和磨合,不斷地學習與思考,方能真正認識自己的內心,立下宏偉的志向,并全力以赴奔向未來。
柳傳志什么時候有了高科技跨國公司的夢想?肯定不是在1984年,那一年,柳傳志的目標是讓聯想成為一個年銷售額為200萬元的“大公司”,此時的聯想還停留在求生存的階段;肯定也不是在1986年,那一年雖然聯想漢卡賣得很火,但柳傳志和他的同事更多的是沉浸在把科研成果轉化為商品的快樂之中;也肯定不是1987年,那一年,聯想剛開始代理AST品牌電腦和惠普繪圖儀,柳傳志想的是更多地把機器賣出去。不過,一旦柳傳志開始有了把聯想做成高科技跨國公司的想法,并認定自己能把這個夢想實現的時候,什么都阻擋不住他了。
關于如何實現愿景,柳傳志說過這樣一段話:“聯想以前有個理論,叫進人的時候要撒一層土,夯實了再撒一層土再夯實,我認真思考以后還是堅信這個理論是正確的,現在的聯想團隊是一群高理想、高追求、高智商的年輕人的結合,但這只是結合,目前還不是一支真正的軍隊,還不是一個斯巴達克方陣,我是下定決心要把這支隊伍帶好,這是我站好最后一班崗的職責之一。”
由此可見,“造夢者”的偉大不僅僅是造夢,而更要能打造一支隊伍去實現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