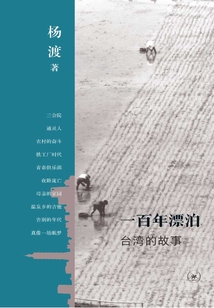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序言:讀楊渡新作《一百年漂泊》(1)
趙剛
九月中旬,楊渡兄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有一部新近完成的名為《一百年漂泊:臺灣的故事》的書稿,想請我寫點東西或是給點意見之類的。這本書主要是以他父親,一個原本注定只能是臺中烏日的鄉下農民,在一九七〇年代磕磕碰碰起起落落,終而成為成功的鍋爐制造業者的一生故事為綱,但也兼寫了頭家娘、地方、家族、信仰、中小企業、工人的故事。“這本書或可作為臺灣史的側顏一讀吧!”——楊渡如此說。
老實說,我有點狐疑。兒女不是不能寫父母(或反之),但要寫得回蕩婉轉寫得有公共意義,也的確比較難,因為常常作者那一廂情愿的耽情,不見得也能讓讀者們產生共鳴。最近這些年頗流行作家爸爸寫兒子寫女兒,我就常不免詫異于這些作家的膽大,這樣親密切膚的關系也敢動輒寫一本書?對象越寫越近,世界越寫越小,就不擔心如此的寫作泄露的不是經驗的逼仄與創作力的枯竭?于是我想起陳映真的一句我以為的名言:“一個人其實不一定要寫作!”
利用課余事親之余,我一頁頁讀下去,竟然發現,沒有勉強,感到興趣,頗有收獲,甚多感慨。《左傳》里說:“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而楊渡兄不正是一個孝子嗎?而且還是一個對大家都可以有所饋贈的孝子。楊渡說得很精準:這本書“告別的不只是父親,是一個時代”。
這本《一百年漂泊》在一個倫理的意義上,是一個孝子為亡父作的一本巨大“行傳”,雖然我必須說它和傳統的行傳不類,因為它并非只是旌表揚善而已,而更是子對父的善惡清濁都試著去盡可能地認識理解,從而認識理解他自身的一個努力。但在一個知識的、社會的意義上,它更是對臺灣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的極其壓縮的“短工業化時代”的一個見證與一紙吊文,以他的父母親為陀螺,畫出小人物在時代的快速旋轉中,在社會的坑坑洼洼中,顛撲沖撞的線條痕跡。因此,這本書的難得可貴恰恰在于它不只是私人或家族感情維度中的書寫,而是以飽滿的對親人的感情為底氣,努力展開對一個時代、對一群轟轟烈烈但卻將被徹底遺忘的人群的認識與反省。而正由于所書寫者是小人物,因此完全沒有某些作家寫大人物父親所帶著的濃濃翻案風,因為這樣的小人物在歷史上根本是無案可稽的。楊渡的寫作救贖了他的父親,更救贖了整整一代的小人物,使之免于被體制化的大官大腕才子佳人的歷史書寫所遺忘。
因此,這本書的確是“可作為臺灣史的側顏一讀”的!
豈止,透過“魅寇”(楊渡父親名字“銘煌”的日語發音)的不尋常的旺盛生命力,我們看到了一般社會經濟史所難以勾畫出來的隱密而驚人的線條,因為魅寇雖是一般意義上的小人物,但卻在他力所能及之地,努力撐破體制與現實所加諸他的種種限制,而這或許是眾多關于臺灣當代的工業化或發展敘事所無從著墨的一個重要側面,因為它們太強調那些既存的結構或文化條件了。楊渡在“終曲”里也如此說:“是的,一個時代,一個屬于工業時代的風景,正隨著父親的離去,慢慢結束了。”讀這本書,讓讀者在魅寇的翻騰不定的無畏人生結束后,深刻地感喟于一個潛在的問題:我們這又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我們又將如何安身立命?我們又將如何面對并迎向未來?我們,又將如何被后人回憶與理解?
以魅寇(一九三〇——二〇一四)的一生為主要線頭,楊渡編織出一個兼具深廣度的社會、人文與歷史的交響風景。又,如果也可以說魅寇的故事是一個被他兒子詩人楊渡所鏤刻出來的一片生動、可信,乃至可愛的浮雕風景,那么,之所以能如此,恰恰是由于魅寇的一生是鑲嵌于一個由小至大、由邇至遠的多層次背景架構之中,包括了家族中的女性、父親與母親的家族史、烏日(或臺中地區)的社會經濟史,以及作為大背景脈絡的日本殖民史與政權更迭史。
這本書是以主人公魅寇的老病臨終為楔子,引領出每一章的歷史回溯。今昔交織,使得敘述張力飽滿。從銘刻著“弘農堂”這個堂號的一間老三合院,作者講起臺灣的一九六〇年代,一個工業化的馬達聲即將響徹全島之前的醞釀蠕動時代。在書寫中,楊渡將這段工業化前的農村史和先人渡海來臺、日本殖民統治、美軍大轟炸、成功嶺的馬場、神風特攻隊以及父系與母系的父祖輩的湖海漂泊或神鬼離奇或兼而有之的命運,以一種蒙太奇的方式拼貼起來,使讀者在平靜的敘事中隱隱地感受到遠方的風雷與腳下的震動。讀楊渡的書,讓我不免想起臺灣這個島嶼的故事的離奇荒誕與血汗現實,絲毫不讓于拉美,但為何終究沒有出現那樣的“魔幻寫實”的文學?這當然是離題了。
“烏日”是一個和包括我在內的眾多成年臺灣男性都發生過關系的地方,因為著名的軍事訓練中心成功嶺就在烏日。千千萬萬的大專生新鮮人都曾在烏日的星空下睡過六周,但其中的絕大多數人卻對這個地方可說一無所知。一九九一年后我來臺中教書,烏日雖是緊鄰臺中市,但卻是一次也沒去過,直到近些年有了高鐵,才常常“到”烏日,從高架公路到烏日高鐵站赴臺北;這也還是一次也沒去過。我服兵役時,連上有一個背后刺了一幅裸女圖的悍兵的家鄉就是烏日,烏日讓我聯想起黑道。那時,我就對這個地名很好奇,感覺這個地名詭異離奇得很,令我無端想起一首黑人靈魂曲《午夜的太陽》。讀了楊渡的書,才知道烏日的地名由來。原來,先民因為烏溪河面寬闊,在靜靜如湖的河水上見到“紅彤彤落日,映滿河面”,就稱這一帶為“湖日”,然后到了日據時期,日本人不索本意,只憑發音,改成了如今的“烏日”二字。但這個誤會還算是“美麗的誤會”,因為相對于“玉井”則是讓人哭笑不得了。在楊渡的書里,因為講到他來自玉井的工程師大姑丈,而有了這一段黑色插播:“玉井原名蕉芭年,余清芳在那里發動襲擊事變,反抗日本殖民統治,日本派出軍隊,機槍大炮全面鎮壓,為了報復,日本人在村子樹一根竹竿,約一百二十厘米高,凡是超過的男子,一律槍殺……它被改名玉井,那是東京一個風化區的名字,殖民政府有意用它來詛咒它的后代。”
借著自家親見與長者口傳,楊渡帶我們回到一個曾經風景迥異的烏日,在那一方水土之中“天空是澄藍的,溪流是干凈的,土地是柔軟的”,而每一個早晨“都是用晶瑩的露水去冰透的風景”。這是楊渡對一九六〇年代烏日的風景記憶。但楊渡并不是一個田園派詩人,他在明媚的大地上看到陰暗的皺褶,從晴空深處聽到霹靂。在謂之烏日的那塊地界上曾終日行走著一個遭受白色恐怖荼毒的“在自己家鄉流浪”,被人叫作“空竹丸仔”的斯文瘋漢。那里的樸實的農民也曾因為干旱而極其惡毒地搶奪水資源乃至親戚反目。而更之前,在日據時期,則因為成功嶺是日本人的軍事養馬場,而使烏日成為經常要躲美軍轟炸的一塊惡地;曾經,成功嶺上、嶺下有過馬匹在如雨的炮彈下,失魂落魄、尖聲嘶鳴、左奔右突的風景,而楊渡的二叔公就是在這樣的空襲下失去了一條腿。這樣一個烏日,在“二戰”末期,又因日本的軍事需要,成為暫時軍服生產的最重要紡織基地,而這個在“工業日本,農業臺灣”政策下的少有例外,卻成為戰后的重要紡織廠——吳火獅的“中和紡織廠”——的前身。
然后就進入了這本書的主要樂章——轟隆隆的臺灣一九七〇年代。魅寇關閉了他脫農轉工的第一個工廠——瓦片廠,開啟了他的“鐵工廠時代”。那是一個雄性的、躁動的、任性的、喜新厭舊的開創時代。
一九七〇年前后是一個關鍵的轉變年代,世世代代綁在土地上的人們開始受到無處不在的“發財”誘惑,于是有人開始種植各式各樣的經濟作物,甚至養一種名叫“白文鳥”的經濟鳥,以為可以牟取暴利,但潮起潮落,總歸是一場熱鬧的空,搞得很多人血本無歸。雖然欲望的心血無時無刻不在劇烈地翻攪著,但是一頭熱的人們對于如何理財、如何借貸、何謂信用、何謂規劃,可謂一竅不通,而這只要看到那時的主要金融機構仍是碾米廠或是各種寄生于地上的信用合作社的地下錢莊就可略見一斑了。而魅寇就是這個時代旋渦下的一個屢遭滅頂但仍奮泅向前的小人物。而那時的烏日已經和一九六〇年代初的烏日風景迥異了。一九七〇年初,那個原先叫作“臺灣紡績株式會社”(村人習稱的“布會社”)的中和紡織廠,已經擴充到一千五百人的規模,而由于大多數勞動者都是女青年,又給這個小鎮帶來了無限的青春風光與愛情故事。也就在此時,瓊瑤的愛情電影也成為人們的必要精神商品,讓無數盼望城市生活的年輕男女得到一種夢想的投射。同時,出現了所謂的“鑰匙俱樂部”,青年男女工人于假日騎摩托車冶游,而女方懷了孕則還要請頭家娘代為提親。與全島的摩托化同時,骨科被時代造就為一重要生意……
楊渡投入而不失冷靜地描寫了魅寇這樣一個臺灣男性農民創業者像一條蠻牛般地沖撞、任性,以及整個家族,特別是他的妻子,為他的發達欲望所付出的包括流亡與坐牢的眾多代價。楊渡不掩其輕蔑與遺恨地速描了那群只想把這只僅余其勇而闖入工業化森林中的小獸魅寇吃干抹凈的無情掠食者的嘴臉,但又以一管熱情如火的筆,描寫了這個時代的新興工人階級群像;他(她)們的揮霍的青春、爆發的生命力、飽滿而壓抑的情欲,他們的肌肉與她們的娉婷,以及工人的粗魯而率真的義氣世界。楊渡把他的腦袋發燒的父親和那個全身滾燙的一九七〇年代寫得極為鮮活。合上書,我還能記得魅寇要周轉,回到家里,非要他母親和妻子答應賣田地的“張”(閩南語,慪氣的意思)樣。“你們啊,憨女人!世界就要翻過來了,你們知不知道?再不抓住機會,難道要一輩子趴在田中央,做一只憨牛?”——魅寇的那兼男性憤怒與小孩撒嬌的聲口,在我書寫的此刻仍余音不絕。雖然這個年代有很多問題,帶來很多的傷害——尤其是環境生態,但楊渡對他父親的這個一九七〇年代卻抱持著一種對英雄與英雄主義的敬重與惜別。一個農民出身的、日據時期小學程度的魅寇,竟然能夠為了自尊,能夠獨力鉆研出一種屬于當時日本鍋爐工業的高端技術。一九七〇年代末的某一個冬天,魅寇在夜暗的埔里鄉間公路上,語重心長地告訴和他一起出差檢查某客戶鍋爐的尚在大學就讀的兒子:“這人生,終歸是一句話:終生職業之奮斗。”
一九七〇年代結束時,這本書的十章已經走完八章了。最后的兩章不能不說是潑墨似的快速走過一九八〇年代之后的三十余年。讀最后兩章的感覺不能說不好,但有一種說不出的蒼涼,而且還是一種似曾相識的蒼涼。后來,我猛然一驚,咦,這不是很典型的中國式的歷史文學書寫嗎?原諒我個人化的聯想,我的確深深地感到楊渡的這兩章書寫很類似《紅樓夢》或是《三國》的尾聲,一種景物蕭條人事全非的大蒼涼:三合院空蕩蕩了,慈祥智慧的老祖母先是不養雞養鴨,然后過世了,魅寇老病殘矣,曾經是烏日美人的小姑姑去世了,紡織廠前朝氣蓬勃青年男女工人進出的盛景消失了……而烏日既沒有了一九六〇年代的山明水秀,也失去了一九七〇年代的朝氣拼搏,而陷入了一片大家樂賭風,處處是揮金如土的“田僑仔”。這當然不只是烏日唯然,全臺灣都變成了“一條大肥蟲,從加工出口型工業吸飽了血,張著大口,饑餓無比,仿佛什么都可以吞進肚”。這股怪風甚至吹到了昔日“弘農堂”的楊家,連一向鄙夷魅寇好賭的魅寇妻也不能豁免于此。而之前非要賣地開工廠的魅寇,此時又為了向家里討錢而“張”(慪氣)了,但不是為了開辦實業,而是為了要買賓士轎車。一九七〇年代終了以后的魅寇唯一的(當然也是很重要的)成就,就是全力投入烏日的媽祖廟的籌劃興建。魅寇從一個無所依憑無所畏懼的壯年,走入了一個回向傳統與宗教的初老之人,而大略從時代的浪頭淡出了。魅寇的下一波,也就是他的兒子——書寫者楊渡,則淡入了鏡頭,攜來了這個社會的變動音訊以及家族的繁衍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