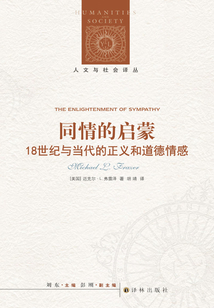
同情的啟蒙:18世紀(jì)與當(dāng)代的正義和道德情感(人文與社會譯叢)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導(dǎo)言:兩種啟蒙(1)
1.反思性革命
人類具有自省這一獨特能力,這一讓我們能反思自己思維和行為的能力。道德反思讓我們停下來,回顧一下自己作為個體的習(xí)慣和行為,并且考察和決定我們是否應(yīng)該繼續(xù)這樣下去。政治反思讓我們將這樣的視角應(yīng)用于掌管和規(guī)范我們的法規(guī)和制度。成熟的反思活動不僅僅是道德和政治哲學(xué)家們的天職,我們每個人也一樣常常會進(jìn)行反思。確實,反思之后我們常常認(rèn)識到我們真應(yīng)該多多反思。
道德反思能讓我們修正和改變我們當(dāng)前的生活方式;政治反思則帶領(lǐng)我們修正和改變我們的社會被統(tǒng)治的方式。這兩者都包含著這樣一種比較活動,也就是事情現(xiàn)在如何,和應(yīng)該如何之間的比較。在政治領(lǐng)域,相應(yīng)的規(guī)范性標(biāo)準(zhǔn)常常被稱為正義的準(zhǔn)則。任何法律、制度或政治實踐若在政治反思中被認(rèn)為是不正義的,那么都該被拒斥。道德和正義的準(zhǔn)則是需要經(jīng)受反思的考驗和修正的。這并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過程,而是要經(jīng)過多重反思和多重修正的。到最后,我們可能認(rèn)識到有一些準(zhǔn)則大概不會被再被改變了——這些準(zhǔn)則就被我們視為具有權(quán)威性的了。用當(dāng)今哲學(xué)里不怎么優(yōu)雅的語言來講,它們變成了我們“反思性平衡中經(jīng)過考察的確信”。[1]
在反思中,我們決定自己的道德和政治準(zhǔn)則。當(dāng)我們堅持反思的自由性時,堅持所有人反思的權(quán)利和責(zé)任時,我們堅持的是自主性,是自我立法。政治上的“自主性”其實是個比喻的說法,這種說法如此普遍以至于我們都忘記了它其實是來自18世紀(jì)的比喻。那時的政治革命的核心是通過共和管理實現(xiàn)“集體的自我立法”,這種集體的自我立法是字面意義上的。啟蒙主義作為同時代思想上的革命,則借用了這個“公民自我制定法律,自我管理”的理念,在個人的層面做了一個類比和比喻——就如個體通過反思來決定正義和道德準(zhǔn)則這個過程一樣。[2]借用這個類比,任何法規(guī)(哪怕是合法指定的)都可以被視作不正義的,一旦它和任何“反思性平衡中經(jīng)過考察的確信”產(chǎn)生矛盾的時候。康德的箴言“敢于認(rèn)識!(Sapere 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WE,8:35)正是啟蒙主義的革命性的口號。
革命者們從來沒法保持陣營的完全統(tǒng)一,在這里也不例外。在該如何理解反思自主性這一點上,并非所有的啟蒙時代思想家都同意康德。對18世紀(jì)道德政治思想的研究表明,啟蒙時代存不同的思想對應(yīng)著對反思自主性的不同理解。我們應(yīng)該分外小心,不要簡單化那個時代的思想流派之間的分別和分歧。此書將主要側(cè)重于對18世紀(jì)兩個主流學(xué)派之間關(guān)于道德和政治反思的分析。第一個是理性主義學(xué)派。18世紀(jì)被稱為是“理性的時代”的,我們對理性主義應(yīng)該不陌生。第二個是情感主義,他們的學(xué)說表明18世紀(jì)并不是理性的天下,也是同情的時代。正是通過同情,經(jīng)修正的反思性情感才得已在個體之間被分享。[3]這并不意味著啟蒙主義的所有倫理和政治學(xué)者們都能被清晰地劃歸入“理性主義者”或是“情感主義者”的陣營。那時代的許多最偉大的思想家就明確地拒絕這個過于簡單的劃分,比如說盧梭。但是事實上,在18世紀(jì)確實存在著關(guān)于反思自主性本質(zhì)的辯論。在這一場大辯論中,很多人明確地站在理性主義的陣營中,而另一些人則旗幟鮮明地站在情感主義的陣營內(nèi)。[4]
啟蒙情感主義的哲學(xué)家們大多是英國人,諸如沙夫茨伯里、巴特勒、哈奇森、休謨和斯密等;而其對立陣營,也就是那時代的理性主義者們則多是法國或德國人。但是這并不準(zhǔn)確,我們不應(yīng)該將學(xué)派上的分別聯(lián)系到國別上。[5]英國也一樣有很多理性主義者,比如塞繆爾·克拉克、威廉姆·沃拉斯頓和理查德·普萊斯等。在歐洲大陸上也有著很多情感主義者,最著名的就是赫德爾,還有他的老師康德在某一個時期也是個情感主義者。情感主義和理性主義不應(yīng)該被看作基于國別的思想之爭。而是關(guān)于反思自主性本質(zhì)為何這個核心問題的,跨越國別的辯論,這個辯論貫穿了整個18世紀(jì)思想史,并一直延續(xù)至今。
無論如何,今日的哲學(xué)和政治學(xué)領(lǐng)域是被理性主義,而非情感主義的繼承者統(tǒng)治的。相較于啟蒙理性主義,啟蒙情感主義長期以來并未得到足夠重視。我們常常將18世紀(jì)稱為“理性的時代”就是最好的證明。今天的哲學(xué)家們?nèi)栽谟眉兇饫硇灾髁x的詞匯來定義啟蒙時代——哪怕他們已經(jīng)認(rèn)識到道德情感主義在18世紀(jì)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羅爾斯就將“啟蒙自由主義”定義為“奠基于理性的,總體上自由又常常是世俗的理論”。這種理論認(rèn)為可以通過對理性的直接訴求而支撐整個政治和道德體系。[6]因此,當(dāng)規(guī)范理論和社會科學(xué)的研究者們重新開始認(rèn)識到感情在我們道德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時,他們常常以為他們在拒斥整個啟蒙時代的哲學(xué),哪怕事實上,他們是在支持18世紀(jì)關(guān)于反思自主性的學(xué)派之一。[7]
本書是對情感主義反思的辯護(hù)和修正。第一章里我將簡短地討論沙夫茨伯里、巴特勒和哈奇森。此后,我將著重討論情感主義最重要的三位思想家——休謨、斯密和赫德爾;與此同時,我還將討論情感主義最大的理性主義批判者:批判時期的康德。雖然此書的很大一部分是對幾百年前文本的研究,但它并不是關(guān)于人類思想史的研究。我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和記錄18世紀(jì)情感主義的發(fā)展過程,而是在于重述在歷史上常被忽略的,理性主義陰影下的情感主義關(guān)于反思的理論;我藉此希望此理論能豐富今日的政治科學(xué),政治哲學(xué)和政治實踐。
2.相互競爭的反思性體制
在啟蒙主義的傳統(tǒng)中,情感主義長期以來都被視為一個破壞性的學(xué)派。這種看法認(rèn)為,一旦我們確定了理性在道德上的無能,我們就只能將正義和道德的基礎(chǔ)建立在感情上了。這種負(fù)面性的對情感主義的理解是具有誤導(dǎo)性的,同時也忽略了啟蒙情感主義對當(dāng)代的最大貢獻(xiàn)。這個貢獻(xiàn)源于情感主義積極性的一面:具體來說,來自它對一種特別的反思自主性的闡明和辯護(hù)。雖然理性主義和情感主義都擁護(hù)這個自主性,但在道德和政治上“何為自我立法”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分歧在于,是哪一部分的自我(self)在承擔(dān)立法工作,哪一部分的自我在遵守所立之法。用柏拉圖主義的話來說,它們的分歧在于心靈的體制。理性主義將立法的部分從其余部分中單另出來,稱其為“理性”。與此同時,情感主義將道德反思所產(chǎn)生的準(zhǔn)則視為整體心靈的產(chǎn)物,他們并不區(qū)分心靈的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部分。
情感主義將心靈作為民主平等制度的理解方式和對情感主義的標(biāo)準(zhǔn)解讀相差甚遠(yuǎn)。尤其是休謨,我們常常認(rèn)為他推崇的是和理性主義一樣的心靈等級制。在這種解讀之下,他和理性主義的分歧只在于心靈的哪種能力應(yīng)為統(tǒng)治者,哪種能力應(yīng)為被統(tǒng)治者。理性主義從柏拉圖起就聲稱理性是主,感情是仆,且本應(yīng)如此;休謨著名地反駁道“理性是,且應(yīng)當(dāng)是感情的奴仆”(T,2.3.3.4)。不過我將在第二章論證,這個引言其實扭曲了休謨的真正意圖。雖然在理論上哲學(xué)家可以將理性和情感的運作區(qū)分開來,但休謨堅持認(rèn)為事實上兩者“密不可分”(T,3.2.2.14)。休謨確實認(rèn)為,僅靠理性是無法帶動任何行為的;也就是在這個層面上,理性只能且應(yīng)該是感情的奴仆。然而休謨筆下所能帶動道德行動的情感(sentiments)并不只有感情(passion),而是包括了理性和想象的整個心靈的產(chǎn)物。感情為這些情感提供行動的沖動,但道德情感可不僅僅是沖動。因此,理性主義和情感主義之間的對比是一個關(guān)于道德心靈是分等級的還是平等的這個觀念之間的對比。平等觀念意味著規(guī)范性權(quán)威的準(zhǔn)則是整個和諧心靈的產(chǎn)物。
雖然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者將心靈的體制視為分等級的,他們自認(rèn)為他們的理論是關(guān)于反思自主性的。因為他們將自己等同于統(tǒng)治者,立法者,而不是被統(tǒng)治和管理的部分。雖然心靈的其它能力和個人的個性都深深被偶然性影響,理性卻只和真相打交道。哪怕我的感情、想象和記憶都是自然和社會因果鏈條中的一環(huán),但我的理性是自由的。啟蒙理想主義者認(rèn)為,如果要將“自我”設(shè)想為可以獨立于自然和社會偶然性的,我們就必須將“真正的自我”看作是純粹的理性的。如果我的行動和準(zhǔn)則是真正的自我的,那它們必須是受這個“真正的自我”立法,管理和命令的。而鑒于這個“真正的自我”是等同于我們所有人都有的某種能力的,那所有個體的“真正的自我”在本質(zhì)上就是一樣的。情感主義對偶然性的看法則大相徑庭,他們將“真正的自我”看作“整體的自我”,包括了社會和心理上的偶然性元素。
康德和啟蒙時期的理性主者們在這一點上和古代極端理性主義者不同,他們承認(rèn),社會和心理上的偶然性造成了我們的許多行為。他們并未試圖根除這些偶然性和其影響,相反的,他們試圖將這些偶然的力量納入理性的控制下。這樣一來,這些力量就會朝著理性必然權(quán)威所要求的方向引導(dǎo)我們。哪怕我的行為是非理性的社會和心理的產(chǎn)物,但若這些偶然性力量是服從我非偶然的“更高的自我”的,那么這些行為就具有了理性上的正當(dāng)性。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的立場在主體上是柏拉圖主義的,而不是斯多葛主義的;在對道德和政治進(jìn)行純粹的理性反思的過程中,感情不需要被完全排除出心理體制來遵從理性權(quán)威的原則。
3.規(guī)范性和描述性
理性主義和情感主義對心靈體制的理解均包含兩種不同的元素。借用休謨的著名區(qū)分,他們都提供了一個關(guān)于實然和應(yīng)然的理論——一個描述性的道德心理學(xué)來解釋我們的道德和政治反思;和一個規(guī)范性的理論來解釋經(jīng)過這樣反思的準(zhǔn)則的權(quán)威性從何而來。情感主義將反思看作包含了感情,想象和認(rèn)知的過程,理性主義將反思看作理性認(rèn)知專有的任務(wù)。情感主義將規(guī)范性看作由對自身全面考察的心靈所達(dá)到的平衡和滿足而來。理性主義將規(guī)范性看作理性的權(quán)威立法,因而,理性是和我們具有自主性的“真正的自我”是對等的。
理性主義和情感主義在描述性心理學(xué)上的分歧,以及他們在規(guī)范理論上的分歧進(jìn)一步指向了他們對這兩個領(lǐng)域的之間關(guān)系的認(rèn)識分歧。在對規(guī)范性和經(jīng)驗性研究的理解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啟蒙理性主義和啟蒙情感主義截然不同。情感主義提供的是規(guī)范性理論和經(jīng)驗性心理學(xué)相結(jié)合的跨學(xué)科的理論。雖然休謨常常被誤認(rèn)為是堅持經(jīng)驗性描述和規(guī)范性判斷之間的分隔的,事實上,對道德和政治現(xiàn)象的經(jīng)驗性研究在他的規(guī)范哲學(xué)體系內(nèi)是占有核心地位的——在這一點上,所有啟蒙情感主義學(xué)派都是一致的。[8]當(dāng)然,在12世紀(jì)出現(xiàn)的學(xué)科分科之前,所有的道德和政治學(xué)家同時也都是社會科學(xué)家,無論他們是理性主義者還是情感主義者。在啟蒙時代,哲學(xué)和科學(xué)之間的明確劃分還未出現(xiàn),這些名詞在18世紀(jì)或多或少都代表著相似的意思,甚至是可以互換的。然而,經(jīng)驗性和規(guī)范性理論之間的關(guān)系在啟蒙情感主義那里卻有截然不同的形式,尤其是相較于其同時代的理性主義學(xué)派來說。
理性主義由規(guī)范性理論開始,純粹基于理性來探索道德原則。此后,他們才轉(zhuǎn)向經(jīng)驗性證據(jù)來決定,如我們這般不完美的真實生物將如何符合理性權(quán)威性的要求。情感主義傳統(tǒng)則恰恰相反,由經(jīng)驗性研究開始,研究是什么讓我們這般真實的生物追隨我們所追隨的東西。情感主義將道德規(guī)范視為我們道德情感的產(chǎn)物,也就是整體心靈的產(chǎn)物。同情在解答這些道德感情的來源時是至關(guān)重要的。同情是社會和心理之間的橋梁,通過同情,我們能分享他人的內(nèi)在心理狀態(tài)。因此,情感主義所提供的經(jīng)驗性的社會心理反思可以被這樣理解,它是關(guān)于我們對他人同情的反思性的擴(kuò)展和修正。與理性主義給出的理性立法相比,情感主義則給我們了更加豐富的,尋找反思性平衡的理論。具體而言,情感主義提供了對道德政治反思的社會和心理解讀,這種解讀是基于經(jīng)驗性的,是側(cè)重于同情這個社會心理能力的。
不過,情感主義關(guān)于反思的理論也不局限于描述性層面。我們承認(rèn),關(guān)于我們道德心理發(fā)展的理論永遠(yuǎn)也不可能單憑一己之力證明我們道德確信的合理性。否則的話我們就搞混了對某種價值判斷的經(jīng)驗性解釋和其規(guī)范權(quán)威性;搞混了實然判斷和應(yīng)然判斷——這一點休謨曾警示我們。不過一旦我們接受對道德心理的相對情感主義的解讀,一旦我們將道德確信看作人類基本感情的反思性發(fā)展,一個獨特的,在規(guī)范層面證明這些確信正當(dāng)性的情感主義方式就會出現(xiàn)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