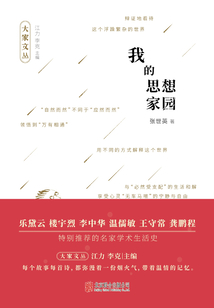
我的思想家園
最新章節
- 第47章 張世英:三十年求進步,三十年尋歸途
- 第46章 張世英:散步時還想哲學問題
- 第45章 人生哲理兩茫茫——張世英教授的哲學人生
- 第44章 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 成一家之言——張世英哲學觀
- 第43章 希望哲學:生長“能思想的葦草”
- 第42章 推進建立當代中國哲學——張世英先生和他的“歸途”
第1章 “為己”與“為人”
《論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如果把這里的“為己”解釋成為一己之私,把“為人”解釋成為他人謀福利,那當然是天大的笑話。朱熹的《論語集注》倒是有一段切要的注解:“程子曰:‘為己,欲得之于己也;為人,欲見知于人也。’”為追求名譽,——“欲見知于人”而為學,則“終至于喪己”;為求自得,——“欲得之于己”而為學,則“終至于成物”。“為人”與“為己”是兩種不同的為學態度,所得到的結果也大不相同:一是“喪己”,一是“成物”。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這兩種不同的為學態度推廣為兩種不同的做人態度。柳宗元自稱:“年少氣銳,不識危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不管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不計較旁人之肯定與否,但欲直抒己見,別無他求,我看這種做人的態度正是“為學為己”的“為己”之意。反之,唯唯諾諾,惟他人之意志是從,效顰學步,不敢稍越雷池,這種做人的態度就叫作“為人”,抱著這種態度做人,其結果只能是“喪己”。
楊朱主張“為我”。這里的“為我”亦非為一己之私。楊朱實際上是要“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孟子罵他“無君”,正說明他反對君王,反對屈從,要作“為己”、“貴己”之人,不作“為人”、“喪己”之人。
中國歷史上有多少但求“自得”,不肯“喪己”的高人雅士值得我們稱頌啊!阮籍不為世之名利所累,自況“至人無宅,天地所容;至人無主,天地為所;至人無事,天地為放”。陸放翁不怕尸骨朽,不患史無名,但喜“墨成池,淋漓豁胸臆”。王陽明主張“學者貴得之于心”,認為“求之于心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李卓吾勸人勿“舍己”,他也主張“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后足”。袁宏道、袁中道“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直攄胸臆”,言其所欲言。他們在為學、做人方面表現了何等超凡脫俗的高遠胸襟!
可悲的是,這些不肯“喪己”之人,卻往往橫遭非議,甚至喪生。何以故?德國現代詩人哲學家海德格爾關于眾人必然“沉淪”的理論,似乎可以用來說明為什么眾人總是淪于“喪己”的道理。在海德格爾看來,人總是“在世界中存在”,總得與他人、他物打交道,這也就是說,人必然“被拋”入一種人世狀態中;而人在這種人世狀態中,總是有意無意地要按照一種外在的標準和并非本己的意志行事,這種標準和意志相當于我們平常所說的“自古皆然”、“人皆如此”、“一般認為”、“固不待言”、“習以為常”、“已成定論”之類的觀念。如果把這類意思用一個籠統的“他”字來概括,那就可以說,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和喜怒哀樂都是取決于“他”,而非取決于己。換言之,常人總是在放棄自己,為他人而存在。海德格爾把這種狀態叫作“沉淪”,“沉淪”的狀態是“非本真”的狀態。反之,擺脫“沉淪”,不受“他”的束縛,就是返回“本真”狀態。用我們中國人的術語來說,“沉淪”、“非本真”就是“為人”、“喪己”,“本真”就是“為己”、“保真”。海德格爾深刻地指出,由于眾人都按照這個主宰一切的“他”行事,所以“人與人之間的差別被磨平了”,“個性和自由選擇被抹殺了”,特立獨行之士“遭到壓制和摧殘”。所謂“木秀于林,風必摧之”,這“風”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他”。在茫茫人海中,特立獨行者寥若晨星,眾人、凡人則總是因“為人”而“喪己”,因“畏”“本真”而“淪”于“非本真”,只有極少數“木秀于林”的高士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寧愿喪生而不肯“喪己”。
如何才能達到“本真”狀態?如何才不致于“沉淪”?前期的海德格爾認為只有靠對死亡的領悟,因為人在死神降臨時,“沉淪”、入世已不可能,這時,人才領會到我們所說的“為己”、“貴己”的真諦和“為人”、“喪己”之無意義。后期的海德格爾認為要靠詩,詩使人沉浸到一個超然物外、超乎喧囂的現實之上的自由境界。這里不是討論死和詩的地方,我也無意評論海德格爾關于死和詩的理論,更不可能要求眾人都不“沉淪”,我在這里只想表示一個愿望,希望多一點“為己”、“貴己”之人,少一點“為人”、“喪己”之人,希望木秀于林、具有獨立性靈之士少受一點“他”的壓制和摧殘!
載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