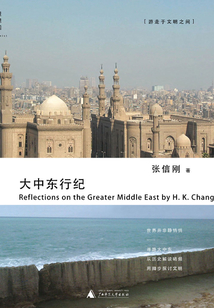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從地理與歷史看大中東局勢
2010年12月,一個突尼斯小販的自焚,改變了北非和中東地區的歷史進程。
突尼斯群眾持續大規模示威,當權二十三年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被逼出走。接著,埃及群眾推翻了掌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兩人都被起訴,兩國都在修改憲法,準備選舉新政府,結果很難預料。
波斯灣島國巴林的什葉派(Shiites)群眾沖擊遜尼派(Sunni)王室,政府以武力鎮壓,又有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前景尚不明朗。
利比亞反對派武裝和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政府由一方示威和一方鎮壓演變成全面內戰;西方國家以武力積極支持反對派,在位四十二年的卡扎菲大勢已去。利比亞可能分裂,前途堪慮。
也門兩派沖突不斷升級,首都薩那(Sanaa)戰火紛飛。在位三十三年的薩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以拖待變,在去留之間徘徊了數月之后,終因受傷而出走。也門的局勢很難預料。
敘利亞先靜后亂,反對派的示威浪潮逐步升高,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政府內似乎有鎮壓和懷柔兩派,近月來軟硬兼施,似乎還有相當的支持者,但已很難扭轉乾坤,重建威權統治。
摩洛哥、約旦、黎巴嫩和伊朗等多國的反政府力量也在尋找機會,隨時可能造成風潮。
美國于此時刺殺了“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將反恐戰爭帶入一個新階段,也使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得以制訂它的新中東政策。
將來無論誰下臺誰上臺,不論美國和它的盟友采取何種政策,阿拉伯各國的人民已經覺醒,中東地區的社會發展和政治生態必將出現深刻變化。
眾多伊斯蘭國家的動亂似乎會使它們更難共同對付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十分清醒,這些伊斯蘭國家的變化極可能會給它帶來比過去更為嚴峻的挑戰。
此外,格魯吉亞最近有反政府示威。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的領土之爭也有激化的傾向。北高加索地區的分離主義和恐怖主義威脅,使整個高加索地區的情勢呈現很大的內部和外部張力。
這一切都說明,這個我稱為“大中東”的地區確實是危機叢生,很值得關心時局的人們密切注視和進一步了解。
2010年3月至12月我在香港《信報》上連續發表了三十九篇“游走于文明之間”的系列文章,記述我個人在“大中東”地區旅游和居住的經歷,介紹各地的歷史、文化、政治、社會和經濟概況,并對這個地區人類文明的發展做了一些綜述。2011年以來,中東和北非形勢驟變。這一方面令我自己多年來的興趣更為增強,另一方面證明我2010年在報上發表的文字,特別是對時局和社會現象的觀察,都頗能經得起考驗。
所以我將已發表的文字加以修訂補充,又增寫了六篇文字,共為四十五篇,以《大中東行紀》為名結集出版。本篇為本書的《緒言》;另附“大中東地圖”、“大中東地區大事年表”和“索引”,以便讀者查對。
“中東”與“大中東”
“中東”是近百年來由歐洲人開始使用的名詞,一般指亞、非、歐三大洲相交的地區,定義并不準確。傳統上中東包括埃及、以色列、(被占領下的)巴勒斯坦、約旦、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門、阿曼、阿聯酋、卡塔爾、巴林、科威特、伊朗、土耳其,共十六個國家。除了以色列,其余十五個都是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伊斯蘭國家。
與上述的十六個中東國家相毗連的還有蘇丹、利比亞、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這五個位于非洲的阿拉伯國家。這二十一國合起來可稱為“文化中東”。
此外,有十個國家的地理和歷史與“文化中東”的關系十分密切;它們的命運難以與這二十一國切割。這十個國家是地中海地區的希臘、塞浦路斯、馬耳他,南高加索的亞美尼亞、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以及非洲東部的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吉布提和索馬里。在這十個國家中,希臘、塞浦路斯、馬耳他、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七國的主要人口是基督教徒;阿塞拜疆、吉布提、索馬里三國的主要人口是穆斯林。
以上三十一個國家(再加上伊朗之東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人類文明最早出現的地區,是世界歷史上不同文明沖突與交融最為顯著的地區,也是當今世界各種矛盾集中表現的地區,可以合稱為“大中東(The Greater Middle East)”。
由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無法與中亞和南亞分割,而這個“游走于文明之間”系列的第二冊將會介紹中亞和南亞,本書的范圍就限于這三十一個國家。
在本書論及的“大中東”三十一國中,二十三個是伊斯蘭國家;除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外,其余二十個是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共有二十二個成員)的成員國。
歷史沿革
從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14世紀,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國(Achaemenid Empire),亞歷山大帝國及其后的塞琉古(Seleucid)王國,羅馬帝國與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拜占庭帝國與波斯薩珊帝國(Sassanian Empire),阿拉伯帝國,塞爾柱帝國(Seljuk Empire),以及蒙古帝國先后在大中東地區建立霸權,控制主要貿易通道。
對今日大中東影響最深的是領土跨越亞、歐、非三洲的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四百年統治(1520-1920)和波斯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的兩百年統治(1520-1720)。19世紀,英國、法國、俄羅斯和意大利先后控制大中東地區的不同部分;一次大戰后奧斯曼帝國崩潰,英、法兩國的勢力達到高峰。今日大中東各國的版圖大致是根據這四個歐洲殖民國家的管轄區而劃定。
二次大戰后美國與蘇聯進行冷戰。美國建立巴格達條約組織,囊括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四個大國;蘇聯則在埃及、敘利亞、南也門、埃塞俄比亞取得優勢。1979年,美國將埃及納入自己的軌道,可謂一大斬獲,卻又因為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而痛失一局。這一年是大中東的一個轉折點。
1990年,蘇聯解體。美國因為伊拉克進攻科威特而發動海灣戰爭,突顯了世界唯一超級強國的實力。從此美國在大中東的力量驟增;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相比也更為強勢。這一年是全世界以及大中東的另一個重要轉折點。
大中東不等于伊斯蘭地區
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一定會同意,大中東是農牧和畜牧業的起始點,城市文明的發源地,象形和拼音兩類文字的首創區,世界三大“一神教”的誕生地。
戰略專家、能源專家和軍事專家都會同意,大中東地區是世界上戰略地位最重要,能源儲量最豐富,武器裝備購買額最高和國際沖突熱點最多的區域。
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也會同意,大中東大部分國家宗教氣氛濃厚,專制統治盛行,經濟發展滯后。
雖然在大中東地區的三十一個國家中有二十三個伊斯蘭國家,卻不能將這個廣大地區定位為伊斯蘭地區。同理,不能因為這二十三個伊斯蘭國家中有二十個是阿拉伯聯盟成員而把它們都視為阿拉伯文化區。然而,由于阿拉伯聯盟的二十二個成員國中有二十個在“大中東”,我們可以認為“阿拉伯世界”涵蓋在“大中東”之內。
大中東的八個非伊斯蘭國家具有顯明的特色,正是由于它們的存在才突顯了大中東地區復雜紛紜的本質。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猶太國家,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大中東地區的忠實盟友,也是這個地區軍事與經濟力量最強的國家。其他的七個基督教國家分屬五種不同的基督教會,但它們都親西方而遠鄰國。
這八個非伊斯蘭國家都缺乏石油資源。除以色列外,經濟與社會發展和它們的伊斯蘭鄰國大致相當。除希臘和亞美尼亞外,其他六國境內都有很高比例的穆斯林人口,處于所謂“文明沖突”的風口浪尖上。
既然大中東地區的三十一個國家中有二十三個是伊斯蘭國家,而伊斯蘭復興又是近三十年來的世界趨勢,要了解大中東就必須要對伊斯蘭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傳統有所認識。
伊斯蘭傳統
伊斯蘭(Islam)于公元7世紀興起于阿拉伯半島西部,創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被尊為先知,是穆斯林(Muslim)社群的宗教、政治和軍事領袖。他的幾任繼承人(哈里發[Khalifa])東征西討,擴張迅速。公元8世紀初,以大馬士革(Damascus)為首都的倭馬亞(Umayyad)王朝的領土西至西班牙,東達巴基斯坦。繼之而起的阿拔斯(Abbasid)王朝在巴格達建立新都,繼承并發展了希臘與波斯文明,于10世紀時創造了輝煌的伊斯蘭文明。在這個文明里,宗教涵蓋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并沒有“政教分離”的概念;法律源自《古蘭經》(Quran,真主的啟示)與《圣訓》(Hadith,穆罕默德言行的匯編);數學、天文學、醫學領先于中世紀的任何其他文明;文學以詩歌為主要形式;哲學大體源自古典希臘,頗多創新,但有些學派曾被判為異端而遭到禁止。
自9世紀起,出現了實質獨立的地方政權。由于哈里發名義上仍是全體穆斯林的領袖,地方統治者一般不敢僭越,只自稱埃米爾(Emir);也有的自稱馬立克(Malik)或蘇丹(Sultan),自行鑄造銀幣,并規定臣民在周五聚禮的禱文中加念自己的名字。伊斯蘭統治者在自己的轄區內統攬軍事、外交、司法、貿易、教育等,擁有絕對權力。統治者依靠軍隊,通過地方士紳和部族首領維持政權,又經常把收稅的工作分包給各地富豪。
伊斯蘭統治者原則上依照《古蘭經》和《圣訓》施政,以宗教區分臣民:穆斯林是一等公民;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瑣羅亞斯德教徒是二等公民,稱為“有經者”(Ahl Al-Kitab),享有宗教自由和一定的自治權,但要交納人丁稅(jizyah);其他人稱為“不信者”(kufr,英譯“infidel”),在社會上被蔑視。
伊斯蘭社會早期是由城市工商階級構成。雖然阿拉伯帝國后來并入許多游牧部落和大量農民,但伊斯蘭統治者向來重視商業活動。在哈里發盛世,帝國的貨幣統一,道路通暢。后來的地方統治者盡管經常互相征伐,但對工商業依舊重視;他們會派出市場巡察員,維護商業道德與秩序,興建商旅客棧以促進貿易。
統治者定期直接傾聽子民的申訴和要求,因此一些宮殿里有接見百姓的廳房。詩人在伊斯蘭社會地位崇高,統治者會經常宴請詩人,而赴宴的詩人則會絞盡腦汁用華麗的辭藻頌揚真主和阿諛君王。統治者也會籠絡宗教學者(ulema),使他們在周五聚禮講經(khutbah,漢譯“呼圖白”)時擁護自己,并在必要時由宗教法官(mufti)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教法裁決(fatwa)。
蘇非主義(Sufism)是伊斯蘭教中的一種神秘主義,它的出現反映了許多穆斯林無法從刻板的正統教義與儀式中得到心靈滿足。蘇非們用祈禱、冥思、舞蹈等方法尋求與真主合一的直接體驗。由于大批本來信奉薩滿教(Shamanism)的中亞游牧民族在10-12世紀轉奉伊斯蘭,之后的蘇非儀式因而帶有若干薩滿教的痕跡。自12世紀起,正統伊斯蘭與蘇非主義開始相互滲透,各地的伊斯蘭社會出現了許多蘇非教團(Tariqa,又譯“道門”)。蘇非教團一般在世襲教主(shaykh,又譯“謝赫”)的領導下,有固定的禮拜和修行的場所,也形成社會上的互助組織,因此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相當影響力。
由于中東地區與歐洲接近,伊斯蘭社會接觸歐洲近代文明較印度和中國為早。奧斯曼帝國在18世紀末期就聘請法國軍官開辦新式軍官學校,并在19世紀中葉開始自上而下的改革運動;埃及在19世紀初開始引進歐洲的軍事和郵政制度。
一百多年來,大中東地區伊斯蘭國家的穆斯林可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是愿意向西方學習、接受國家世俗化概念、傾向民族主義的“西化派”,主要是軍人和專業人員。第二類是希望通過伊斯蘭復興而振興社會的“伊斯蘭主義者(Islamists)”,包括許多在伊斯蘭社會具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學者;其中的溫和派鼓吹建立符合伊斯蘭教義的現代社會,激烈派則敵視西方,主張清除一切違反伊斯蘭教義和禮儀的外來習俗。第三類是教育程度不高、居大多數的中下階層,他們有樸素的宗教認同和民族感情,看法較易受伊斯蘭宗教學者的影響。
經過百余年的演變,這三類穆斯林目前在不同國家的比例各不相同。他們之間力量的消長將會決定大中東地區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