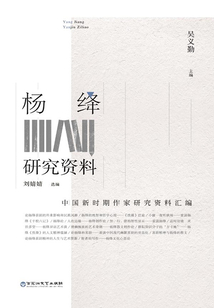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37章 注釋
- 第36章 附錄:楊絳研究資料索引
- 第35章 溫婉與堅韌——論楊絳先生的藝術品格
- 第34章 取法經典 閱世啟智——楊絳的小說寫作觀念
- 第33章 論楊絳喜劇對莫里哀的接受
- 第32章 楊絳研究述略
第1章 論楊絳喜劇的外來影響和民族風格
莊浩然
在中國現代喜劇史上,楊絳是一位后起作家。較早從事喜劇創作、形成獨特風格的是幽默喜劇作家丁西林。之后,又有李健吾、陳白塵等人。李健吾擅長性格刻畫和心理分析的性格喜劇,陳白塵則以辛辣揭露社會黑暗的諷刺喜劇著稱。這些作家在劇壇上露面都比楊絳早,影響也比楊絳大。然而,后起的楊絳卻獨辟蹊徑,在喜劇領域里作出新的開辟與貢獻。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她在上海相繼寫出四幕喜劇《稱心如意》和五幕喜劇《弄真成假》[1](下文簡稱《稱》《弄》),真實地描繪以小資產階級青年為中心的舊中國都市世態畫,給喜劇史帶來富有個人風格的現代風俗喜劇。柯靈回憶上海淪陷時期戲劇文學時,曾譽之為“喜劇的雙璧”“中國話劇庫存中有數的好作品”。[2]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建國以來出版的幾本現代文學史上,卻見不到楊絳的名字。誠如夏衍最近指出,“談當代作家而不提楊絳,是不公道的”[3]。本文意在探討、研究這位長期被忽視的女作家喜劇的外來影響和民族風格。
喜劇是現代話劇中后進的一翼,但如同話劇的其他體裁、樣式一樣,現代喜劇產生、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也是吸收、擺脫、融化外國戲劇,并在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民族的藝術傳統的基礎上,逐步達到現代化、民族化的過程。楊絳的劇作從民族的現實生活出發,在批判地借鑒外來形式和繼承民族傳統方面,不但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也體現融會中外、創建民族的現代喜劇的一些客觀規律。現代話劇的發展歷史表明,任何一種外來形式都受制于民族的社會生活,為民族的歷史和環境所牽引。外來形式只有落根于本國的沃壤中,與民族的生活方式、語言格調、欣賞習慣和藝術趣味相結合,才能經受風雨,茁壯成長。“五四”以來,為創建民族的現代喜劇,不少劇作家曾在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借鑒外國風俗喜劇。這一借鑒一開始就與民族化的過程聯系在一起,經過二十年代的初步探索和三十年代的深入實踐,到四十年代終于進入成熟期。但就每一個作家而言,表現情況又各有不同。個別作家雖也反映民族的現實生活,但全盤搬用外來形式,忽視藝術傳統的繼承。如老一輩劇作家王文顯二十年代用英文寫作的風俗喜劇《委曲求全》,其內容描寫北平高等學府的腐惡生活,揭露教育界的黑暗,但就技巧而言,基本襲用康格里夫、哥爾斯密等人的風俗喜劇。臺詞的俏皮,幽默,以及矯情的議論,更是道地的英國舞臺語言。而多數作家則注重批判地借鑒外來形式,同時繼承民族傳統,努力創建民族的現代喜劇。在這些作家中,楊絳是最遲嶄露劇壇的一位。四十年代喜劇創作在參照中西、消化融會方面臻于成熟的時代條件,楊絳獨特的生活經歷、審美情趣和深厚的中西文學造詣,使她成為這條藝術長鏈中最后也是最為耀眼奪目的一環。誠然,楊絳并不屬于二三十年代把歐洲風俗喜劇引入文學傳統的作家之列,但由于她就學于王文顯任系主任的清華大學外文系,后又一度留學英、法,且孤島時期和石華父、李健吾、黃佐臨等話劇藝術家交往密切,因而她有可能接受、梳理、篩選前輩和同代作家借鑒外國風俗喜劇的經驗教訓,也有條件吸取抗戰時期話劇大眾化和民族化的實踐成果,從一開始就在一個更高的審美層次上進行卓越的藝術創造。其次,楊絳借鑒的出發點是創作現代風俗喜劇,而不是其他喜劇樣式。作者青年時就酷愛描繪社會生活和人情世態的西方小說、戲劇,喜歡觀察、體驗舊中國都市“見慣不怪”[4]的風俗習尚;從她后來創作風俗畫小說《倒影集》,翻譯《小癩子》《堂·吉訶德》《吉爾·布拉斯》諸名著以及卡卜·德·維加等人的喜劇論著,也不難看出她這方面的藝術愛好和精湛修養。顯然,像丁西林、李健吾或陳白塵等人,從幽默喜劇、性格喜劇或諷刺喜劇的角度攝取外國風俗喜劇的有益成分,已不能使楊絳滿足;創作現代風俗喜劇的審美追求,促使她重新回到歐洲風俗喜劇那里,直接探求被前輩和同代作家忽視和更改過的特點。這種間接影響和直接影響的相互承接和旋式推進,使楊絳的藝術創造帶有前人不可比擬的豐富性,也達到一個新的廣度和深度。
楊絳借鑒外國風俗喜劇,一個重要方面是題材內容和思想觀點。風俗喜劇(也稱世態喜劇)原是資產階級的一種喜劇樣式,以描寫上流社會的世態習俗而得名。它雖有諷刺和幽默因素,但諷刺不像諷刺喜劇那樣尖銳辛辣,態度往往比較溫和;其最主要特征是機智。作為歐洲劇壇上流行數百年之久的喜劇樣式,風俗喜劇的題材、觀點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時代的社會生活的演變,它也不斷地發展,呈現新的變化。十七十八世紀英國王政復辟時期,風俗喜劇一度淪為表現宮廷淫蕩風尚的庸俗劇種,但由于啟蒙主義的勃起,它又獲得新的生機與發展。十八世紀后期哥爾斯密、謝立丹等人,承繼文藝復興時期卡卜·德·維加和莎士比亞等人風俗喜劇的進步傳統,以“批判”取代“欣賞”,將英國貴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尚構成一幅幅動人的諷刺畫,恢復并拓展風俗喜劇的現實主義戰斗傳統。到十九世紀俄國奧斯特羅夫斯基,風俗喜劇又被推上新的發展階段。奧氏不是一般地描寫商人和官吏因循守舊的生活習慣和思想情感,而是將“經濟關系當作理解人的行為的鑰匙”[5],深入地揭露少數人專橫頑固而大多數人備受欺凌的沙俄黑暗王國。這就突破西歐風俗喜劇并不否定當時的社會制度的嚴重局限。楊絳的借鑒明顯擺脫新文學初期一度出現的盲目接受、兼收并蓄的幼稚做法,而又承繼“左聯”以來把借鑒的視野從西歐拓展到俄國的發展軌跡。她在重新審視歐洲風俗喜劇題材、觀點的演變歷史的基礎上,對它加以科學分析、鑒別,剔除其糟粕,吸取其帶有批判精神的民主性內容和唯物觀點。她的劇作擅長描寫舊中國都市社會的生活方式和世態人情,而且采取鮮明的批判態度,這無疑得益于西歐風俗喜劇的進步傳統。但在既展示上層社會,又描寫下層社會,從倫理也從生活和財產方面,揭示舊的風俗賴以存在的經濟關系上,又明顯帶有奧斯特羅夫斯基的影響。相比之下,后者的影響更為重要。新文學從最初眼看西方到后來轉向注視俄國的強有力規律又在這里閃現,人們很難在丁西林、王文顯、李健吾的喜劇中見到俄國影響,但這影響在后起的陳白塵、楊絳的作品里卻表現得相當明顯。這并不難于理解。奧氏的主要劇作從二十年代起就相繼譯成中文,而更重要的是,各民族文學的相互影響往往“與其社會關系的類似成正比例”[6],由于中、俄兩國社會的相似,經濟和文化都有一種不期而然的關系,楊絳在題材和觀點方面更多地借鑒俄國風俗喜劇,也就勢在必行。
楊絳的藝術根須始終扎在現實生活和民族傳統的土壤中。她借鑒外國風俗喜劇,為的是創造反映民族生活的嶄新的喜劇藝術。在借鑒中,既有取舍,也有增益。這種從生活出發改造外國風俗喜劇的革新精神,賦予她的風俗喜劇嶄新的時代風貌和民族內容。首先,構成楊絳藝術反映的中心,已不是上層社會的風尚和人物的品行,而是小資產階級青年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作者真實地描寫舊中國都市的生活條件和社會環境,揭示它像一張偌大無比、難于掙脫的羅網,絡住一個個小資產階級青年,演出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劇。淪陷區的黑暗政治和審查制度,雖使楊絳不可能正面觸及日、偽的野蠻統治,不免減弱作品的時代氣氛和政治色彩,但她突破西歐風俗喜劇單純描寫具體生活環境的限制,也不像奧斯特羅夫斯基一般地描寫富與貧這類生活條件和經濟關系,而是深入到物質生產關系這一最基本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域。在楊絳筆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造成財產關系的不平等,使社會分化為貧富懸殊的兩個階層:富者愈富,虛偽狡詐;貧者愈貧,困苦不堪。構筑在商品生產基礎上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倫理道德,儼然占據著統治地位,但封建的宗法的關系、習尚也依然存在,呈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都市社會特有的風貌。《稱》女主人公李君玉投奔的外祖家就是這個社會的一個縮影。二十年前她的母親原是名門中父母偏憐的小女兒,因和一位窮畫家結婚,外祖家就與他們斷絕來往,不久父母在貧病中相繼亡逝,也未惹動外祖家的一絲憐憫之情。如今孤女長成,資產階級的紳士太太竟把自己無情撕毀的親戚關系的破紗衣,撿來作為雇傭剝削的遮羞布。孤女被從北平招到上海,三位舅母想方設法榨取她的廉價勞動,暗里卻又嫌棄她,猶如拍賣商品似的,把她一家家往外推。而早已決定和姑表妹訂婚的表哥也把她視為獵取的對象。《弄》的主人公、小職員周大璋和張燕華,一個只是在叔父家寄居,也得像女傭一樣服侍地產商一家人,還要遭受愛人被奪的痛苦;一個“明知道人家瞧不起”,但為了生存、溫飽與發展,還得“仰著頭在地下爬”。楊絳并未描寫無產者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深重災難,但都市小資產階級青年的種種苦楚和不幸,卻折射出那個社會的罪惡。
馬克思早就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總是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7]。伴隨商品生產關系和價值法則滲入都市社會的各個領域,利己主義和金錢關系成了人們相互關系和一切活動的杠桿,但它罩著封建宗法關系的溫情脈脈的面紗;喜劇所展現的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風尚習俗,也膠結著濃郁的民族色彩。出現在戲中的望族紳士,既有外交官出身的洋氣十足的自由派文人,也有飽食終日、吟詩品茗的封建遺老。勢利自私、專愛雇年輕妖冶的女秘書的銀行經理,表面上道貌岸然,循規蹈矩;滿身銅臭的地產商,一本正經地訓誡妻女“三從四德”,當舊式太太、小姐。而名門閨閣中的太太們,同樣各有癖性,色相不一:或工于心計,口蜜腹劍;或喜歡奉承,刻薄任性;或追慕榮利,揮霍無度……但都富而愈貪,愚而自用,利之所在,鉤心斗角,爾虞我詐。金錢、利欲毒化了人性、人情,也抹去資產階級家庭的神圣靈光。利己主義的冰水,釀成陳祖蔭夫婦的相互攻訐、唇槍舌劍;赤裸裸的現金交易,做成維系陳祖懋夫妻感情的紐帶。愛情、婚姻也不例外。地產商張祥甫把嫁女兒、挑女婿當作生意買賣。陳景蓀和表妹錢令嫻的婚姻,也被烙上爭奪遺產繼承權的恥辱印記。資產階級的腐敗風尚和投機心理彌漫著整個社會,一些蓬門小戶的男女老小,尤其出身寒微、家境清貧的小資產階級青年不能不受其熏染、荼毒。周大璋、張燕華這對為金錢所顛倒的舊戀人,竟把戀愛當作登天梯。一次偶然的機會,周大璋貴識張祥甫的闊小姐張婉華,立即移情別注。他仗著一身漂亮西裝,心機靈活,把兩個姑娘哄得神魂顛倒。而矜才使氣的張燕華也不甘埋沒,耍用閃電式的巧妙手腕,從堂妹手里奪回情人。但他們費盡心機,不擇手段,到頭來竟是“弄真成假”一場空。在舊都市,像周大璋、張燕華這類青年多得很。他們的種種弱點和惡習,并非出于天性惡劣,也非存心不良,而是現存的社會制度造成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貧困驅使成千上萬的人走上爾虞我詐、喪失人格的道路,居于統治地位的生活方式和世態習俗猶如毒菌一樣腐蝕著人們,使小資產者養成一種畸形心理:為了自身的發展,就是進行欺騙、不擇手段也行。周大璋和張燕華的形象,蘊含著作者對舊中國都市社會的否定和使人獲得合理發展的新的社會的憧憬,比起李君玉具有較大的典型性和現實意義。
楊絳的劇作家的生涯是短暫的,但她的喜劇世界并不乏獨創與深度。盡管她的作品很少接觸社會的活動,劇中的社會環境也未能透示特定時代的氣氛,其內容缺乏政治色彩和斗爭意義。但判斷一個作家的歷史功績,不是根據他們“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8]。楊絳所描繪的舊中國都市世態畫,以小資產階級青年為中心,且把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當作理解生活方式和人情世態的鑰匙。她提供的已不是舊的西歐或俄國式的風俗喜劇,而是一種新型的風俗喜劇,它是現代的,也是民族的。無論寄人籬下,中表聯姻,走鬧親家,婚娶儀式,抑或夫妻反目,妯娌齟齬,婦姑勃,叔侄斗嘴,所寫都是民族的生活方式,風尚習俗,同時也是民族的心理情緒和思想性格。它以新的表現對象和深厚的民族內容,契合民族的現代社會關系的特點,也體現作者對現代喜劇的一個重要課題的拓新。舊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分極其廣大的國度。自胡適一九一九年發表“游戲的喜劇”《終身大事》以來,不少喜劇作家傾心于表現小資產階級青年的個性解放、婚姻自主和職業問題等,并以獨特的審美反映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就。丁西林透過日常生活現象,幽默地嘲諷舊都市某些風尚習俗,頌揚反抗壓迫,追求個性解放的小資產階級青年;李健吾從剖析人性落筆,深入內心世界,對小資產階級青年的弱點和品德進行倫理和心理評價;而具有鮮明傾向的陳白塵,則把倫理、心理評價隸屬于社會政治評價,深刻揭示造成小資產階級青年悲喜劇命運的根源。楊絳沒有在前人的成就面前卻步。長期生活在都市青年中間的經歷,為她提供豐富的創作素材;對風俗習尚的敏銳感受和女性作者的細致觀察,使她獲得獨特而深入的審美體驗;而歐洲風俗喜劇和風俗畫小說的深厚造詣,又幫助她出色地完成小資產階級青年為軸心的都市世態畫的藝術創造。楊絳在現代風俗喜劇方面的成功開拓,使她進入屈指可數的有成就的現代喜劇作家之列。
楊絳移植外來形式,創造現代風俗喜劇的藝術實踐,包括相互制約、緊密聯系的兩個環節。與藝術內容相比,藝術形式本身具有更多的繼承性;一種創新的形式往往是通過對舊的形式的吸收、融化而產生的。歐洲風俗喜劇的藝術形式有其最一般的標志,但這些標志也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在新陳代謝、不斷演變中維系其生命力。楊絳沒有隨意采摘歐洲風俗喜劇的某些手法,而是全面透視它的藝術形式的興衰繼絕,并在把握其基本原則和美學特征的基礎上,棄其糟粕,留其精華,因而她的借鑒深得外來形式積淀而成的精粹。作者的喜劇恰如哥爾多尼、謝立丹等人的風俗劇,不但具有復雜的故事情節和計謀成分,緊張熱烈的場面和有趣的穿插,而且包含一整串的風俗性場面和細節;但它們已不像后者單純用以表現環境氣氛和社會心理,同時也是構成劇作情節的基礎,劇本的故事就是通過這些風俗性的、純粹情節性的場面而透露出來,這又酷似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風俗劇。這種種采取,保留了風俗喜劇賴以存在的情節結構的要素,也體現作者獨具匠心的藝術借鑒。比起情節結構,表現手法和語言的借鑒顯得較為復雜。歐洲風俗喜劇以對話的機智俏皮、幽默風趣為重要美學特征,但在綿遠久長的演變中,也曾受過十六世紀英國“尤菲綺斯體”[9]的影響,出現離開性格和情勢,專從對話中的雙關語、明喻、警語和各種華麗的藻飾去獲得喜劇效果的不良傾向。康格里夫、謝立丹等人不必說了,就是近代的王爾德也未能擺脫其羈縻。這一傾向也曾程度不同地浸淫二三十年代中國某些作家的喜劇創作。楊絳堅決摒棄它的消極影響,而張揚以維加、莎士比亞、哥爾多尼和奧斯特羅夫斯基等人為代表的優秀傳統,把民間的群眾口語作源泉,努力創造和性格、情勢一致的幽默機智的對話。實踐表明,藝術形式的借鑒總是受制于作家的文藝觀點和審美追求,離開正確、健康的文藝觀和美學觀,就談不上棄其蹄毛,留其精粹。但關鍵還在于民族化、現代化。借鑒如不消化,生吞活剝,就有“西化”的危險;而繼承倘若離開現代話劇的特點,削足適履,也會有“變異”的危險。楊絳深諳此中三昧。她從新的表現對象和話劇形式的特點出發,一面采取外來的良規,并聯系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藝術趣味加以發揮;同時研究、了解傳統藝術的基本精神和美學特征,學而化之,以豐富和發展風俗喜劇的藝術表現手段,使劇作形式在個人獨特風貌中蘊涵著嶄新的民族風格。
情節結構是構成民族風格的重要因素。細心的讀者不難見出,楊絳引進以風俗喜劇為主的外來結構藝術,正是立足于中國觀眾“要故事,要穿插,要熱烈的場面”[10]的欣賞習慣和藝術趣味,而且在引進的同時就加以改造制作,并吸收傳統結構藝術的要素給以延伸和發展,形成寓豐繁于單純的顯著特點。從結構形式看,作者雖承襲包括風俗喜劇在內的歐洲戲劇的焦點透視法,但在情節的安排、布局上,卻摒棄歐洲戲劇常見的藏頭露尾的寫法,而把西歐流浪漢體小說“用一個主角來貫穿”[11]的結構方式,和點線組合的傳統結構形式加以融化。作者以小資產階級青年的悲喜劇遭際為中軸線,全部紛繁復雜的劇情圍繞這條中軸線布局,使整出戲有主體,有陪襯,有穿插,首尾銜接,渾然一體,而且貫穿在中軸線上的每個點——每幕戲都有相對獨立性,形成近似傳統戲曲縱向發展、點線分明的組合形式,但由于中軸線采用多線結構(由一主兩副或多副糅合而成),且從固定的視點和視向去表現劇情,組織畫面,加之時空的限制,因此又內蘊著歐洲戲劇的集中凝練,縱橫交織。在這方面,楊絳的劇作是與李健吾的《青春》、陳白塵的《升官圖》取同一步調的,但就點線組合的方式而言,楊絳的劇作純用喜劇式,又迥異于后者。《稱》圍繞孤女寄人籬下的悲喜劇遭遇,用喜劇反復式串合:一幕是一家,好比翻畫冊,一幅幅翻過去,展現上流社會不同的世態,孤女各別的遭遇,最后霧消云散,來了個出人意表的大團圓。《弄》則用喜劇對比式,男女主人公戀愛的悲喜劇,一面聯系著名門望族的紳士淑女,一面聯系著蓬門小戶的男女老小。在不斷映照中,真假互見,虛實相生,不但展示都市不同階層的眾生相,也做成主人公的“弄真成假”,可笑可憫!事實表明,楊絳劇作借鑒戲曲的結構形式,并未脫離話劇自身的特點,而是把戲曲的東西完全化為自己的血肉,“仍其體質,變其豐姿”,在保持話劇本體形式的同時,賦予它豐盈的民族風姿。這種批判地繼承的態度,也表現在采取傳統結構原則、手法方面。從風俗喜劇極摹世態、曲盡人情的美學要求出發,楊絳沿襲西方戲劇讓劇中人敘述戲臺以外所發生的事,巧妙處理疏密和隱顯之間的辯證關系。作者善于“審輕重”,做到該省略的冷淡處,只需三言兩語,就把來龍去脈交代清楚,該渲染的熱鬧處,則不惜筆墨,極盡描摹之能事。《弄》第三幕后,把重點放在智奪情人、走鬧親家、補行婚禮等關鍵的喜劇場面,緊鑼密鼓,極力敷演,而對其他次要情節,則通過敘述,一帶而過。這一疏密處理,突出線上的點,有力地表現全劇的主旨。為強化重點,作者在情節發展的各個層次上,還綽綽有余地揳入巧妙有趣的穿插,使喜劇糾葛錯綜復雜,波瀾迭起,而又諧趣橫生,令人解頤。而對不必要的非本質的部分,則善用截斷之法,在隱去的部分,給觀眾留出想象的空間,并利用它們業已造成的氣氛和節奏,為緊接發生的場面做鋪墊,使藝術結構具有傳統畫論所說的“隱顯之勢”。作者還擅長通過“貫穿道具”(如“行李”“佛手戒指”等)的埋伏照映,一面渲染全劇的“主腦”,同時溝通點線,成為“穿插聯絡之關目”[12]。顯示借鑒傳統、“為我所用”的卓越才能。
含而不露,婉而多諷,是楊絳劇作民族風格又一顯著特點。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核心,不是西方的模仿說(即寫實),而是虛擬說(即寫意)。它不滿足于逼真地模擬客觀生活對象,而要求表現它的本質特征,重視意味的美,強調發揮作者和觀眾的創造作用。楊絳以西方戲劇的寫實為基礎,融會傳統戲劇、小說的寫意。她總是通過人物外部言行的逼真模仿,揭示其內在的性格和感情特征,但這種模仿并非人物外部形態的簡單再現,而是擇其主要特征而加以表現,筆觸委婉,細致,而又留有余地,引人遐思,呈出她特有的含而不露、婉而多諷的風格特征。作者描繪名門望族的紳士淑女,明顯帶有中國古典美學強調神似和表現的特點,但它不像陳白塵借助漫畫式夸張,變其形來傳其神,而采用以形傳神的手法,常常只是描寫他們衣冠楚楚、言辭堂皇的外表,引導觀眾透過偽裝,去深入地感受、認識人物的各色嘴臉和丑惡靈魂,從而做出間接性的審美判斷。張祥甫和太太議論嫁女兒、挑女婿的一場戲,作者并未直接剖露祥甫內心的丑,但他那似乎通曉世故、人情練達的一席話,卻引起觀眾對這位商賈靈魂的庸俗和銅臭的判斷。實踐表明,讓丑藏于美的假象中,對丑的本質的揭露就來得更深刻、更含蓄。這種讓觀眾體味包含在漂亮言辭背后的無形的褒貶,或從自我吹噓的漏洞窺其無知、可恥的寫法,酷似《儒林外史》“不著一辭,而情偽畢露”[13]的諷刺藝術。把丑的本質與美的假象加以對照,也是楊絳常用的手法。人物丑與美不協調的兩面,往往不是在某一瞬間同時暴露出來,而是表現在各別的言行的總體中。作者巧妙利用舞臺時間和空間的距離,以一連串的形象因素不斷誘發觀眾的思考和想象,使他們通過形象因素的有機銜接和重新組合,對人物的本質特征獲得深刻的審美認識。蔭夫人體恤、愛護、關懷孤女的高尚表白與憎厭、誹謗、驅趕孤女的卑劣行徑,就是在各種矛盾糾葛、不同場面中表露出來。由于拉長時空的距離,觀眾就能在審美再創造中獲得鮮明的整體感,真正把握蔭夫人口蜜腹劍、貪婪狡詐的喜劇性格。楊絳的劇作不但有諷刺,更有幽默和機智。西方風俗喜劇又名機智喜劇,其主要人物都有意處理成富于機智的人物,且往往以機智取勝。丁西林筆下的男女主人公多數也屬于這類機智的喜劇人物。而楊絳筆下的青年知識分子,則是受環境宰制、帶有悲劇色彩的喜劇人物,他們更接近陳白塵《結婚進行曲》的男女主人公,卻又缺乏后者與黑暗環境抗爭的意識和斗志。楊絳賦予人物機智的氣質,但更多的是以含淚的微笑,表現他們盲目的營營擾擾,可笑可憫;即使是個別品行純正的人物,也以深厚的同情,憐惜地撫摸他們的傷痛,形成“感也能諧,婉而多諷”[14]的特點。《稱》中的李君玉置身于勢利炎涼的環境,卻始終保持晶瑩、純潔的品性。她雖年輕,但機敏聰慧,識見不凡。無論逆境、順境,都以時常露在嘴角的一絲微笑,應付裕如。但這位精神樂觀、性格幽默的少女,也有安分守己、屈從忍受的一面。她對個人的權利缺乏認識,更不曾為擺脫左右自身的環境而抗爭。她的“稱心如意”的結局,只是作者主觀的美好想望。而周大璋和張燕華則是帶有明顯缺陷的人物。盡管他們不肯向環境屈服,卻又始終不曾征服他們的環境。他們悲苦的命運與其說是悲劇,不如說是人生的諷刺。楊絳對他們有同情也有諷刺。她的同情只是寬容,并非贊許;她的諷刺雖非鞭撻,但分明還是諷刺。柯靈說得好,楊絳的笑“是用淚水洗過的,所以笑得明凈,笑得蘊藉,笑里有橄欖式的回甘”[15]。這種含淚的笑,烙上孤島時期鮮明的時代印記,但也透露出作者“在漫漫長夜的黑暗里始終沒喪失信心,在艱苦的生活里始終保持著樂觀的精神”[16]。
楊絳喜劇的民族風格還突出表現在語言方面。“五四”以來,丁西林、李健吾等人都曾借鑒西歐風俗喜劇對話的機智俏皮、幽默風趣,以及其他外來語言養分,并在民族化、群眾化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獨特的語言風格。但毋庸諱言,他們的前期劇作對語言的民族化、群眾化尚缺乏有力的實踐。相比之下,楊絳喜劇語言的民族化、群眾化,一出手就達到較高的水平。中國傳統戲曲講究賓白“明白簡質,用不得太文字”,“作劇詩,亦須令老嫗解得,方入眾耳”[17]。楊絳的語言既無二、三十年代喜劇作品常見的歐化毛病,也無文白駁雜或知識分子腔調很濃的文句,它是從現代日常生活口語提煉而成的規范的文學語言,質樸、純凈、簡潔、曉暢,即使沒有文化的人,也能聽得真切明白,但又不乏機智諧趣,留有令人品嘗、思考和想象的余地。這種帶有醇厚民族風味和個人風格的語言,是楊絳喜劇民族風格的重要標識,而其呈露出來的最大特色乃是臺詞生活化。傳統戲曲推重“家常口頭語,熔鑄渾成,不見斧鑿痕跡”[18]。楊絳尤為擅長通過日常生活的言談話語,自然而然地引起喜劇沖突,讓觀眾透過人物似乎無關宏旨的三言兩語,領悟他們不協調、不正常的關系,也窺見陳腐、庸俗的世態人情。如張元甫出場的一段對白,短短十幾行,只是家常話語,但從“我本來也不想來——恰好有點事兒,燕華的媽要配花邊,說是上海的好”,到“跑了,就跑了”,“當然是男人,不會跟女人跑”,“騙得她喜歡就好”,再到“嫁妝么?她那一身本領就是活嫁妝,一個月二三分錢的利呢”,“一個子兒也沒有”,卻層層剝露這位娶了后妻的父親的絕情;張元甫并非富商,但人的靈魂一旦為金錢所扭曲,父女關系也就成了赤裸裸的商品關系。這種生活化臺詞,扎根于性格和世態的深處,富有幽默和機智的趣味,但又完全摒棄西歐風俗喜劇的矯情議論,長篇臺詞。探究作者藝術創造的奧秘,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較少借用外來的語言表現手法,而主要采用白描、寫意等傳統手法。顧愷之論畫指出,“四體妍媸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19]。楊絳可謂深得其精義。她從不直接介紹人物的外貌、性格,也不注重外部動作的描寫,總是憑借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家常話語,就能傳神地描摹性格、心理,畢肖地狀寫世態、習俗。擔心兒子入贅的周母,腳著破鞋闖門索子,已是令人忍俊不禁,而她在大庭廣眾之中,一會兒纏住假“親家”,據理抗爭:“男比女大,陽比陰貴,倒讓你們女家壓沒了我們男家,只怕皇帝家也沒有這個規矩。”“你女婿怎么能干,也是從我這個肚腸子里爬出來的呀!”一會兒頓腳坐地,放聲大哭:“我還想穿了紅裙子做婆婆呢!送終兒子都沒有了。活著沒依沒靠,死了也只好到三岔路口搶些冷羹飯吃了!”這些臺詞,令一位市井婦女聲態并作,現身紙上,使彼癡愚村俗的世相,如在眼前。白描、寫意也用于布景設計和幕前提示。作者沒有描繪宛如生活全貌的寫實布景,總是有意識地凈化舞臺,或用少許實物概括全貌,或露其要處而隱其全,以單純、洗練的布景和提示,充分揭示規定情景的本質,烘托人物的喜劇性格。這種寫法“不似中有似”,留給觀眾藝術想象的廣闊空間,引導他們進入比生活真實更為深邃的藝術真實的境界。但不容否認,楊絳的生活化臺詞注重狀世態,有時不免忽略肖口吻,因而有些對白過于淺顯,含蓄不夠。比不上李健吾喜劇對話的含蓄蘊藉,意味深長。
原載《福建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