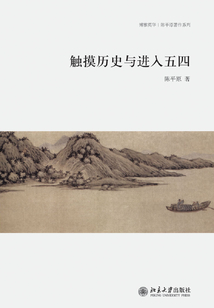
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關于“五四運動”
在20世紀中國,“五四”運動是個使用頻率極高的專有名詞,老百姓耳熟能詳,學界更是了如指掌。作為一門新崛起的顯學(相對于四書五經或唐詩宋詞),關于“五四”的研究著作,確實稱得上“車載斗量”。八十年來,當事人、反對者、先驅、后學,無不激揚文字,留下各自心目中的“五四”。仔細分梳這些色彩斑斕而又互相癥牾的圖景,那是專家學者的工作;至于一般讀者,只需要對這場影響極為深遠、不斷被后人掛在嘴邊的群眾運動,有個大致的了解。
于是,我選擇了權威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希望能得到一個簡明扼要的答案。因為,與“成一家之言”的專家著述不同,辭書講究準確、簡要、平實。誰都知道,若想盡快進入某一特定語境,沒有比借助辭書更合適的了。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紛紜復雜的“五四”,固然并非三言兩語就能打發;可“百科全書”出現如此多的錯漏,畢竟出人意料。看來,“耳熟能詳”、“了如指掌”云云,需要打點折扣。
以下抄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五四運動”這一詞條,然后略做補充、辨析。文中*號為筆者所加,目的是提供對照閱讀的線索。
五四運動(May Fourth Movement)1919年5月4日中國發生的一次群眾運動,其宗旨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政府。一般認為,這次運動是現代中國的一場文化和思想上的啟蒙運動*。1919年1月,各協約國談判對德和約,消息傳到中國,中國人得悉和會決定將原德國在中國山東省的特權轉交給日本,同時日本政府對以軍閥袁世凱為首的北京政府發出最后通牒,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企圖獨自支配全中國*。當北洋政府即將簽訂和約并答應二十一條要求的消息傳開時,北京13所大專院校的3000余名學生舉行罷課*,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同時舉行游行示威。政府軍警對運動實行鎮壓,逮捕學生32人,這立即引起北京各校學生舉行總罷課,隨后全國各地學生紛紛走上街頭,舉行示威游行,召開宣傳大會,并實行抵制日貨。6月3—4日,北洋政府進行了大規模逮捕,僅北京一地,即有千名學生被捕。運動聲勢波及各大城市,上海、南京、天津及其他各地的工人舉行罷工,上海各家商店舉行罷市,以聲援學生和工人,全國文化界也表達了對這次群眾性斗爭的同情,斗爭隨即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革命運動。北洋政府最后被迫釋放全部被捕學生,將三名親日的內閣總長撤職*,并答應將不簽訂和約及二十一條要求*。
五四運動前夕,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開始創辦刊物、發表文章,提倡民主和科學,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推動新文化*。溫和派知識分子以胡適為代表,反對馬克思主義,卻強烈支持文學改革,主張用白話文代替古文;提倡婚姻自由,反對父母包辦;主張取締娼妓;并以實用主義代替儒家學說*。五四運動既加速了國民黨的改組,也為共產黨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上和組織上的基礎。
——錄自《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
關于“五四運動”,不同政治立場及思想傾向的論者,會有相去甚遠的解釋。注重思想啟蒙的,會突出《新青年》的創辦、北京大學的改革以及新文化運動的勃興對“五四事件”的決定性影響,因此,論述的時間跨度,大約是1917至1921年;表彰愛國主義的,則強調學生及市民之反對北洋軍閥統治,抵制列強霸權,盡量淡化甚至割裂5月4日的政治抗議與此前的新文化運動的聯系。但不論哪一種,都不會只講“文化和思想”,而不涉及“政治和社會”。承認5月4日天安門前的集會游行具有標志性意義,那么,所論當不只是“思想啟蒙”,更應該包括“政治革命”。
“二十一條”乃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由日駐華公使于1915年1月當面向袁世凱提出。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袁世凱在四十八小時內答復。兩天后,袁除對五號條款聲明“容日后商議”外,基本接受日本要求。1919年1月,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上,要爭取的是廢除“二十一條”,歸還山東,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等,而不是是否答應“二十一條”。另外,袁世凱死于1916年6月6日,“同時”一說,令人誤會1919年的中國,仍由袁執政。其時中華民國的總統乃徐世昌,總理為錢能訓,外交部長則是率團出席巴黎和會的陸徵祥。
“北京13所大專院校的3000余名學生”舉行的不是“罷課”,而是示威游行——事件發生在1919年的5月4日。由于政府采取高壓政策,逮捕了32名學生,第二天方才有各專門以上學校的學生代表集會,決議自即日起一律罷課,同時通電全國并上書大總統。而《上大總統書》上簽字的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有23所,代表9860名學生。
北洋政府被迫釋放全部被捕學生,是在6月7日。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的職務,則是6月10日。不過,三位親日派,并非如文中所說都是“內閣總長”——曹時任交通總長,章乃駐日公使,陸則是幣制局總裁。
罷免親日派曹、章、陸后,北洋政府仍然準備對列強屈服:17日電令和談代表簽字,23日改為讓代表“相機行事”。因國內壓力日益增大,徐世昌總統25日方才通知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可以拒絕簽字。根據當時的通訊條件,政府的電報6月28日夜里才送達,而和約則定在當天上午簽字。據陸徵祥、顧維鈞日后撰寫的回憶錄,他們的拒絕簽字純屬“自作主張”。另據《時事新報》和《民國日報》大同小異的報道,28日那一天,眾多旅法華工和學生包圍了專使寓所,“以致專使等不能赴會簽字”。
《晨報》1919年7月5日發表《我國拒絕簽字之經過》,介紹7月3日晚收到的陸徵祥等6月28日所發電文,至此,國人對于拒簽經過方才有比較詳細的了解。陸等稱“不料大會專橫至此,竟不稍顧我國幾微體面,曷勝憤慨”,“不得已當時不往簽字”,作為和談代表,未能盡職,只好辭職并準備接受懲戒。7月11日《晨報》刊出《政府訓電專使之內容》:“某方面消息云,政府前日(9日)電巴黎專使轉各國云:中國之不簽字,系國民反對甚烈,政府愿全民意,是以拒絕簽字。唯中國極希望于得滿意之妥協后,當即行補簽。望和會延長期限,俾得從容討論云云。”不難想象,此則被公開曝光的“訓令”,激起了極大的公憤。5月15日《晨報》又發《政府對外態度之近訊》,稱國際上確有要求中國政府“補簽”的巨大壓力,日本輿論表現得尤其露骨,“唯政府方面對于訓令補簽之說,仍極力否認;據云,政府本無簽字之成心”——如果說前者真假難辨,后者則是公開撒謊。
談論影響“五四”運動之得以形成與展開的“知識分子”,李、陳、毛的排列順序令人費解。就算排除“溫和派”的蔡元培與胡適,影響最大的“激進派”,也仍非陳獨秀莫屬。尤其是談論“創辦刊物”,還有比陳之主編《新青年》更值得夸耀的嗎?至于毛澤東在湖南主辦的學聯刊物《湘江評論》,總共只出版了五冊(1—4號,加上臨時增刊1號,刊行于1919年7—8月),文章質量再高,也無法擠進“五四”時期重要刊物的前三名。更值得注意的是,《湘江評論》創刊號出版于1919年7月14日,將其放在“五四運動前夕”論述,無論如何不恰當。
作為一種思想方法的“實用主義”,與作為一種價值體系的“儒家學說”,二者并不完全對等。“五四”時期,批判“儒家學說”的,遠不只胡適一派;而胡適之接受西學,也不局限于“實用主義”。談“問題與主義”之爭,“實用主義”可以派上很大用場;可新文化人之“打倒孔家店”,從終極目標到理論武器,均與“實用主義”沒有多大關系。將“五四”時期的思想潮流,簡化為李大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與胡適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兩大流派的斗爭,此乃50年代全國上下批胡適留下的后遺癥。
這里僅就史實考辨而言;至于意識形態與解釋框架如何制約著“五四”運動的意義闡發,牽涉的問題更多,暫不涉及。
其實,以上所述,沒有驚世駭俗的高論,也談不上獨創性。之所以選擇具有權威性而又代表一般知識體系的“百科全書”,目的只是說明一點:紀念了幾十年的“五四”,未必真的為大眾與學界所了解。
那么,“五四”運動到底是如何爆發,又如何被后世紀念與詮釋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