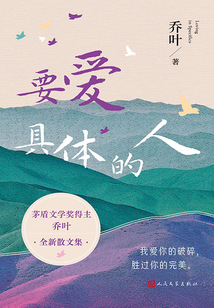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自序
《要愛具體的人》,這本書的書名取自于書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和編輯們商量書名的時候,我們在第一時間不謀而合地選中了它。等到定了之后,我才開始琢磨,這書名怎么就那么投我們的心思呢?
要,這個字頗有一種祈使句的口氣,仿佛命令。但用在此處當然不是命令。這是我的自說自話,是我對自己的提醒。而之所以有此提醒,是因為我發現,相比于具體的人,抽象的人總是更容易讓人愛的。比如那些在舞臺中央的明星偶像,抑或是那些活在傳說中的歷史人物。他們在抽象中纖塵不染,散發著璀璨的光芒。就人的意義而言,這些抽象的人就是我們的“詩與遠方”。而身邊所有具體的人——無論熟悉的還是陌生的人,他們是多么的灰暗駁雜,懦弱易碎,與此同時,柔軟溫暖,剛硬熱烈,堅韌頑強,這也是他們。走在大街上,坐在地鐵里,看著身邊這些陌生面孔,我知道,所有抽象的形容詞都附著在這些具體的人們身上。
我清楚地知道著他們,如同知道著我自己。因為毋庸置疑,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個,最平平無奇的一個。我提醒自己去愛他們,其實就是提醒自己去愛自己。
至于愛,這當然也是艱難的,如同修行——去掉“如同”吧,就是修行。不知不覺,我的寫作時長已經有三十多年。可以說,在這三十多年里,我既學習著如何寫作,也學習著如何愛自己,更學習著如何愛這個世界。
愛這世界的什么呢?當然只能是人。
網約車司機、菜市場小商販、保潔女工、飯店服務員、散步時邂逅的孤獨的老人……我在生活中遇到的這些具體的人們,就這樣聚集在了這本書中。就是這些具體的人們,常常讓我感到這個貌似散淡的世界其實是那么默契,這個貌似黯淡的世界其實是那么多彩,這個貌似粗糙的世界其實是那么精微,這個貌似平凡的世界其實是那么可愛。
汪曾祺曾在一篇自述文章里寫自己的童年生活,說他小時候從家到學校的路上要經過一條大街和一條巷子,街巷上有很多店鋪、手工作坊、布店、醬園、雜貨店、爆仗店、燒餅店、賣石灰麻刀的鋪子、染坊等等,“我到銀匠店里去看銀匠在一個模子上鏨出一個小羅漢,到竹器廠看師傅怎樣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車匠店看車匠用硬木車旋出各種形狀的器物,看燈籠鋪糊燈籠……百看不厭。有人問我是怎樣成為一個作家的,我說這跟我從小喜歡東看看西看看有關。這些店鋪、這些手藝人使我深受感動,使我聞嗅到一種辛勞、篤實、輕甜、微苦的生活氣息。”
——辛勞、篤實、輕甜、微苦,這四個詞準確地擊中了我。是的,這也是我從這些具體的人們身上感受到的氣息。從他們身邊路過時,和他們擦肩而過時,他們的這些氣息總是會讓我不由得放慢腳步,甚或駐足良久,去細細觀看,細細聆聽,細細想。
在一篇創作談里,我曾比喻自己是個拿針的人:“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拿針的人。……拿針的人,似乎也有一根針一樣的心。常常覺得自己的心是很小很尖的,見到什么都想扎一扎,縫一縫。”——針一樣的心,不是針眼兒一樣的心。針眼兒的重點是極端狹窄的面積,而針一樣的心,其要義在于針尖的敏感和銳利。作為一個拿針的人,我有自己的小野心:渴望或者說奢望著這小小的針尖上有著天空的遼闊和海洋的深情。仿佛這小小的針尖上有一顆顆被施了魔法的種子,能夠生長出奇跡般的大。
后來就明白了,我有的只是針,種子和土壤都在這些具體的人們這里。正如《認真的人》里那個叮囑我要去什么地方看頭茬月季花的老人,她和媽媽常常奔赴這個城市的各個角落賞花,她七十五歲,她媽媽九十五歲。亦如《活得明白的人》里那個說話嘎嘣利落脆的小服務員,她在給盤里的魚翻身時告訴我們,翻魚不能叫翻魚,要叫順魚,這是黃河岸邊的老規矩……
我愛他們。我明白我的存在對他們無足輕重,但他們對我的意義卻截然不同。因為我和我的文字就生活在他們日復一日的奔波勞作中,生活在他們一行一行的淚水汗水中,生活在他們千絲萬縷的悲傷和歡顏中,生活在他們青石一樣的足跡和海浪一樣的呼吸中。我和我的文字靠他們的滋養而活,他們卻對自己的施與一無所知。他們因不知而更質樸,我因所知而小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