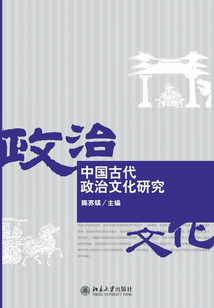
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研究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一釋張衡“禁絕圖讖”疏
《后漢書》卷五九《張衡傳》載:“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后,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張衡認為“圖緯虛妄,非圣人之法”,“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遂上疏順帝,要求“收藏圖讖,一禁絕之”。疏中為說明圖讖之“虛妄”,做了如下考證: 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者,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后,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后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于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圣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余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于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后人皮傅,無所容篡。中華書局點校本,1965年,第1910頁。 文中的“讖”、“讖書”、“圖”、“圖讖”、“圖緯”,顯然都是泛指讖緯,關于讖與緯的異同問題,筆者贊同二者互辭、不可區分說。參陳槃:《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1本第1分,中華書局,1987年;鐘肇鵬:《讖緯論略》,第9—11頁。即所謂“《河洛》《六藝》”。李賢注引《張衡集》云:“《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是張衡所見讖緯有《河洛》類四十五篇,《六藝》類三十六篇,共八十一篇。疏中所謂“八十篇”,系舉成數而言。《續漢書·祭祀志上》載劉秀封禪刻石曰“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見《后漢書》,中華書局點校本,1965年,第3166頁。荀悅《申鑒·俗嫌篇》引荀爽語曰“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諸子百家叢書》影印明文始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3頁。劉勰《文心雕龍·正緯篇》曰“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可證東漢的讖緯確有八十一篇。《隋書》卷三二《經籍志》讖緯條對八十一篇的構成有更具體的說明: 其書出于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中華書局點校本,1973年,第941頁。八十一篇究竟包括哪些篇目?張衡、荀爽等東漢人應該是清楚的,可惜未留下有關文字。現在只有后人的一些說法可供參考。
《隋志》著錄《河洛》類只有《河圖》二十卷、《河圖龍文》一卷,本注曰:“梁《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亡。”顯然,《隋志》作者見到的《河洛》之書已不全了,完整的目錄也未見到,因而說不清四十五篇的全部篇目。《文選》李善注引用了《河圖》類的《括地象》、《帝覽嬉》、《帝通紀》、《著命》、《闿包受》、《會昌符》、《龍文》、《玉版》、《考鉤》,清人汪師韓認為這些就相當于《河圖》九篇。汪師韓:《韓門綴學》卷一“緯候圖讖”條,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錢塘汪氏刻本。安居香山認為,此說雖缺乏堅實的證據,但這九篇“確是《河圖》各篇中最可信賴的資料”。說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6頁。清人蔣清翊考得《洛書》類的《甄曜度》、《靈準聽》、《寶命號》、《錄運期(法)》、《稽命曜》、《摘命(亡)辭》六種。安居香山亦持肯定態度,認為在現存的《洛書》篇目中這六種較為可信。 同上書,第68頁。鐘肇鵬則認為《洛書》六篇中無《稽命曜》,而有《洛罪級》。鐘肇鵬:《讖緯論略》,第73頁。今天尚可見到的《河圖》篇目共有四十余種,《緯書集成·解說》統計為42種(第67頁),《讖緯論略》統計為40種(第71—72頁)。《洛書》篇目共有十余種,《緯書集成·解說》舉出11種(第67—68頁),《讖緯論略》舉出13種(第73頁)。除上面提到的十六種外,還有三十余種。安居香山指出:“它們中的許多是六朝以后的偽作,或是篇名的誤寫”。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第67頁。此說大致不錯,但《赤伏符》、《合古篇》、《秘徵篇》、《提劉篇》等見于《后漢書》、《續漢志》的篇目,應當是比較可信的,“九圣之所增演”的三十篇或有殘存其中者。
關于《七經緯》篇目,《后漢書》卷八二《方術樊英傳》李賢注有一種說法: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琁機(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此注所舉只有三十五篇,所缺的一篇,有人認為是《禮》緯《默房》,也有人認為是《孝經》緯《左右契》或《春秋》緯《命歷序》。參閱鐘肇鵬:《讖緯論略》,第35、60頁。李賢的《后漢書注》是他作太子期間(675—680)召集張大安、劉訥言、格希元、許叔牙等學者共同完成的,《舊唐書》卷八六《章懷太子賢傳》,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年,第2832頁。其中只有劉訥言是當時著名的《漢書》學家,《舊唐書》卷一八九《儒林傳》,第4956頁。其他人學術背景不詳,所提供的《七經緯》篇目也未載明出處。陳槃便懷疑其真實性,認為“賢注三十六緯之目,東拼西湊,無以充其數,故止于三十五篇也。”見氏著:《讖緯釋名》,《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第313頁。
《隋志》著錄的七經緯有《易緯》八卷、《尚書緯》三卷、《詩緯》十八卷、《禮緯》三卷、《樂緯》三卷、《孝經勾命決》六卷、《孝經援神契》七卷。另有《禮記默房》二卷,不知是否屬《禮緯》;有《孝經內事》一卷,不知是否屬《孝經緯》。《春秋緯》全然不見,只有漢末人郗萌“集圖緯讖雜占”而成的《春秋災異》十五卷。本注曰:“梁有《春秋緯》三十卷,……亡。”《隋志》作者已見不到完整的《七經緯》,對三十六種篇目也未一一舉出。《隋志》又說:八十一篇之外“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似乎認為《詩》緯《推度災》、《氾歷樞》、《含神霧》和《孝經》緯《勾命決》、《援神契》不在三十六篇中,與李賢注的說法不同。
《隋志》成書于顯慶元年(656),早于李賢注二十余年。《隋志》的作者已不知《七經緯》三十六篇的確切篇目,李賢等人的說法又從何而來呢?趙翼《陔馀叢考》“后漢書注”條:“梁時有王規,嘗輯《后漢》眾家異同,注《續后漢書》二百卷。又劉昭集《后漢》同異,注《后漢書》一百八十卷。吳均又注《后漢書》九十卷。則唐以前注此書者已多。章懷注蓋又本諸書也。”中華書局,1963年,第110頁。原文“昭”誤作“昉”。今據《梁書》卷四九《劉昭傳》(中華書局,1973年,第692頁)改。李賢注中的《七經緯》篇目或許來自南朝舊注,但其可靠性仍無法確定。今天尚能見到的《七經緯》篇目超出李賢所列之外的還有數十種,見《緯書集成》和《讖緯論略》相關部分。它們是否都屬于三十六篇之外的“雜讖緯”也難以斷言。
張衡所謂“八十一篇”究竟包括哪些篇目今已無法確定,但東漢時的讖緯有個朝廷認可的八十一篇的定本存在是肯定的。《后漢書》卷一《光武帝紀》中元元年條明確記載:“是歲……宣布圖讖于天下。”自此以后,再造圖讖便屬非法。《后漢書》卷二《明帝紀》載:永平十三年十一月,“楚王英謀反,廢……所連及死徙者數千人”。同書卷四二《光武十王傳》載其事曰:“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此事還涉及濟南王康。《光武十王傳》:“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奸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明帝紀》又載:永平十六年五月,“淮陽王延謀反,發覺 ……所連及誅死者甚眾”。《光武十王傳》載其事曰:“有上書告延……招奸猾,作圖讖,祠祭祝詛。”同書卷四〇《班固傳》還提到:“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這幾樁大獄都與圖讖有關,張衡所說“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也許就是指此類事件而言。可見自光武帝宣布圖讖于天下之后,八十一篇成為定本,于此之外再行造作便是大罪。自明帝懲處三王之后直至漢末禪代之際,公然造作讖緯的事很少發生。除朝廷厲禁之外,張衡所說“《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后人皮傅,無所容篡”也是原因之一。無所容篡,李賢注:“謂不容妄有加增也”。《后漢書》卷五九《張衡傳》,第1912、1913頁。前述汪師韓、蔣清翊、李賢等人的說法,則為我們大致勾畫了這一定本的輪廓, 那么這些讖緯又是何時形成的?張衡疏中自“讖書始出”至“哀平之際也”,都是關于這一問題的考證。其中自“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至“成哀之后,乃始聞之”一段,說的是成帝以前不見有人稱引讖緯,劉向父子“亦無讖錄”。然而眾所周知,秦始皇時曾出現“亡秦者胡”、“今年祖龍死”、“始皇死而地分”等讖語;見《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年,第252、259頁;《漢書》卷二七《五行志》,中華書局點校本,1962年,第1400頁。昭帝時“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亦為讖語,眭弘(字孟)則做出了“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的解釋。《漢書》卷七五《眭弘傳》,第3153—3154頁。更重要的是劉向父子雖無讖錄,但于術數略天文種著錄了“《圖書秘記》十七篇”。見《漢書》卷三〇《藝文志》,第1765頁。姚振宗《七略別錄佚文序》曰:“《藝文志》所載書名、篇數、卷數,本諸《七略》,《七略》本諸《別錄》,無大異也。”(《師石山房叢書》,開明書店制版,第2頁)
案“圖書”一詞在漢代或泛指官府中的圖籍文書,如《史記》卷五三《蕭相國世家》:“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卷九六《張丞相列傳》:“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或為《河圖》、《洛書》之簡稱,如《漢書》卷六《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有“麟鳳在郊菽,河洛出《圖》《書》”。或特指讖緯,如《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燕人盧生……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續漢志》卷二《律歷中》載章帝詔,引《河圖》及《尚書》緯《琁璣鈐》、《帝命驗》之文,既而曰“每見圖書,中心恧焉”。“秘記”一詞的用法與“圖書”大致相同,有時泛指官府圖籍,如《晉書》卷二四《職官志》:漢成帝置尚書五人,“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有時亦特指讖緯,如《后漢書》卷三〇《楊厚傳》:“祖父春卿,善圖讖學”,臨死戒子統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秘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楊厚“少學統業,……曉讀圖書”。文中“圖讖”、“秘記”、“圖書”皆指讖緯。“秘記”有時又稱“秘書”,亦指讖緯。參《漢書補注》卷三〇《藝文志》“圖書秘記十七篇”條,中華書局影印本,1983年,第898頁。劉向父子著錄的《圖書秘記》十七篇,當然不是泛指官府圖籍文書,因而很可能是讖緯。
劉向校書時,成帝還命謁者陳農為使者,“使求遺書于天下”。《漢書》卷十《成帝紀》,第310頁。這十七篇《圖書秘記》或許就是陳農搜集來的,其中多有言及天文星象的內容,故被劉向歸入天文種。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圖書秘記十七篇”條曰:“《續漢志》、《晉志》、《帝王世紀》、《通鑒外紀》皆有黃帝受《河圖》作星官之文,意者天文家取《河圖》、《洛書》中所有如《稽曜鉤》、《甄曜度》之類錄為是書。”《師石山房叢書》,開明書店制版,第146頁。其說可以參考。又《后漢書》卷二〇《祭遵傳》載張滿反叛失敗后嘆曰“讖文誤我”,而《華陽國志·公孫述劉二牧志》載張滿此語作“為天文所誤”。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1頁。《后漢書》卷二三《竇融傳》有“今皇帝姓號見于圖書”之語,袁宏《后漢紀》則作“上之姓號具見于天文”。張烈點校:《兩漢紀》,中華書局,2002年,下冊,第78頁。可見讖緯有時就被稱作“天文”。參任乃強說,見《華陽國志校補圖注》,第334頁。
張衡對上述事實肯定是知道的,所作《思玄賦》有“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一句,即指“亡秦者胡”而言。《后漢書》卷五九《張衡傳》,第1924頁。因此,他說秦漢之際“莫或稱讖”,夏侯勝、眭孟“無讖一言”,不是指零星的讖語尚不存在,而是指屬八十一篇系統的讖緯尚處于“始出”階段,“知之者寡”,故不見稱引。《漢書》卷七五《李尋傳》載尋語有“五經六緯,尊術顯士”一句。顏師古注引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孝經》緯也。”(第3179頁)清人閻若璩認為據此可“知成帝朝已有緯名矣”。(見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卷五九《張衡傳》,中華書局影印本,1984年,第668頁)但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劉攽據上下文提出疑義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謂二十八舍。”又引官本考證云:“劉攽駁顏,其論甚合。”王氏進而指出:“案《天文志》,太微廷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五帝者……蓋即五經,六緯者,六諸侯。《天官書》同。蓋漢世天文家說如此。”(第1381頁)劉攽、王先謙等人的解釋雖缺乏根據(說見李學勤:《〈漢書·李尋傳〉與緯學的興起》,《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96年第2期),但從上下文看,將“五經六緯”理解為某種天象,仍有一定道理。所以,“成哀之后,乃始聞之”一句應理解為:屬八十一篇系統的讖緯自成帝、哀帝后才開始大量出現,并為人們所知。
自“《尚書》堯使鯀理洪水”至“圖讖成于哀平之際也”一段,是關于讖緯大量出現于哀、平之際的考證。這段文字文意不太通順,不知是否有錯簡。但仔細分析,仍可看出其中包含了兩層意思。第一層自“《尚書》堯使鯀理洪水”至“堯受命”,下接“一卷之書”至“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說的是讖緯內容自相矛盾,決非圣人所做,而是后人偽造的。第二層自“《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至“訖于成帝”,下接“至于王莽篡位”至“圖讖成于哀、平之際也”,說的是讖緯中出現了戰國之人和西漢成帝以前之事,而對成帝之后的事,包括王莽篡漢這樣的大事,卻只字不提。由此判定“圖讖成于哀、平之際”。
對這段考證中的共工和公輸班兩條,有學者提出質疑。惠棟《后漢書補注》卷十四曰:“共工治河,事見汲郡《竹書》及《周語》,在鯀前。而張平子駁之,非也。”又引吳仁杰《補疑》曰:“《禮記》:‘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尚幼,般請以機封。’般與班同,則公輸班正出春秋時矣。”張舜徽主編:《二十五史三編》,岳麓書社,1994年,第4冊,第170頁。參閱王先謙:《后漢書集解》,第668頁。但這些質疑并不能動搖張衡的基本結論。特別是讖緯中出現的西漢皇帝至成帝止,不見哀帝、平帝及王莽,確是讖緯大量形成于哀、平之際的有力證據。此疏限于篇幅未將相關考證充分展開,但張衡是東漢順帝時人,所見八十一篇不僅完整無缺,而且尚未摻入后人繼續編造的內容。他對待讖緯的態度也比較公允客觀。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對他的看法整體上應給予充分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