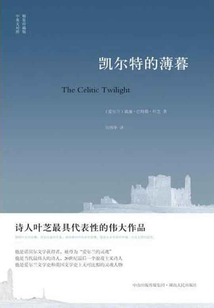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85章 走入薄暮
- 第84章 INTO THE TWILIGHT
- 第83章 在路邊
- 第82章 BY THE ROADSIDE
- 第81章 無意義的夢
- 第80章 DREAMS THAT HAVE NO MORAL
第1章 前言
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出生于距離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不遠的山迪蒙。父親約翰·巴特勒·葉芝是亞麻商人杰維斯·葉芝的后裔。約翰·葉芝結婚的時候正在學習法律,但是很快他便輟學,轉而學習畫肖像畫。他的母親(即威廉·巴特勒·葉芝的祖母)蘇珊·瑪麗·波雷克斯芬來自斯萊果郡上一個盎格魯—愛爾蘭裔家族。葉芝出生后不久,便遷至位于斯萊果的大家族中,他本人也一直認為是斯萊果郡孕育了自己真正的童年歲月。巴特勒—葉芝家族是一個非常具有藝術氣息的家族。詩人的哥哥杰克后來成為一位知名的畫家,而他的兩個姐妹伊麗莎白和蘇珊則均參加過著名的“工藝美術運動”。
為了詩人父親的繪畫事業,葉芝的家庭后遷至倫敦。起初,葉芝和他的兄弟姐妹接受的是家庭教育。詩人的母親由于非常思念故地斯萊果,經常給孩子們講家鄉的故事和民間傳說。1877年,威廉·葉芝進入葛多芬小學,并在那里學習了四年。不過威廉似乎并不喜歡在葛多芬的這段經歷,而且成績也并不突出。由于經濟上的困難,葉芝全家于1880年底遷回了都柏林。起初住在市中心,其后搬到位于郊外的皓斯。
在皓斯的時光是詩人重要的發展階段。皓斯周圍是丘陵和樹林,相傳有精靈出沒。葉芝家雇了一個女仆,是一個漁人的妻子,她熟知各類鄉野傳奇,娓娓道來的神秘冒險全都收錄在后來出版的《凱爾特的薄暮》里。
在開始進行詩歌創作之前,葉芝便已經嘗試將詩歌和宗教觀念、情感結合起來。后來,他在描述自己童年生活的時候曾說過“……我認為……如果是一種強大且悲天憫人的精神構成了這個世界的宿命,那么我們便可以通過那些融合了人的心靈對這個世界的欲望的詞句來更好地理解這種宿命。”
葉芝早年的詩作通常從愛爾蘭神話和民間傳說中取材,其語言風格則受到拉斐爾前派散文的影響。這一時期,雪萊的詩對葉芝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后來的一篇關于雪萊的文章中葉芝寫道:“我重讀了《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在世界上的所有偉大著作之中,它在我心里的地位比我預想得還要高得多。”
葉芝早期還受到彼時愛爾蘭著名的芬尼亞組織領袖約翰·奧里亞雷的影響。詩人晚年曾說,奧里亞雷是他所見的最“風流倜儻的老人”,“從奧里亞雷的談話以及他借我或送我的愛爾蘭書籍中,成就了我一生的志業。”在奧里亞雷的介紹下,葉芝認識了道格拉斯·海德和約翰·泰勒。
1896年,葉芝結識了奧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介紹人是他們共同的朋友愛德華·馬丁。格雷戈里夫人鼓勵葉芝投身民族主義運動,并進行戲劇的創作。盡管葉芝受到法國象征主義的影響,但顯然他的創作具有清晰而獨特的愛爾蘭風格。這種風格在葉芝與愛爾蘭年輕一代的作家的交往中得到強化。葉芝和格雷戈里夫人、馬丁以及一些其他愛爾蘭作家共同發起了著名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或稱“凱爾特文藝復興運動”)。
這場運動最不朽的成就之一便是艾比劇院的成立。1889年,葉芝、格雷戈里夫人、馬丁和喬治·摩爾創立的“愛爾蘭文學劇場”。這個團體僅僅存在了兩年,而且并不成功。在兩位擁有豐富戲劇創作經驗的愛爾蘭兄弟威廉·費依和弗蘭克·費依以及葉芝不計報酬的秘書安妮·伊麗莎白·弗萊德里卡·霍爾尼曼(一位曾經于1894年參與過蕭伯納《武器與人》在倫敦首演的富有的英國女人)的鼎力協助下,這個團體成功打造了一個嶄新的愛爾蘭國家戲劇界。在著名劇作家約翰·米林頓·辛參與進來以后,這個團體甚至在都柏林靠戲劇演出賺到了不少錢,并于1904年12月27日修建了艾比劇院。在劇院的開幕之夜,葉芝的兩部劇作隆重上映。從此以后一直到去世,葉芝的創作生涯始終和艾比劇院相關。他不僅僅是劇院的董事會成員之一,同時也是一位高產的劇作家。
葉芝一生都對神秘主義和唯靈論有濃厚的興趣。他晚年甚至親自將印度教《奧義書》譯成英文。通靈學說和超自然的冥思成為葉芝晚期詩歌創作的靈感來源。一些批評家曾抨擊葉芝詩作中的神秘主義傾向,認為其缺乏嚴謹和可信度。W·H·奧登就曾尖銳地批評晚年的葉芝為“一個被關于巫術和印度的胡言亂語侵占了大腦的、可嘆的成年人的展覽品”。然而正是在這一時期,葉芝寫出了他一生中很多最不朽的作品。若想理解葉芝晚年詩作的奧妙,就必須要了解他于1925年出版的《靈視》一書的神秘主義思維體系。
1913年,葉芝在倫敦結識了年輕的美國詩人艾茲拉·龐德。事實上,龐德來倫敦的原因一部分便是為了結識這位比他年紀稍長的詩人。龐德認為葉芝是“唯一一位值得認真研究的詩人”。從1913年到1916年,每年冬天葉芝和龐德都在亞士頓森林的一個鄉間別墅中度過。這段時間里龐德擔任葉芝名義上的助手。然而當龐德未經葉芝的允許擅自修改了他的一些詩作,并將其公開發表在《詩刊》雜志上后,兩位詩人的關系便開始惡化了。龐德對葉芝詩作的修改主要體現出他對維多利亞式的詩歌韻律的憎惡。然而很快兩位詩人都開始懷念雙方共事、互相學習的日子。尤其是龐德從歐內斯特·費諾羅薩的寡婦處學到的關于日本能樂的知識為葉芝即將創作的貴族風格的劇作提供了靈感。葉芝創作的第一部模仿了日本能樂的劇作是《鷹之井畔》。他于1916年1月將這部作品的第一稿獻給龐德。
葉芝通常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用英文寫作的詩人之一。然而,不同于大多數現代主義詩人在自由體詩領域不斷做出嘗試,葉芝是傳統詩歌形式的大師。現代主義對葉芝詩作風格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詩人逐漸放棄早期作品中傳統詩歌樣式的寫作,語言風格也越來越冷峻,直接切入主題。這種風格上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他的中期創作中,包括作品集《七片樹林》、《責任》和《綠盔》。
1923年葉芝獲諾貝爾文學獎,由瑞典國王親自頒獎。獲獎的理由是“以其高度藝術化且洋溢著靈感的詩作表達了整個民族的靈魂”。他在兩年之后發表了一首短詩《瑞典之豐饒》,以表達感激之情。1925年,葉芝出版了一本嘔心瀝血的散文作品《靈視》,其中他推舉柏拉圖、布列塔諾以及幾位現代哲學家的觀點來證實自己的占星學、神秘主義及歷史理論。
葉芝通過龐德結識了很多年輕的現代主義者,這使得他中期的詩作已經遠離了早期的《凱爾特的薄暮》時的風格。他對政治的關注也已經不再局限于文藝復興運動早期他所醉心的文化政治領域。在葉芝早期的作品中,他靈魂深處的貴族立場體現無余。他將愛爾蘭平民的生活理想化,并且有意忽視這個階層貧窮孱弱的現實。然而一場由城市中的下層天主教徒發起的革命運動迫使葉芝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創作姿態。
葉芝新的政治傾向在《1913年9月》這首詩中得到了體現。這首詩抨擊由詹姆斯·拉爾金領導的著名的1913年都柏林大罷工。在《1916年復活節》中,詩人反復吟誦:“一切都已改變,徹底改變,一種恐怖的美卻已誕生”。葉芝終于意識到復活節起義的領袖們的價值就在于他們卑微的出身和貧困的生活。
整個20世紀二十和三十年代,葉芝無可避免地受到他的國家以及整個世界動蕩局勢的影響。1922年,葉芝進入愛爾蘭參議院。在他的參議員生涯中,葉芝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曾擔任貨幣委員會的主席。正是這一機構設計了愛爾蘭獨立之后的第一批貨幣。在1925年,他熱心地倡導離婚的合法化。1927年,葉芝在他的詩作《在學童中間》里如此描述作為一名公眾人物的自己:“一位花甲之年的、微笑的名人”。1928年,由于健康問題,葉芝從參議院退休。
葉芝的貴族階級立場以及他和龐德之間的密切關系使得這位詩人和墨索里尼相當接近。他曾在許多場合表達過對這位法西斯獨裁者的仰慕。他甚至寫過一些歌頌法西斯主義的贊歌,盡管這些作品從未發表過。然而當巴勃羅·聶魯達于1937年邀請他到馬德里時,葉芝在回信中表明他支持西班牙革命,反對法西斯主義。葉芝的政治傾向非常曖昧。他不支持民主派,在晚年卻也有意疏遠納粹和法西斯主義。然而縱觀葉芝的一生,他從未真正接受或贊同過民主政治。同時,他深受所謂“優生運動”的影響。
進入晚年后,葉芝逐漸不再如中年時一樣直接觸及和政治相關的題材,而是開始以一種更加個人化的風格寫作。他開始為自己的家人兒女寫詩,有的時候則描繪自己關于時間流逝、逐漸衰老的經歷和心緒。收錄在他最后一部詩集中的作品《馬戲團動物的大逃亡》生動地表現了他晚期作品的靈感來源:“既然我的階梯已經消失,我必須平躺在那些階梯攀升的起點”。1929年之后,葉芝搬離了圖爾巴列利塔。盡管詩人一生中的很多回憶都在愛爾蘭國土之外,他還是于1932年在都柏林的近郊租了一間房子。晚年的葉芝非常高產,出版了許多詩集、戲劇和散文,許多著名的詩作都是在晚年寫成的,包括一生的顛峰之作《駛向拜占庭》。這首代表性的詩作體現了葉芝對古老而神秘的東方文明的向往。1934年,他和拉迪亞德·吉卜林共同獲得歌德堡詩歌獎。1938年,葉芝最后一次來到艾比劇院,觀賞他的劇作《煉獄》的首映式。同年,他出版了《威廉·巴特勒·葉芝的自傳》。
晚年的葉芝百病纏身,在妻子的陪伴下到法國休養。然而最終還是于1939年1月28日在法國曼頓的“快樂假日旅館”逝世。他的最后一首詩作是以亞瑟王傳說為主題的《黑塔》。逝世之后,葉芝起初被埋葬在羅克布羅恩。1948年9月,人們依照詩人的遺愿,將他的遺體移至他的故鄉斯萊果郡。他的墳墓后來成了斯萊果郡的一處引人注目的景點。他的墓志銘是詩人晚年作品《班磅礴山麓下》的最后一句:“投出冷眼,看生,看死,騎士,策馬向前!”葉芝生前曾說斯萊果是一生當中對他影響最深遠的地方,所以他的雕塑和紀念館也將地址選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