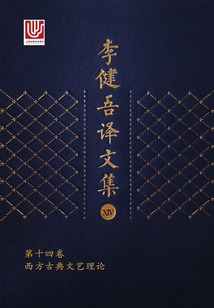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西方古典作家論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1](1)
試論嚴肅劇類(節選)(法)
博馬舍
……
所以說,嚴肅劇只能用既沒有彩飾,也沒有花環的樸實的風格來寫:它的全部的美麗應該來自內容、安排、對題材的興趣和題材的開展。它和自然本身一樣真實,因此,悲劇的格言和筆調,喜劇的諷刺和噱頭,對它是絕對不適用的;永遠沒有格言,除非它們寓于行動中。它的人物應該永遠以這種姿態出現,那就是,他們不需要用辭藻引起興趣,它的真正的說服力寓于情景之中,它唯一能用的色彩是語言;它和詩句中嚴格的停頓以及矯揉做作的韻腳是毫不相似的,而后面這些東西,詩人在詩體的戲劇中,費盡心機也不能使它們不被覺察。要使嚴肅戲劇達到人們有權要求它的那種真實,作者首先要注意的是使我在整個舞臺上,看不見演員的一切逗趣和戲劇布景,以便使我在整個戲的進行期間一刻也不會想到這些東西上去。因為,只含有默契的真實的詩體對話所引起的第一個效果難道不是使我的思想回到戲院中去,因而毀了作者企圖使我產生的一切幻想嗎?在萬戴爾克戲廳里,我完全忘記了布赫維爾和貝利扎爾[2],眼前只有善良的安東納和他那杰出的主人[3],而且我真正地和他們一起受感動。你們想,如果他們向我背誦的都是些詩句,那我還會這樣嗎?我不但會在人物身上看到演員,而且,更壞的是,每一個韻腳都會使我在演員身上看到詩人。于是,這個戲的如此可貴的真實性就全部煙消云散了;而這個如此真實,如此動人的安東納就會由于他那不自然的語言而顯得笨拙討厭,就好像是一個天真的農民,人們為了使他出落得自然而給他古怪地穿上華麗的仆役號衣。
我和狄德羅先生一樣,認為嚴肅戲劇應該用散文寫。我認為這種散文不應該有太多的修飾,而且,如果人們被迫在華麗和話力之間作選擇的話,前者切記應該從屬于后者。
論古典詩與浪漫詩
德·斯達爾夫人
為了區別從行吟詩人的歌詠發展起來的詩,從騎士制度和基督教出來的詩,“浪漫的”這個詞,新近被介紹到了德國。假如我們不承認異教和基督教、北方和南方、古代和中世紀、騎士制度和希臘與羅馬制度分占文學這塊領土的話。想以一種哲學觀點來評論古代鑒嘗和現代鑒嘗,我們也就決辦不到了。
“古典的”這個詞,我們有時當作“完美的”同義語。我現在用這個詞,又是一種涵義,那就是:把古典詩看成古人的詩。把浪漫詩看成和騎士傳統有相當關聯的詩,這種分法同樣適用于世界的兩個時代:基督教興起以前的時代和基督教興起以后的時代。
我們根據各種德國作品,還把古典詩比作雕刻,浪漫詩比作繪畫;總之,人類精神從拜物的宗教到崇靈的宗教,從自然到唯靈的進程,我們用了種種方式來說明它的特征。
拉丁國家中間最有教化的國家是法國,法國傾向于從希臘人和羅馬人那邊模仿來的古典詩。日耳曼國家中間最顯赫的國家是英國。英國喜歡浪漫與騎士詩,以有這一類杰作自豪。這兩類詩,哪一類值得特別稱許,我現在也不想作什么評判:關于這一點,指出鑒賞的多樣性不光來自偶然因素,也不光來自想象和思想的原始根源,也就夠了。
史詩和古人的悲劇有一種單純性質,這種性質和人們在這一時期與自然打成一片有關系,以為自己受命運支配,就像自然受必然所支配一樣。人不大思索,總是把他的靈魂的行動露在外頭;良心本身就用外在的事物來象征,復仇女神們的火炬,在罪人們的頭上,搖撼著疚心,在古代,事變起絕對作用;也就是到了現代,性格才占到更多的位置;左思右想的思維經常吞噬我們,就像禿鷲吞噬普羅米修斯一樣;古人的戶籍和身份,表現出來的關系,是清楚的、明顯的;這種思維和這種關系萬一到了一起的話,不像思維,倒像瘋狂了。
在藝術起始的階段,人在希臘從事的,只是一些孤立的雕像;組合是更后才形成的。我們即使說,當時任何藝術都沒有組合,也不見得就不正確。被表現的事物一個接連一個,像浮雕一樣,沒有配合、沒有任何種類的交錯。自然被人格化了;水仙住在溪澗里,木仙住在森林里;而自然同時也把人搶了過來,我們未嘗不可以說:他像急流、像閃電、像火山,因為使他行動的,是一種自己做不了主的沖動,這里沒有能改變他的行動的動機或者前后次序的思維。我們不妨說,古人的靈魂是有形體的。它的每一個動作全是強烈的、直接的、明確的。基督教培養出來的人心就兩樣了:現代人從基督教的懺悔中養成了不斷反省的習慣。
但是要想表明完全屬于內在的存在,就必須有大量錯綜復雜的事實。以種種形象來表現靈魂內的千變萬化。假如古人的單純還照樣控制著我們今天的美術,我們一方面得不到使古人不同于后人的原始力量,一方面還失去了我們的靈魂所能感受的親切與繁復的情緒。現代人的藝術的單純,很容易變冰冷、變抽象的,而古人的單純卻充滿了生命。榮譽和愛情、勇猛和憐憫是區別騎士的基督教的感情;靈魂的這些情況,只能通過危險、功績、戀愛、禍殃,總之,不斷作成畫面變化的浪漫興趣,才能讓人看清楚了。所以從許多觀點看來,浪漫詩里的藝術效果的根源是不同的:統治前者的是命運,統治后者的是上天;命運不看重人的感情,上天只憑感情判斷行動,命運既盲且聾,永遠和生人作對;上帝回答著我們的心的問話,統率著有條有理的布局,既然必須描寫命運的玩物或者這種布局,詩怎么會不創造一個性質不同的世界出來?
異教詩應當像外在的事物那樣單純、顯著;基督教詩需要虹的不和浮云混淆的彩色。古人的詩,作為藝術,更加純潔;現代人的詩讓人流下更多的眼淚。不過對于我們,問題不在古典詩與浪漫詩本身,而在古典詩的模擬與浪漫詩的感興。古人的文學,到了現代人身上,是一種移植文學;浪漫或者騎士文學,在我們這邊。土生土長,是我們的宗教和我們的制度讓它開花的,模擬古人的作家要遵守鑒賞的最嚴格的規則;因為不能參考他們本人的性格或者他們本人的回憶,古人的杰作所能適用的法則,他們也就非適應不可,雖然產生這些杰作的政治與宗教的環境完全變了。不過這些擬古詩,盡管完美,很少家喻戶曉的,因為它們一點也不結合本國人目前的需要。
在所有現代詩里,法國詩是最古典的,也是唯一沒有流傳到民間的詩,威尼斯的船夫唱著塔索[4]的詩句;各個階級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背得出卡爾德隆[5]和卡蒙斯[6]的詩行。莎士比亞在英國,得到了人民的稱道,也得到統治階級的稱道,歌德和畢爾格[7]的詩被譜成了樂章;從萊茵河岸到波羅的海。你聽見人在吟來唱去。我們和歐洲其他國家的有修養的人都稱道我們法國詩人;可是平民,甚至于市民,也完全不曉得他們,因為藝術在法國,不像在旁的國家那樣,是本土的土著,而藝術的美麗卻是在本土發展起來的。
有些法國批評家,認為日耳曼民族的文學,還停留在藝術的幼稚時期,這種意見完全錯誤,精通古人的語言和作品的人們,一定曉得他們采用或拋棄的文體的優、缺點,可是他們的性格、他們的習慣以及他們的理論,又引導他們喜愛以騎士的回憶和中世紀的奇異為基礎的文學,甚于喜愛建立在希臘神話基礎之上的文學,浪漫文學是唯一還有完美可能的文學,因為它把根扎在我們自己的土壤,是唯一能成長和重新向榮的文學:它表現我們的宗教;它追憶我們的歷史;它的根源是老而不古。
古典詩想感動我們,一定要通過異教的回憶;日耳曼人的詩是美術的基督教時代:它用我們個人的印象來感動我們:從它這里得來靈感的天才,立刻就打動我們的心,似乎把我們自己的生命召喚回來,就像召喚一個幽靈、那最強大與最可怖的幽靈一樣。
附志:這篇短論選自德·斯達爾(De Sta?l,1766—1817)夫人的《論德國》;它構成卷二第十一章。法國浪漫主義的形成,《論德國》這部書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從這篇短論可以看出她對希臘和羅馬文學缺乏足夠的認識。但是另一方面,她介紹了也肯定了日耳曼文學,給法國陳陳相因的文壇帶來了一新耳目的新的天地。伏爾泰介紹了英國,特別是莎士比亞和牛頓,但是很快就又否定了莎士比亞。古典主義的偏好和法國第一的自尊心阻礙了他。德·斯達爾夫人介紹北方文學的時候,不但有熱情,而且有獨到的見地,她繼續了十七世紀末葉的“古今之爭”,她站在“今”這方面:我們從這篇短論就體會出她的說法。同時她還具體地發揮了孟德斯鳩提出來的環境影響的說法:我們從這篇短論也可以明確這一點。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她提出“浪漫的”這個字樣,加以具體解釋,并因而和“古典的”對立,又進一步從“現代人”的立場,否定了對古人作品的模擬。當然她還站在宗教立場來說明她的觀點,這就難免顯出了武斷的情況。
《論德國》這部名著在1810年印好,但是拿破侖派人把印出來的書給銷毀了,同時也把她給驅逐出境了。1813年,書又在倫敦印行。
譯者
神秘的性質(外一篇)
夏多布里昂
生活里面沒有比神秘事物再美麗、再動人、再偉大的東西了。最美妙的感情就是那些朦朦朧朧激動我們的感情。廉恥心、堅貞的愛情、忠誠的友誼,充滿了秘密,我們不妨說,兩心相愛,就像是門敞開了一半一樣,言詞隱約,彼此照樣了解。天真不是別的,只是一種神圣的愚昧:難道天真不正是最難以言傳的神秘?童年之所以那樣幸福,就只因為什么也不知道;老年之所以那樣苦惱,就只因為什么也全知道;生之神秘結束,死之神秘開始,對老年來說,何嘗不是幸福。
感情假如是這樣的話,道德也是一樣的:最高的道德是那些直接從上帝那邊得來的道德,例如慈善,如同它們本源一樣,喜歡不被人看見。
從精神的關系出發,我們發現思想的樂趣也正在于秘密。秘密屬于一種非常神圣的性質,亞洲最早的人們只用記號說話。我們經常注意的是什么學問?是那永遠要我們猜測的學問,是那把我們的視線確定在無限的遠景的學問……
宇宙之中,一切被隱藏著,一切是不可知。人本身不就是一種奇怪的神秘。我們叫做存在的光閃,是從什么地方來的?又在什么樣的夜晚滅掉?上帝在我們生涯的兩端,通過兩個蒙著面紗的幽靈的形體,放下了生和死:前者產生出來我們生命的不可思議的同時,后者卻又急于把它吞噬了。
描寫詩
神話的最大的主要缺點,首先就是縮小自然,把真實從自然這邊攆走。關于這一事實,有一個抗辯不了的證據,就是我們所謂的“描寫”詩,古代是不知道的;就連歌詠自然的詩人們,例如赫西俄德[8],忒奧克里托斯[9]和維吉爾[10],照我們所了解的“描寫”的意思,就都沒有對自然作過描寫。關于工作、風俗,以及農村生活的幸福,他們確實給我們留下了一些悅目的畫幅;但是至于那些增加現代詩神財富的關于田野、四季、天空變化的圖畫,從他們的著作,我們就找不出幾行來。
不錯,這寥寥幾行詩,像他們作品的其余部分一樣,是很好的。荷馬描寫獨眼巨人的洞穴,沒有讓它遍地全是“丁香花”和“玫瑰花”;他像忒奧克里托斯一樣,在這里栽了幾棵“桂樹”和“長松”。[11]他在阿耳席諾屋斯的花園,詠到泉水潺潺,有用的樹木開花[12];他在別的地方,說起“風打著長滿無花果樹的山岡”;[13]他形容席爾賽的宮殿的煙,說它比樹林還要高。
維吉爾把同樣的真實寫進他的畫幅。他拿“和諧的”形容詞形容松樹,因為松樹輕輕擺動的時候,確實發出一種柔和的呻吟;在《農事詩》里面,浮云被比作風卷起來的羊毛團;[14]在《埃涅阿斯紀》里面,燕子在國王艾望德的茅廬底下啁唽,或者掠過宮殿的廊廡[15]。賀拉斯、[16]卡圖魯斯、[17]普羅佩爾提烏斯[18]、奧維德[19],也勾勒了一些自然景象;不過這永遠只是夢神喜愛的一片樹蔭涼,愛神走下來的一座山谷,海神在水仙胸懷安息的一道泉水……
我們決不能設想,像古人那樣敏感的人們,會缺乏眼睛看見自然,會缺乏才分描寫自然,假如不是有什么重大的原因使他們視而無睹的話。重大的原因就是神話。它給宇宙添了許多優雅的幽靈,從創造中抽去了它的嚴肅、它的偉大和它的寂寞。也只是基督教來了以后,才把這群山野的男妖女怪攆走,把安靜還給了洞穴,把冥思還給了樹林。在我們的宗教信仰的影響下,沙漠有了一種更憂郁、更廣漠、更崇高的特征;森林的穹隆越發高了;河流摔碎了它們的小瓶子,水不再從小瓶子流出來了,[20]而是從山頂的深淵流出來:真正的上帝,在重回到他的作品中的時候,把他的浩瀚給了自然。
附記:這兩節文字,選自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84)的《基督教真諦》(Le Génie du christianisme,1802):第一節見于卷一第二章;第二節見于卷四第一章。《基督教真諦》是一部對法國浪漫主義運動起了很大影響的書。他的目的是為了把天主教再在大革命后的法國建立起來。他的精神完全是反動的。但是另一方面,他歌頌自然,重視風景描寫,同時宣傳個人感情(通過他的小說,特別是《勒內》與《阿達拉》,最先都收在《基督教真諦》里面,后來才另出單行本),宣泄個人的苦悶和憂郁,尤其是風格清麗,事實上打擊了古典主義百五十年來的統治。
他稱道神秘,不僅企圖否定古典主義的唯理主張,而且企圖反駁百科全書派的唯物觀點。奇怪的是,他對后來風起云涌的浪漫主義運動并不同情。他給法國文學帶來了“世紀病”,可是他把責任推給了拜倫(見于他的《論英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