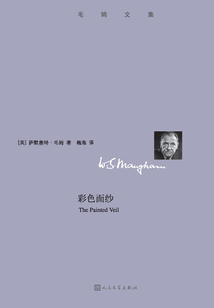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前言
威廉·薩默塞特·毛姆(一八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法國巴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逝世于法國尼斯),英國小說家和劇作家,著述甚豐,作品以文風樸素、背景廣闊和對人性的深刻剖析而著稱。
毛姆十歲時,因雙親先后故去而被送回了英國,在叔父家寄居,并在英國接受教育。稍長,曾到過德國海德堡,住了約一年,后入倫敦圣托馬斯醫院學醫,于一八九七年畢業。他把自己在倫敦貧民區行醫期間的見聞經歷寫進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蘭貝斯的麗莎》(1897),發表后頗受歡迎,遂棄醫專事寫作。曾游歷西班牙和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先是在紅十字會和救護團隊里服務,后來又從事過情報工作,到過瑞士和俄羅斯。戰后曾在遠東和東南亞旅行。一九二八年他在法國尼斯的菲拉海角購買了一幢別墅,并在那里定居。
毛姆最初成名于戲劇創作,一九〇八年他的四部劇本同時在倫敦上演,轟動一時,一生共創作了約三十部劇本,但是他的主要文學成就是在小說創作方面,共發表了二十部長篇小說和一百多篇短篇小說。他的小說結構嚴謹,情節曲折,剪裁得體,語言簡練。他的最為著名的四部長篇是:《人性的枷鎖》(1915)——這部半自傳性質的小說,敘述了一位年輕的醫科學生的痛苦的成長經歷;《月亮與六便士》(1919)——回顧了一位離經叛道的英國畫家(據信是以法國印象派畫家保羅·高更為原型)的藝術人生;《尋歡作樂》(1930)——刻畫了一位文壇巨匠(以托馬斯·哈代為藍本)及其周圍形形色色的人物;《刀鋒》(1944)——講述了一位年輕的美國軍人探求人生真諦的故事。毛姆的短篇創作也深受讀者喜愛,許多描寫歐洲人在異國環境中的矛盾沖突的短篇都曾引起過強烈的反響。他的短篇創作風格接近于莫泊桑。
《彩色面紗》最初分別在美國的《時尚》雜志(Cosmopolitan)(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和英國的《納什雜志》(Nash's Magazine)(一九二五年五月)上開始連載時,毛姆已經是五十歲出頭的人了,而小說的創作靈感卻是他在三十年前,從但丁《神曲》的煉獄篇的詩句中獲得的,一位意大利女人給他講述了詩句背后的那個哀婉的故事,從而激發了他的想象。他在小說的序言里寫道:“我在心里反復地琢磨它,在其后的許多年里,我也總是不時地將它翻出來仔細地推敲上兩三天……我把它設想成了一個現代故事……”但是,由于他想不出一個環境,能讓這個故事合情合理地發生,也由于這個故事只不過是縈繞在他腦際的許多題材當中的一個而已,時間一長,他就把它給忘記了。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從一九一九年底至一九二〇年三月,已值盛年的毛姆,到中國做了一次長途旅行,這才終于為那個潛藏心中近三十年的故事,找到了一個合適的環境。數年后他便推出了這部篇幅不大卻內涵豐富的引人入勝的小說。
凱蒂·加斯廷嫁給了她既不喜歡也不了解的細菌學家沃爾特·費恩,并同他一起來到殖民地香港。在香港,凱蒂跟風度翩翩的助理輔政司查利·湯森,一位有婦之夫,發生了曖昧的關系。沃爾特在發現了妻子的不貞之后,自愿申請前往中國內地霍亂流行的梅潭府地區行醫,并給妻子下了最后通牒:要么跟湯森結婚,要么隨他一道去梅潭府。湯森為了自己的前程,拒絕跟凱蒂結婚。走投無路的凱蒂,只得隨丈夫前往疫區,想就此了卻一生。在梅潭府,沃爾特投入了日以繼夜的防止疫情蔓延和救治病人的工作。凱蒂則結識了英國海關官員沃丁頓和當地修道院里的一群法國修女。修女們冒著生命危險,義無反顧地救助孤兒和患者。在她們的無私精神的感召下,凱蒂也加入了她們的行列,開始了人生的轉變。得知凱蒂有了身孕,沃爾特軟化了對妻子的態度,并催促她離開梅潭府,雖然他并不相信自己是孩子的父親。不久,沃爾特即死于霍亂。凱蒂只身一人返回香港后,在完全違背自己心愿的情況下,竟再次委身于查利·湯森。帶著深深的自責,凱蒂回到了英國,并在途中接到了母親去世的電報。最后,凱蒂打算與父親相依為命,并隨他前往巴哈馬群島。
這是一部脈絡并不復雜,卻讓人沉湎其中,不忍釋手,讀時常常會掩卷深思,讀后仍然要細細回味的小說。書中涉及的事物似乎都不那么簡單,情節從一個高潮進展到另一個高潮,正如連載小說所可以預期的那樣。然而書中的人物描寫才是最耐人尋味的。你或許還摸不準它的男女主人公是否值得你去喜愛,究竟誰更正面一些,卻已經不由自主地跟隨著他們走過了這段形象鮮明的文學旅程了。
在小說的前半部分,女主人公凱蒂的形象決不能用正面來形容。然而在她輕佻放蕩、用情不專的行為背后,卻隱藏著追求自由的沖動。凱蒂先是想要擺脫專橫跋扈的母親而草草地嫁給了不愛的人,然后又因為對婚后生活的厭倦而同一位自私自利、慣于玩弄女性的男人發生了不正當的關系,接著,又因為奸情敗露走投無路,踏上了前往霍亂疫區的死亡之旅。當她因丈夫死亡而結束了那段煉獄般的生活,只身一人返回香港的途中,作者加進了這樣一段文字:
“自由!正是這個念頭在她的心中歌唱……自由!不僅掙脫了煩惱的束縛,而且從令她抑郁寡歡的伴侶關系中解脫出來;不僅擺脫了死亡的威脅,而且也甩開了使她墮落的愛情。她從一切精神枷鎖中解放了出來,成了自由自在的靈魂。有了自由,她就有了勇氣,無論今后發生什么,她都能從容地面對。”
有趣的是,這樣的內涵,竟使這部小說在近幾十年里受到了女權主義者的青睞。小說在結尾處借凱蒂之口,告誡母親們要教育自己的女兒切莫重犯前輩的錯誤,要珍惜真正的精神自由,決不能因為物欲而出賣自己的自由,淪為男性的玩物。
人性的矛盾,是毛姆經常在小說里探索的一個主題。在這部小說里,善與惡的對立不僅存在于人物之間,而且交織在每個人物的性格里。一個人的善惡表現之間并沒有什么難于跨越的鴻溝,有時甚至以相反的面目出現。人物之間的愛恨情仇,也往往只是一線之隔。譬如,生性靦腆、舉止木訥的沃爾特對凱蒂一見鐘情,愛她“超過了世上的一切”,婚后對她也是“極為體貼,盡心盡力想使她過得舒適,……誰也不能像他那樣溫柔或體貼周到”。但是,當他發現了妻子的不貞之后,卻老謀深算地策劃了殘忍的報復方式,帶她到霍亂肆虐的梅潭府,想要置她于死地。手段之惡更甚于妻子的不貞,與他通常的為人大相徑庭。可是,來到梅潭府后,不僅他漸漸地平息了憤怒,妻子也從厄運的夢魘中掙脫了出來。沃爾特最終原諒了凱蒂,并把他的愛心轉而傾注到了不幸的病人們的身上。凱蒂也在與修女們朝夕相處、共同照料孤兒的過程中,開始了人生的轉變。然而,看似新生的凱蒂,回到香港后,竟再次投入了湯森的懷抱,惡又一次抬起頭來,雖然她隨即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責。你不禁會驚異于作者看待人性的冷峻的目光。對于善良的天性,就其廣度和深度而言,毛姆都是持懷疑或保留態度的。
這部小說的書名取自詩人雪萊的一首十四行詩。詩人認為生活就是一幅彩色的面紗,上面所畫的都是些人們樂于相信的不真實的東西。小說借用“面紗”來暗示那些難于看透的人和事,這在小說中可說是俯拾皆是,這恐怕就是它讀起來頗費思量的原因吧。女主人公生活態度的轉變,是作者著墨最多,同時也是書中最發人深思的部分,其中貫穿著對生活真諦或人生意義的探索。命運將凱蒂帶到了霍亂肆虐的梅潭府,在那里,她一方面目睹了大量的死亡:修女,士兵,孤兒和當地的民眾,另一方面也目睹了修女們同死亡搏斗,忘我地救助和照料孤兒和病人們的英勇行為,心靈受到了極大的震動,并加入到照料孤兒的工作中去。正是在這個人間“煉獄”里,她開始了靈魂的凈化。她改變了對丈夫的態度,看清了自己的自私、輕浮和淺薄,開始懂得生活有遠比尋歡作樂重要得多的豐富的內容,明白了“愛別人,從而也為別人所愛”的道理,并為自己對別人有用而高興。這是她人生的轉折點,真正的轉變一旦開始,便會順著它本身的邏輯向前發展。她說:“我一直在尋找一樣東西,卻又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弄清它對我來說非常重要,而且一旦我弄清楚了,那么一切就會大不相同了。”她在尋找什么呢?小說并沒有明說。但是,她一直視那些圣徒般的修女們為榜樣,“她們放棄了一切,她們的家,她們的祖國、愛情、孩子和自由,……獻身于一種充滿了犧牲、貧困、絕對服從、勞累和祈禱的生活。”她們之所以能這樣,是因為她們相信這會讓她們獲得死后的永生。凱蒂為無法擁有這樣的信仰而苦惱,而沃丁頓則對修女們的信仰深表懷疑:“假如根本就沒有永生呢?想想,如果死亡實際上就是一切的結束,那將意味著什么呢?她們放棄了一切卻一無所獲。她們受騙了……”他又說:“她們所追求的僅僅是虛構的幻想……其實……生活本身就是美麗的。我有個想法,我們之所以能夠尊重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而不感到失望,唯一的原因,就是人們能從一片混沌中不斷地創造出美來。他們繪畫、創作音樂、寫書并開創生活。而在這一切當中,最為豐富的美就是美好的生活。”這些對凱蒂來說是過于深奧了。凱蒂未能為已經轉折的人生尋找到精神上的支撐點,她最終也沒能掀開這層神秘的“面紗”。
毫無保留地向讀者推薦這本書。書如其名,就請讀者親自來掀開這幅彩色的面紗吧。
梅海
二〇一五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