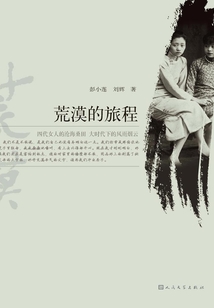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一:讀這樣一部書
陳思和
《荒漠的旅程》付梓,彭小蓮十分堅決地告訴我,這不是一部長篇小說,它的內容絕不是虛構的。她稱它是一部“延續性紀實短篇集”。可“紀實短篇集”又是什么意思?紀實性的短篇小說?還是短篇的紀實體文章?我帶著疑團開始閱讀——眼睛一接觸這樣的文字,我就明白了。顯然,這已經超越了小蓮的前作《他們的歲月》。這回不僅是一群“胡風分子”的特殊遭遇,書中人物的背景更加復雜,時間的跨度更加久遠,“他們”的歲月又夾雜了“我們”一代的歲月,四代人漫漫跋涉于無邊荒漠。歲月太殘酷,時間太漫長,題材太浩大,歷程太復雜,以這樣的大題材與本書的篇幅作對比,這些文字只能說是一個“短篇集”,但這是長途跋涉中人們留下的血滴汗珠,蘊含了受難者身體發出的難聞的生命氣味,撒落在歷史荒漠上,然而“它”又是“延續地”撒落、撒落,連綴成了這樣一本用血汗生命譜寫的書。
記得何滿子先生生前在為彭小蓮的《他們的歲月》作序時,也說到了文體的問題。他說:“很難從文體論的概念來為這本書定性:家史?人物傳記?專題性的長篇報告文學?電影故事的文本?或是人們常說卻于理不能認同的所謂‘紀實小說’?都像,都不全像。我只能說,這是一部敘事體的詰問人生的書。”如果說,《他們的歲月》是彭小蓮以其父親的遭遇追問了1955年“胡風冤案”的悲劇形成與可怕后果,那么,《荒漠的旅程》的兩位作者——彭小蓮和劉輝,則以更廣闊的社會背景和作家劉溪一家的前世今生,對著百年中國歷史提出了嚴峻的詰問:百年來的中國人是怎么過日子的?一代代中國人——從晚清算起:洋務派傅冰之算第一代,留日醫學博士吳序新以及比他小十多歲的羅人鵬、羅人鸞算第二代,追求革命并成為“革命”隊伍一分子的劉溪和吳頤、吳進以及蘇銘適等是第三代,而敘事人彭小蓮、“小鶯”(劉輝)、“小鶯”丈夫秦孝章、姍姍等是第四代,他們是受盡蹂躪而出國逃亡的一代;至于第五代——晶晶,則已經成為一個不怎么會說中文的洋學生,專業是美國文學,成為美國的第二代移民,下一輪的歷史將在大洋彼岸開始輪回了。當我們打開任何一本歷史教科書,洋務派、留學生、中共革命者,都是時代的驕子,他們的人生實踐,成為優秀的中國知識精英百年來前赴后繼的一條拯救國民于千年古國昏睡中的康莊大道,輝煌的理想也曾一直鼓舞著人們透過一時籠罩的滅頂之災而期盼永恒的未來之光。但是,最終是什么力量,什么魔怪精靈,把他們的后裔們推向海外,一如隨風飄去的飛花轉蓬,無根可依?這是歷史的悖論,是荒誕的時間之流所映像的百年中國之命運,也是當代中國人萬不可輕易放過的世紀之問。
當然,這樣的莊嚴之問,可以用更宏大的篇幅精心構造史詩般的文學巨著來探尋,也可以用多卷本的大河小說和眾多的藝術形象來表達——當代文學創作中并不缺乏這一類的主題及其表現。而《荒漠的旅程》沒有走這樣一條創作之路,它的兩位作者,利用的是自身的家史和經歷,以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真實家史為見證手段,從一個社會細胞家庭、家族的演變史里揭示啟人深思的人生問題。因為是家史的整理,就來不得虛構,書中的敘事人也就成了故事的當事人,“小鶯”(敘事人“我”)對家族史的探尋,成為整個敘事的起點。“小鶯”的敘事是從1989年4月申請赴美探親,攜女出國后又遭丈夫冷遇開始寫起,敘事起點是個人的命運處在一個糾結點上——婚姻、家庭、國家的命運都處在臨界點上,飛花轉蓬成了這一代人的新的命運象征。如果說,“文革”時期家破人亡、插隊時期漂泊天涯,都還是來自外在的災難性力量的推動,而這一次,則是“小鶯”自己的事情,需要自己來擔當。按照時間的推算,“小鶯”應該是一個工農兵大學生,1978年分配在上海一家中學擔任歷史老師,丈夫秦孝章似乎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后的大學生,華師大畢業后出國深造,他們應該在1982年前后結婚,有一個五歲的女兒。也就是說,本來她已經獲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職業、家庭和生活的權利。而這一次出國和異地定居,是申請者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但是這個選擇的背后,又關聯著敘事人對這一份來之不易的穩定生活的極度不安全感,而事實也證明,這種不安全的預感不是空穴來風。于是,可怕的家史回憶與此時此地的境遇就聯系起來了。我不了解作者劉輝,但從文本上看,這個以劉溪家庭為中心的家史,應該是劉輝的家庭故事,劉輝即“小鶯”。而有相似身份、毀家更早的彭小蓮參與了這份血淚家史的對話、整理和書寫。看得出來,書中許多感慨、議論與《他們的歲月》《美麗上海》里的非常相似,屬于彭小蓮式的激憤、牢騷和思考。
這份家史涉及了多方面的內容,從傅冰之到“小鶯”整整四代人血脈相傳的延續性歷史,但是因為出于私人的回憶,或者是聽者的轉述,很多隱私就不得其詳,全書三十幾人出場,真正能夠勾勒出來的還是外公吳序新、小外婆羅人鸞、大姨吳頤、母親吳進、父親劉溪等等,關鍵人物還配了照片,印證家史的真實性。
從全書的敘事來看,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劉溪家庭及其妻子吳進的上代家庭的歷史回憶,另一部分則是當事人“小鶯”出國后的個人經歷。這兩部分不是按章節分前后敘述,而是穿插在一起交替敘述。能夠使這兩部分緊緊地融為一體的,除了對家史的連綴以外,還有一條更為重要的線索,也是作品隱藏于家史敘事之內的最感人的部分,那就是人類現代社會中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她們內心世界被關注的程度。敘事中從傅敏、羅人鵬等女性的故事開始,她們幾乎都是在現代社會觀念的照耀下,經歷了從追求自由戀愛到充當賢妻良母,最終又都以難言之痛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的過程;這還不是最重要的,由于敘事者的故事是從異國投親、丈夫有外遇、幾乎遭到遺棄開始的,又是以弘揚了忍耐的傳統美德,維持了家庭的圓滿為終止。本來這條線索可以深入挖掘,從這個現代女性內心深處的靈魂顫音及其前輩婦女百年命運的傳承中獲得一些新的啟迪。可惜這一點被敘述者有意忽略了,反倒是美國女性妮娜的飽滿形象,給作品增添了亮色。
如果我們從更為宏觀的中華民族苦難史著眼,百年歷史,無論苦難還是輝煌,都算不了什么。彈指一揮間,歷史照樣轟然向前,大國崛起,在當下世界凜然可見;但落實到一個家族或者幾代人的個體命運,他們是有權利提出這個詰問:為什么在這百年中,優秀者都不免悲慘命運,忠誠者都會遍體鱗傷,信仰者都死有余辜?!始作俑者,其無后乎?這些與國民事業的奠基者血肉相連的大是大非沒有得到澄清,與國家權力捆綁在一起的巨奸兇頑沒有徹底清算,民族的優秀者不能揚眉吐氣,那么,歷史的陰影永遠會籠罩在國民的心頭,讓集體吞下藏污納垢的苦水,讓罪惡、腐敗和卑鄙隱藏在表層的巍峨之下;那么,終有一天,樓起了也會坍塌,大國也會成為冰山。歷史的教訓,如是我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