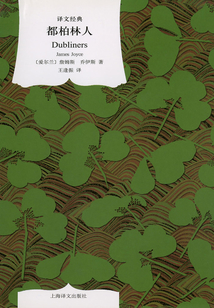
都柏林人(譯文經(jīng)典)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前言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 1882—1941)是愛爾蘭作家,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大師,1882年2月2日生于都柏林郊區(qū)拉斯加爾,1941年1月13日在瑞士蘇黎士逝世。
喬伊斯一生坎坷多舛。他生長在一個(gè)天主教家庭,父親是收稅官,起初家境相當(dāng)舒適,但由于父親熱衷于政治,退休后又染上酒癮,家境開始衰敗,喬伊斯不得不一度輟學(xué),后來進(jìn)入一所免費(fèi)的耶穌會走讀學(xué)校。1898年,他進(jìn)入都柏林大學(xué)學(xué)習(xí),在那里他學(xué)習(xí)多種外語,以便閱讀歐洲大陸國家的文學(xué)作品。1902年大學(xué)畢業(yè)后,他結(jié)識了愛爾蘭文學(xué)復(fù)興運(yùn)動的核心人物巴·葉芝、格雷戈里夫人、喬治·莫爾、約·米·辛格等人,但他與他們的關(guān)系并不融洽,觀點(diǎn)也不一致,后來甚至強(qiáng)烈地反對愛爾蘭文學(xué)復(fù)興運(yùn)動,指責(zé)葉芝迎合低級趣味。此后他離開愛爾蘭到巴黎,以教英文謀生。不久,他母親病危,他又回到愛爾蘭。其間他愛上了愛爾蘭鄉(xiāng)村姑娘娜拉·約瑟夫·巴納克爾。1904年,他們在朋友的資助下私奔,去到巴黎,但一直到1931年才正式結(jié)婚。他們在歐洲大陸的生活十分艱辛,輾轉(zhuǎn)于法國和瑞士,沒有可靠的職業(yè)。1905年他們到意大利投奔在那里教書的弟弟,靠弟弟的幫助在那里安頓下來。但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1915年喬伊斯一家又被迫離開意大利,遷往瑞士的蘇黎士。由于生活的窘迫,喬伊斯經(jīng)常醉飲,并且染上了濕熱病,視力也日漸衰退,但他一直堅(jiān)持寫作。他一生寫出了四部現(xiàn)代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都柏林人》、《一個(gè)青年藝術(shù)家的畫像》,以及驚世駭俗的巨著《尤利西斯》和《為芬尼根守靈》。
一般說,大部分短篇小說集都是選收多種題材的故事,但《都柏林人》與眾不同,從一開始它就被構(gòu)想為一本有機(jī)的整體,其中的故事通過題材、風(fēng)格、技巧和主題相互連接在一起。正如喬伊斯在1906年5月5日致格蘭特·理查茲的信中所說:“我的意圖是一章寫我國的道德歷史,我選擇了都柏林作為地點(diǎn),因?yàn)檫@個(gè)城市處于麻木狀態(tài)的核心。我試圖從四個(gè)方面把它呈現(xiàn)給無動于衷的公眾:童年,青年,成年,以及公共生活。故事按照這個(gè)順序安排。大部分都采取審慎的平民詞語的風(fēng)格……”[1]
正是由于《都柏林人》的內(nèi)容和特殊寫法,《都柏林人》的經(jīng)歷十分坎坷,拖了好幾年才得以出版。大約1905年,倫敦出版商格蘭特·理查德先生接受了《都柏林人》,但他把書稿扣壓一年之后又退給了喬伊斯。后來書稿交給了都柏林的出版商毛瑟爾先生,他與喬伊斯簽訂合同,約定1910年9月之前出版該書。但出版時(shí)間一拖再拖。后來毛瑟爾先生要求喬伊斯修改《委員會辦公室里的常青節(jié)》中的一些段落。喬伊斯不情愿地進(jìn)行了修改,然而仍然拖著沒有出版。那時(shí)喬伊斯住在意大利,他專程到都柏林與出版商協(xié)商該書的出版事宜。1912年,書稿的清樣印了出來。
據(jù)他的朋友帕德雷克·考勒姆說,當(dāng)時(shí)他和喬伊斯去見毛瑟爾的經(jīng)理,經(jīng)理說:小說里公共的房子用了私人房屋主人的名字。喬伊斯提出和經(jīng)理一起去問房主人是否反對在書里用他們的名字,但經(jīng)理拒絕了,并說《委員會辦公室里的常青節(jié)》談到國王愛德華七世時(shí)所用的詞語冒犯了許多都柏林人,如果小說出版會引起他們的抗議行動——這是拖延出版的又一個(gè)原因。雖然喬伊斯提出作某些修改,但經(jīng)理卻要求他完全刪除某些小說。最后竟宣稱他們不會出版《都柏林人》。
考勒姆去找一個(gè)律師,也是喬伊斯大學(xué)時(shí)的朋友,問他是否可以使出版商照合同辦事。律師說,在都柏林無法補(bǔ)救,喬伊斯也得不到任何賠償。法官會認(rèn)為《都柏林人》是一本不道德的、犯眾怒的書,因而會不追究出版商的違約行為。于是喬伊斯給出版商寫了一封信,提出他們可以以任何他們滿意的形式出版該書,但他得到的回答是:他們已經(jīng)拆了鉛版,毀了已經(jīng)印出的清樣。喬伊斯別無選擇,只好帶著留下的唯一一本《都柏林人》的清樣,離開了都柏林。
究竟為什么出版商拒絕出版這本已經(jīng)簽約出版的書呢?出版商為什么拆了鉛版、毀掉清樣?人們可以有各種猜測,例如喬伊斯可能有什么仇人暗中操縱;或者天主教的都柏林覺得書里描寫的事件和刻畫的人物觸犯了他們,使他們憤怒,因而迫使出版商放棄這本書;或者出版商覺得這本書有損他們的名聲,等等。無論如何,《都柏林人》最終未能在都柏林出版。大約兩年以后,曾經(jīng)接受爾后退稿的倫敦出版商格蘭特·理查德先生才出版了這本書。
在《都柏林人》之前,喬伊斯出版了詩集《室內(nèi)樂》,后來又先后出版了小說《一個(gè)青年藝術(shù)家的畫像》、戲劇《流亡者》和劃時(shí)代的小說《尤利西斯》。研究者發(fā)現(xiàn),《都柏林人》和所有這些作品都存在著聯(lián)系。《都柏林人》里的前三個(gè)故事顯然出于個(gè)人的記憶,它們可能是從《一個(gè)青年藝術(shù)家的畫像》初稿里剪取的事件;在《阿拉比》里,男孩走過燈光搖曳的街道,不時(shí)受到醉漢和討價(jià)還價(jià)女人的干擾,覺得自己仿佛拿著圣餐杯安全地穿過一群敵人——這個(gè)男孩肯定就是小說《畫像》里的斯蒂芬·第達(dá)勒斯。最后一個(gè)故事《死者》里的加布里埃爾·康洛伊,通過另一個(gè)男人對他妻子的影響提出問題,明顯與《流亡者》里的主人公相似。如果把這四個(gè)故事從《都柏林人》里抽出來,那么剩下的其他故事就都與《尤利西斯》相關(guān),后者塑造的許多人物都曾在《都柏林人》里出現(xiàn),例如卡寧漢姆、郝洛漢、萊恩漢姆和奧馬登·勃克先生等。這種聯(lián)系并不奇怪,因?yàn)榘凑諉桃了沟淖畛跤?jì)劃,布魯姆的一天(《尤利西斯》的主題)也是《都柏林人》里的一篇故事。
年輕時(shí)的喬伊斯對都柏林人的兩個(gè)獨(dú)特的方面非常了解:一個(gè)方面是他們愛去酒吧;另一個(gè)方面是關(guān)于他們的政治。另外他也了解一個(gè)不太典型的方面,即都柏林的音樂。喬伊斯的父親在都柏林算是個(gè)著名的人物,他的社交活動使喬伊斯有機(jī)會接觸各種各樣的人。老喬伊斯先生在帕奈爾時(shí)期曾介入相關(guān)的改革;因此幼年的喬伊斯經(jīng)常聽到憤怒和哀傷的聲音,因?yàn)榕聊螤柸ナ懒耍S多追隨者背離了他。喬伊斯九歲的時(shí)候,寫了第一篇文章《還有你,希利!》,這是一篇政治譴責(zé)文章,矛頭直指當(dāng)時(shí)一個(gè)著名的政客,他背叛了帕奈爾。他父親的一些老朋友認(rèn)為,那篇文章是喬伊斯最好的文學(xué)作品,而對他后來的作品感到哀傷。
在《都柏林人》里,《委員會辦公室里的常青節(jié)》是一篇非常典型的故事。一些人多少有些隨意性地匯聚在一間凄涼的辦公室里;他們的行為顯得有點(diǎn)荒誕,其中一個(gè)應(yīng)邀朗誦一首他幾年前寫的一首詩——《帕奈爾之死,1891年10月6日》。詩有些業(yè)余,修辭也都是常見的,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透過這首舊詩卻傳遞出真實(shí)的悲哀和真正的忠誠。詩念完之后,人們對作者作了幾句評論,然后故事就結(jié)束了。讀者可能覺得與他們完全無關(guān),但同時(shí)也會覺得作者了解事件的所有含義,而且完全是為讀者寫的。他在寫這首詩之前仿佛進(jìn)入了海恩斯的心里。
“你覺得這詩怎么樣,克羅夫頓?”亨奇先生叫道,“難道不好嗎?你說什么?”
克羅夫頓先生說這是一篇絕好的作品。
如果喬伊斯讓克羅夫頓先生自己說這些贊美的話,那么他就冤枉了這位紳士善良的沉默。因?yàn)榭肆_夫特先生曾為保守派拉選票,他必然覺得詩里有某種叛逆的色彩。然而他是個(gè)普通的人,在那種場合里他只會寬容。“克羅夫頓先生說這是一篇絕好的作品。”這句話使人感覺到他的超然的態(tài)度。這種超然的情調(diào)可以說是《都柏林人》的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
在《都柏林人》的大部分小說里,喬伊斯都使讀者通過他的目光來觀察事件而不作任何評論。因此讀者在這些故事里總感到一種疏離感,仿佛他要通過一系列的報(bào)道來說明都柏林的生活,就像一個(gè)注重科學(xué)性的歷史學(xué)家描繪事件那樣。
不過《死者》的寫法不同。開頭三篇(《姊妹們》、《一次遭遇》和《阿拉比》)根據(jù)記憶而寫,也沒有這種疏離感或冷漠。但大部分故事都有。其中有三篇以女人為主要人物,即《伊芙琳》、《泥土》和《母親》。《母親》的寫法與其他關(guān)于男人的故事相似,也有冷漠的色彩。但《伊芙琳》和《泥土》里卻充滿了感情,喬伊斯對伊芙琳的命運(yùn)非常同情,對《泥土》里瑪麗亞的性格也多有崇敬。兩個(gè)女人都是思想單純,恪守常規(guī),待人誠懇。
《都柏林人》里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孤獨(dú)寂寞、互不相關(guān)的人。他們大多生活在狹小的空間里,但又以某種文雅的態(tài)度面對世界。有些人物的故事令人難忘,因?yàn)樗麄兛吹搅撕诎档纳钐帯?
死亡是《都柏林人》最重要的一個(gè)主題。最后一篇故事是《死者》,但死者也出現(xiàn)在第一篇故事里,《姊妹們》里的男孩遇到了他的鄰居老牧師的死亡:老人躺在那里,死了,對這個(gè)男孩變成了一個(gè)活的不可思議的人。《伊芙琳》里的伊芙琳不斷憶起她死去的母親。《泥土》里對瑪麗亞隱蔽的預(yù)兆其實(shí)就是她死亡的預(yù)兆。在《痛苦的事件》里,杜菲先生拒絕接受的一個(gè)女人死亡的消息,不斷在腦海里浮現(xiàn)并使他孤獨(dú)的生活更加寂寞。《委員會辦公室里的常青節(jié)》通篇圍繞著死去的帕奈爾展開。而在《死者》里,一個(gè)不知道是誰的男人,通過一首歌從死者的回憶,使一個(gè)丈夫意識到他妻子生活中有一部分他不能參與。實(shí)際上,在《都柏林人》里,最令人難忘的是那些被死亡感動的人的故事。因此最后一個(gè)故事結(jié)尾的那段話,帶有一種安魂曲的音樂感:
幾聲輕輕拍打玻璃的聲音使他轉(zhuǎn)過身面向窗戶。又開始下雪了。他睡意蒙眬地望著雪花,銀白和灰暗的雪花在燈光的襯托下斜斜地飄落。時(shí)間已到他出發(fā)西行的時(shí)候。是的,報(bào)紙是對的:整個(gè)愛爾蘭都在下雪。雪落在陰晦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沒有樹木的山丘上,輕輕地落在艾倫沼地上,再往西,輕輕地落進(jìn)山農(nóng)河面洶涌澎湃的黑浪之中。它也落在山丘上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一個(gè)角落,邁克爾·福瑞就埋在那里。它飄落下來,厚厚地堆積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積在小門一根根柵欄的尖頂上,堆積在光禿禿的荊棘叢上。他聽著雪花隱隱約約地飄落,慢慢地睡著了,雪花穿過宇宙輕輕地落下,就像他們的結(jié)局似的,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的身上。
總起來看,《都柏林人》可以說是由十五個(gè)故事組成的一個(gè)整體,它反映了都柏林不同層面的生活,在寫作方法上具有以下幾個(gè)突出的特點(diǎn):第一,它集中使用某些詞匯,例如“徒勞”、“無用”、“厭倦”、“絕望”等在多個(gè)故事里反復(fù)出現(xiàn),其目的是使讀者不知不覺地感受到每一個(gè)故事是普通人的道德構(gòu)成。第二,以“混亂”表示癱瘓,每當(dāng)人物不得不面對選擇某種積極生活的關(guān)鍵時(shí)刻,他們就變得不知所措,像嚇壞的兔子一樣靜止不動。第三,以單色調(diào)的散文風(fēng)格象征都柏林單調(diào)乏味的生活,產(chǎn)生出黑白照片的效果,但并不是一種單純懷舊的風(fēng)格。第四,故事的情節(jié)都是瑣事,人物是一種導(dǎo)致癱瘓的體制的受害者,而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會以微妙地改變了目光觀察細(xì)小的事件。第五,故意破壞讀者通常期望的“開始、中間和結(jié)束”的順序,但不是采取蒙太奇式的編織方式,而是依靠在讀者記憶中揮之不去的轉(zhuǎn)折點(diǎn)。
當(dāng)然,與所有經(jīng)典名著一樣,《都柏林人》為讀者提供了充分的解讀空間。上面的一些看法只是一己之見,唯一的希望是它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這次《都柏林人》的出版得到譯文出版社領(lǐng)導(dǎo)和馮濤編輯的大力支持,在此謹(jǐn)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翻譯永遠(yuǎn)難以達(dá)到至善至美,總有需要改進(jìn)甚或疏誤的地方,因此懇切希望讀者提出寶貴的批評和建議。
王逢振
2010年盛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