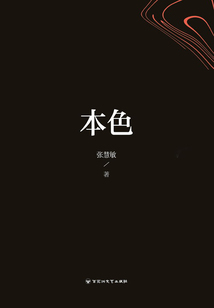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隨遇隨緣(代序)
近日讀周作人,敬仰之至。知堂老人的許多話、不少心境,肺腑如己出。想象中好似能觸摸到老人那份寂寥、落寞之痛。這里特記下一段,是周作人論及石川啄木詩歌,突然橫插一段心情:“我這樣想著,在那秒針走了一圈的期間,凝然的坐著,我于是覺得我的心漸漸的陰暗起來了。——我所感到不便的,不僅是將一首歌寫作一行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現今能夠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過是這桌上的擺鐘石硯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類罷了。說起來,原是無可無不可的那些事情罷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種種的東西,我豈不是連一個指頭都不能觸它一下么?不但如此,除卻對于它們忍從屈服,繼續的過那悲慘的二重生活以外,豈不是更沒有別的生于此世的方法么?我自己也用了種種的話對自己試為辯解,但是我的生活總是現在的家族制度、階級制度、資本制度、知識買賣制度的犧牲。我轉過眼來,看見像死人似的被拋在席上的一個木偶。歌也是我的悲哀的玩具罷了。”能托情以具,也算得一人生態度吧,我們將如此堅持下去。
臨近清明,算是對知堂老人的一個懷念。
周作人談清明有力作《故鄉的野菜》,是這篇文啟示出我的“隨遇隨緣”。一如開篇:“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于我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情分,只因釣于斯游于斯的關系,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我昨日念及波士頓的老房東一樣,雖然不是親戚,更不同國籍、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但是,回想起異國他鄉的清教徒時,滿懷感念曾獲得的許多布施。我的矛盾和復雜性在于,既認同魯迅的惡憤“布施”之境,也傾心知堂的寬容與豁達。甚至,在日漸狹窄的呼吸空間里,不禁悠然升起對波士頓老房東屋子附近偌大之湖之森林公園無阻暢游的思念。
不過亦如知堂老人,一時的心情一時的言語,只不過是“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到今天,在準許的時間段,我得以跑進“封鎖區”,享受沒有汽車廢氣侵擾的跑步,還聽到了性情學生的優美笛音,已是心情舒暢。雖然景區的亮光短促,距離也倉促得很,但這份寧靜和算得上的舒適,能免費給予景德鎮的百姓,在當下的時代,實屬難得了!(就不知道會不會某個時候有再度的規定,有再度的喪失?)這是一個物質豐富到地皮和自然都必須緊張脅迫以至于呼吸空間漸趨喪失的時代!夾縫中謀生存,知堂老人的苦茶技藝,彌足珍貴。
隨遇隨緣,也是我的為生之態。比如我喜好路邊碰上什么買什么,是因為總不記得什么物品在何地何時有合理的價格。又不是特別精于挑揀和講價。路邊若遇上稱自家種植的水果蔬菜,總會欣喜無比,一如知堂老人懷念紹興的野菜。
景德鎮的清明粑應該就是周作人懷念的艾餃了。這幾天,心中特別饞清明粑。總盤算去趟一院附近,有一家賣這小吃的小店,只有這個時節才能吃到充滿艾葉香味的可口粑餃。記得剛回景借居衛校婷婷家,過了清明,這小店的主人就說,不賣清明粑了,因為沒有艾葉了。當時我奇怪,景德鎮賣餃子粑的不都賣清明粑么?原來那是假的,是用色素糊弄人的。從此后,我對這家小店滿懷信任。從前的家鄉景德鎮,不太熟悉這個“假”字,粑果都很實在,就是幾分錢一個的煎包,也有豐厚的韭菜肉末大餡。而今價錢抬轎子似的蹭蹭上漲,品格卻淪落不堪。事實上,上周下完課,我就騎上自行車去尋找過,不遇小店。后來到老八湯店買了三籠所謂“清明粑”,口味卻很一般,一點白豆腐糊弄一下。
當我很有目的地去追尋時,空手而歸會很痛苦。當然,也如知堂老人所言,我能掙扎的,也只不過是清明粑等小玩意而已。真的讓我心痛追隨,甚至不惜生命拼搏的,卻被迫喪失而且永遠夭折。出師未捷身先死,我又奈何得了什么呢!上周找清明粑的那一天,還在路邊遇上賣香腸和腌肉的,購得香腸32元一斤,腌肉15元一斤。買完后,我方記起,在景德鎮買東西是總要還價的,又一次忘記了。也許人家32元一斤,那2元的零頭就是等你來還價的。可我總是在買完東西后,方記起。后來,在買蕨菜時,牢牢記住,7元一斤,就趕緊問:可不可以便宜一些呀?人家說:不可以!今年還是第一次吃到蕨菜。今年還沒有吃到過水竹筍。這個季節是景德鎮有最多最好野菜的時候,要是知堂老人的魂靈神游此地,也一定流連忘返,沒準更生一篇新作《景德鎮野菜》,說不定呢!
其實,我思念清明粑,正如知堂老人念及他“兒時的黃花麥果糕”。再也吃不到小時候狄仔姆姆(景德鎮話,舅舅的意思,來源于母舅)家送的清明粑還有蕎麥餃子了。即使是在景德鎮,也翻天覆地變化了。狄仔姆姆的母親是外祖母的丫鬟,她后來嫁人生子。我外祖母被掛牌游街,即使是在唾棄地主婆的時代,狄仔姆姆家也一如既往地給我們家從古田鄉下送來柴火,清明有清明粑、蕎麥餃;端午有肉粽、糖粽;春節有年糕、糖糕,還有一種叫作洋糕的,好吃得不得了。狄仔姆姆家的清明粑餡子飽滿豐盛,味美的冬筍加臘肉,特別是辣的,即使小時候我吃完上蹦亂跳,眼淚稀里嘩啦,還是愛吃!而今狄仔姆姆的后代們有自己的事業,無暇再做粑了。(校稿時,狄仔姆姆已駕鶴仙去,此記,權當悼念了!)
隨遇隨緣的好處就在于沒有負擔的不經意。無論長久,卻又淡淡幽香。周作人對托盤在路邊兜售青黃豆要結緣的和尚是有點看法的,因為贈一顆豆是要索回來世萬千豆的那種。天地間,有一份緣,偶然所得,便是福,便值念。遇人遇事,讀書寫作,無不如是。世間許多緣,往往斷送在執念下,知堂老人的沉默低吟,輕輕放下的不辯解,我感覺特別合適于這寒食清風季。學老人樣,借食言憶,并非那多篇“清明”文中所言的“厚人薄鬼”,而是共賦一份歷經人間滄桑后的孤冷清俊。
2012年3月28日于高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