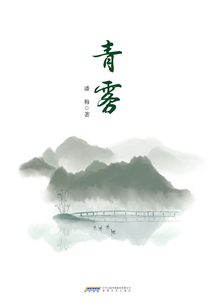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3評論第1章 序言
《青霧》的故事,幾近真實,起于潘園,止于潘園。
潘園是皖西大地上的一個小小村落。我父親是土生土長的潘園人,也是最早離開故土奔赴小城營生的潘園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隨父親回潘園探親,成了兒時的我最向往的一件事情。那時的潘園于我而言,一草一木都充滿著極致的誘惑,古老又神秘,讓我新奇、興奮且又深深地恐懼。
隨著生活的跌宕,我離潘園越來越遠,對潘園的印象,變得模糊,分崩離析成一個個零碎又混亂的畫面,隱匿在我記憶的夾縫里,潘園,仿佛只剩一個空洞的、遙遠的概念。曾一度以為,我對潘園的情感淡漠了。可往往,就在某個時刻,哪怕是嗅到了類似潘園的鄉野氣息,也會措不及防地觸動一段我對潘園的回憶。閉上眼睛,我依然能清晰地看見久遠時空外的潘園:厚重的黃土地、靜謐幽深的竹林、盤桓在潘塘上的濃霧、古老的杏子樹,在破舊草房的殘垣斷壁處,偶爾竄出條黑紅相間的毒蛇——潘園人叫它“土根蛇”。還有更讓我恐懼的裹著小腳的巫婆、被家人深鎖在土房里的瘋子……原來,曾經的潘園,始終駐扎在我靈魂的最深處。
原諒我使用“曾經的潘園”一詞。我不確定除了“曾經的潘園”,還有什么詞匯可以概括那個記憶中彌散著神秘的、隔世氣息的村落。總之,它與當下的潘園截然不同。
城市的擴張,經濟浪潮的沖刷,使年輕力壯的潘園人遠赴各個城市謀生,現在的潘園,只殘留幾個老弱婦孺的身影在日漸萎縮的土地上勞作:種種豆角或拾拾麥穗。豆角是一畦菜園里的豆角,麥穗是田間遺落的麥穗。他們閑散的步調,無力也無心忠于農事,一任夕陽,將他們孤單的影子越拉越長。
潘園人對土地的依附感弱了,祖祖輩輩曾賴以養家糊口的土地好像可有可無。這是時代變遷引發的蝴蝶效應,也是城市化進程必然的癥候之一。可這一切,應該與潘園人對待土地的情感無關吧?是了,憨實的潘園人怎會拋卻生養他們的土地?無論現代文明的皈依或是背叛,土地,始終都報以寬厚的沉默。可一聽見“土地”,潘園人仿佛就能嗅到小麥的香味、聽見玉米拔節的脆響。潘園的土地,隱喻了質樸、包容、沉穩和綿綿不盡的生命。對待土地,潘園人的血液里一直傳承著信徒般的敬畏和虔誠。雖然,機械和科技正在密不透風地武裝人們的生活,土地離人們越來越遠,可潘園人依然堅信,嘹亮的勞作口號,伴著閃閃發亮的汗滴,終會再度盤旋在潘園如洗的藍天。這種隱秘的傳承使散落在各地的潘園人如一個個放飛的風箏,線的那頭,緊緊地牽扯在潘園的土地上。
月圓中秋,遠在都市打工的某個潘園姑娘,抬頭望望鋼筋水泥夾縫里一線灰茫的天空,她突然很渴望來一把帶著潘園泥土清香的秋花生,咬一口從潘園枝頭上摘下的紅柿子。炎夏酷暑,正在辦公室加班的某個潘園小伙,被空調里的冷風吹得直哆嗦。他想起了潘塘,想起了小時候光著腚一頭扎進潘塘里的清涼。潘塘里的魚蝦甚多,他一猛子扎下去,待再探出身時,手里興許會多條鯽魚。不遠處,一條水蛇漫不經心地游弋,靈動的身段甚是從容優雅,身后漾起長長的水紋。塘邊的河蚌,莫名就將兩扇貝殼緊攏,在淤泥里拖出一條筆直的痕跡,向潘塘深處滑去……這個潘園小伙抿抿唇,清秀的手扶了扶眼鏡,繼續在鍵盤敲出一片鏗鏘之聲。
我已經沒有機會再去追問,病重的父親,執拗地遷戶回潘園時,他是否全然忘記了當初奮不顧身擠進城只為一紙商品糧戶口本的辛酸?兜兜轉轉,便是一生,父親最終安詳地躺在牽扯他一生的黃土地上,魂落潘園。
竹林深處的墳冢,是潘園人認定的歸宿。
潘園的老人最忌諱鄰村的亂墳崗。亂墳崗,葬的或是客死異鄉的外族人,或是因自殺等種種原因不能落葬自家祖墳的孤魂。在潘園這片土地上,一直都有這樣古老的傳說:人有三魂七魄,人死后,魄消散,獨留魂存在,若是不能落葬祖墳,受不到祖先神靈的庇佑和后人拜祭的香火,就會變作充滿戾氣的孤魂野鬼,入不了天道輪回。在潘園人的意識里,那將是多么可怕的事!以至于潘園人可以不計較活著時遭遇的種種磨難,唯獨懼怕死后,變成一縷亂墳崗上無家的孤魂。村里的老人早早就為自己做了準備:把棺槨漆得锃亮,黑色壽衣上,花團錦簇。請風水先生挑選陰宅時,他們的神情尤為認真肅穆,像是舉行生命中最重要的儀式,也是最后一次,虔誠地叩問土地。
至今我仍然無法想象,這些老人親手為自己砍制棺槨或縫紉壽衣時的心境。在我看來,油漆再亮、花朵再艷,也遮不住棺槨和壽衣散發出的陰森的、死亡的氣息。單就那兩個詞本身,就足以讓我戰栗和恐懼,毫無美感可言。
鄰村的亂墳崗早已不在,據說是八九年的一場洪水把它沖平了。潘園的老人們心里像是卸下塊重石,無端地輕松了許多。洪水退去,亂墳崗里露出許多女嬰的骸骨。潘園人聽聞后,長久地嘆息一聲,伴著更長久的沉默。蒙昧的年代,在未開化的鄉風里,女嬰的離奇死因,鮮有人深究。地要鋤,田要耕,糧要收……哪一樣不是指望兒子們的一身蠻力接替父輩在土地上折騰?重男輕女,也一直根深在潘園人的思想里。
我曾不止一次地揣測,是不是時代的迅猛發展遠遠超出了潘園人單純的認知,導致潘園人缺失安全感,不得已才順從于手忙腳亂的隨波逐流?仿佛多米諾骨牌,誰碰倒的第一個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第一個倒下,后面的骨牌就會跟著起連鎖反應。潘園經常出現這樣詭異的現象:打工,許多人背負行囊去一個地方打工;蓋房,全村爭先恐后去蓋洋房——有沒有人住倒是次要的。有段時間,連去九華山等佛門凈地當僧侶,都在潘園形成了一股流行的風尚。據說,那時潘園人去九華山觀光不用買門票——寺里有很多老鄉。尋常人得花重金才求得的開過光的佛珠,在潘園,基本人手一串,當然也是寺廟里的老鄉給請的。
經濟浪潮用快到幾乎讓人窒息的速度席卷著皖西大地,潘園也逐漸脫離了農耕社會的軌跡。第一棟刷滿油漆的洋房取代了曾經的土墻草房,很快,棟棟洋房,便以驚人的速度蔓延,霧色中,無聲無息地吞噬著潘園的土地。我總以為,是命運開的一個玩笑吧,潘園蓋的第一棟洋房,名為洋房,出于何種原因卻帶上了永遠也掩飾不了的土氣。不久,潘園有了第二棟、第三棟……一棟棟望去,它們盡管大小各異,卻都有著驚人的神似——土氣。這種土氣,由內而外散發著說不清道不明的別扭。我曾試圖找個比喻來類比,卻沮喪地發現,除非用建筑學的專業術語解釋,否則,空泛的語言無法替代我強烈的視覺感受。神奇的是,在潘園,沒人覺得不妥,仿佛洋房本該如此!他們恬淡的態度幾乎讓我產生錯覺:或許洋房,本該如此?
這些洋房通常都很寂靜,稀有人煙,沉默地矗立在小城邊緣。更深人靜時,偶爾也會有那么不安分的一棟,像一條鬼鬼祟祟的貪食蛇,趁人不備,迅疾就多出幾平方米——類似城市拆遷時常見的伎倆——看似笨拙的洋房,除了頑強的侵占力,也會透著些許農民式的狡黠,一如潘園人。人性,總會在某個細微之處彰顯,微妙又復雜。
當然,樸實、善良、和順,才是潘園人亙古不變的底色。潘園的每一片土地都刻著生命的印記,流經的每一條河流都承載著有溫度的故事。
許久不回潘園,而若是回到潘園,必定是瘸腿的春花站在潘塘邊迎接我。她是我的堂姐。每每見到她,我都有一種抑制不住的沖動,要把她的故事寫成小說。
一走近她家樓房,我便看見桌上一束雛菊正在怒放。這時候,春花遞給我一把竹椅,擺上一碟皖西的咸瓜子,我一坐下,她便開始重復她冗長的故事。她唇角上揚,眉眼波瀾不驚,語氣平和得像是在述說別人的故事。她把所有的悲喜都隱匿在了故事的背后。陳年往事像是一塊風化的石頭,被她緩緩的語調層層剝開。
如果人的靈魂可以用實物來區分屬性的話,潘園的每一個靈魂都有著不一樣的屬性。有些靈魂充滿粗獷、生腥的野性,像潘塘里的黑魚,以強悍的方式肆意掠奪食物侵占巢穴;有些靈魂則是塑膠的合成品,始終保持著固化的姿勢,若是有幾縷陽光照射上,你會發現,上面已蒙上了一層薄薄的灰塵。
而春花,我想,她的靈魂屬性應該是野雛菊,扎根在土地上,卑微地怒放。潘園的野雛菊盛開在初秋,是灰冷肅殺的霧色里突然跳出的一抹嫩黃,這抹小小的嫩黃,歷著風吹雨打,每一天都在新鮮地生長,頑強地散發著沁人心脾的香味。鄉野田間的野雛菊,似乎并不迎合大眾的審美趣味,無人懂得欣賞,可這并不妨礙它沐一場燦爛的花事,唯一的觀眾,是它自己,也只能是它自己。
就像我始終無法真正走入春花的故事,替代她所有的情感一樣。
我一直在思考,我是個寫小說的人嗎?也許不是,對于她的故事,我充其量只是一個轉述者。我想,如果春花識文斷字的話,她必定是個很好的小說家。一個作家的成功,往往并非依賴于文學知識,而是依賴于真實的生活經驗,最好的小說家應該是經歷故事的她自己。
沈從文說,寫小說要貼著人物寫。捫心自問,《青霧》里我時時貼著春花寫了嗎?答案是否定的。我想,我可以輕而易舉地轉述她一生如何艱難地尋求更好地活著,卻始終游離在她切身的、強烈的、真實的喜怒哀樂等情感之外。在屬于她的故事里,我的情感似乎陷入一個灰色地帶,哪怕我的筆下已經砌滿了歡喜、歡愉的色彩,也沒法完全描述她當時的喜,而她時時經歷的巨大哀慟,又豈是我寥寥數筆可以概括的?她數十年的歲月就這樣被我殘忍地壓扁成十幾萬字,輕飄飄地一頁一頁給翻過去。
很多人熱衷于討論意蘊,也許故事本身就是意蘊。如同潘園的青霧,更多時候只是個意象,代表著某種隱喻——生活不時讓我們如墜身青霧,茍且于三丈以內,前方是漫無邊際的迷茫。這個叫潘園的村落,又何嘗不是一種意象?
生活的本質是什么?我想,應該是尋求如何更好地活著吧。潘園的每個人都在不停地掙扎、折騰,與命運做抗衡,保持著向上的姿態,赤手空拳,努力沿著自己看似正確的人生軌道前行,春花是這樣,張務軍也是這樣。他為了擺脫土地的束縛,通過聯姻方式去尋求前途,帶來的是空洞,是瑣碎,是無盡的苦惱。或許,生活本身就是一場不動聲色的圍剿,不用刀光劍影,僅僅是一地雞毛的堆疊,就足以磨滅人的意志和肉身。對于潘園人,唯有土地是包容的、寬厚的,默默滋養著每個潘園人。
春花的第三段婚姻我并不看好,那時我父親正好在小城開了座賓館,收入可觀,帶著憐憫與施舍,我請她來我這打工。她笑著說走不開,土地里的農活要忙,家里的孫子要帶——她第三任丈夫的孫子,與她并無任何血緣關系。嘲諷的話還沒出口,一抬頭,望著她那雙明亮的眼睛,我頓時羞愧不已。我的憐憫是源自俯視的心態,泛著缺失溫度的冰冷,就連施舍,都烙著可恥的炫耀。其實,誰比誰活得更好,又怎能分辨清楚?終日困扎在鋼筋水泥閣樓里的人不見得就一定比心思簡樸的潘園人更加熱愛生活。
文化、文明,大時代背景下人物的生存和命運,土地的依附,精神的荒蕪,人性的多層,命運的不可知……潘園的青霧,是無法說清的人生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