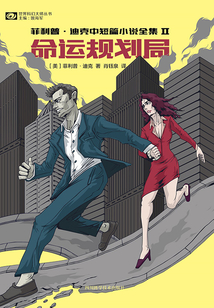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引言
[美]諾曼·斯賓拉德
1952年,菲利普·迪克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說《烏布》。1955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系大樂透》問世。本卷《命運規劃局》便收錄了迪克從1952年到1955年間發表的二十七篇短篇小說。
值得一提的是,迪克在作家生涯的頭四年所發表的作品遠不止二十七篇。
就作品數量而言,已經非常了不起。鮮有作家能在開始寫作的頭四年發表如此之多的作品——即使這一時期的短篇小說市場相對繁盛,編輯們對投稿的需求量較大。必須承認的是,本書中確實存在一些故事立意膚淺、華而不實,但書中大多數故事已初顯迪克日后成熟作品中的那種獨一無二的風格,即使其中最不出彩的作品也具有他獨特的烙印。
一名初出茅廬的作家,用如此短的時間完成了如此多的作品,這么做的目的是想賺取金錢、博取名聲。這是事實,但盡管如此,這二十七篇小說仍瑕不掩瑜。
實際上,本書中的小說沒有一篇是有固定套路的動作冒險故事。沒有太空歌劇,也沒有長篇累牘地渲染細節,甚至沒有高度發達的外星球文明,更不要說老套的硬漢英雄、反面惡棍、瘋狂的科學家,以及好人打壞人之類的了。在寫作之初,迪克便視科幻小說的商業慣例為無物,即使是只能講一次的噱頭也帶有其強烈的“迪克式”風格。從一開始,迪克便在徹底地改造科幻小說。他將科幻小說變成了表達自身關注,或者說自身迷思的一種文學手段。
本書是一枚迷人的時間膠囊,它裝載著二十七篇在菲利普·迪克首部長篇小說面世之前發表的中短篇小說。它讓我們得以窺見他那短暫的、高度壓縮的學徒期。在那之后,他便成長為二十世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或許也是史上最偉大的哲理小說家。
迪克開始寫作的年代,至少就出版業而言,正處于科幻界最重要的轉型期。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早期,科幻出版業仍以雜志發行為主,這意味著科幻文學的主要形式是短篇。到1955年迪克發表《太陽系大樂透》時,平裝書逐漸成了主流的發行方式,于是長篇小說開始流行起來。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一部長篇科幻小說的常規預付款約為1500美元。所以,科幻作家要想維持本已捉襟見肘的生活,不得不向雜志社投稿大量短篇小說。而且當時對長篇小說的需求量并不大,科幻作家在沒有獲得出版社的長篇小說合同之前,想要揚名,只能寄希望于短篇小說。
現在來看,正如這本短篇小說集所呈現的,至少在文學層面,即使對于像迪克這種天生適合寫長篇小說的作家來說,這也并不是件壞事。本書的二十七篇小說,和迪克在《太陽系大樂透》之前發表的其他小說,很好地詮釋了他所經歷的鍛煉。
當讀者們一篇接一篇閱讀本書中的小說時,會切實感受到各篇作品中存在的某種雷同、重復或者是千篇一律,似乎與作者后來的作品有不小的出入。這種現象,我們在同時期,甚至于之后一段時期內的作家,如約翰·瓦利、威廉·吉布森、盧修斯·謝潑德和金·斯坦利·羅賓森等人所寫的短篇小說中也能看到。
但在本書中,我們看到的雷同是絕無僅有的迪克式風格。
大多數科幻作家會在創作早期的短篇小說時圈定自己的題材范圍,并在之后的寫作生涯中對此進行深度和廣度上的擴展。如拉里·尼文的“已知空間”系列,創造了連貫一致的宇宙;或如凱恩·諾莫的“雷蒂夫”系列,塑造了一位常青樹般的主人翁;或如羅伯特·海因萊因的“未來歷史”系列,打造出了一個歷史范本。三者兼有之的亦不少見。
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商業策略。一位新作家,不管出于天真或瘋狂,想將寫科幻短篇作為全職工作,并以之為生,那他必須用極快的速度寫出大量作品以便一直為大眾熟知。重復地利用歷史背景、人物角色和科幻設定比每次都從零開始要容易得多,而且,正如有線電視早已證明的那樣,連續劇是也建立受眾群最快捷的方法。
然而,菲利普·迪克并非如此。在這些小說中,沒有常青樹般的角色,也沒有將所有故事放在一個連貫的宇宙中的企圖。除《二號變種》《喬恩的世界》和《詹姆斯·P.克勞》這三篇作品間存在微弱聯系外,迪克甚至也未嘗試采用一致的歷史設定。
當然,迪克也重復使用相同的主題、意象和形而上的哲思。在之后的作品中,他使其充分擴展,變得繁復而意義深刻,并投射進更為宏大的場景當中。
地球淪為了核灰燼的堆積場。機器人武器正進化成兇惡無情的仿生人。人類的自由以軍事安全、經濟繁榮,甚至以自由本身的名義慘遭蹂躪。不同的現實間的穿插;充滿諷刺意味的時間循環和悖論;小說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做著平凡工作的平凡人,只想混口飯吃,全無偉大的抱負。
迪克創作這些小說的時期,正值冷戰進入白熱化,約瑟夫·麥卡錫議員和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掀起的反共產主義狂潮上升到頂點,核戰狂想陷入低谷。學校的老師教導學生,空襲警報響起時,要躲在桌子底下。顯然他的小說大膽地反思了這些現象。這說明,從一開始,迪克就是一位深刻關注政治的作家。
他的小說所透露的意義并非局限于此。那時,軍國主義、癡迷軍防、仇外情緒和沙文主義等各種極端言論盛行;盡管面臨極大危險,迪克仍響亮而明確地發聲反對。
而進一步分析你會發現,小說中站在這些大規模政治罪惡對立面的,并不是同樣規模的、正面的政治理念,而是小小的、謙遜的人類美德,比如低調的英雄主義、博愛無私以及最為重要的以己度人、感同身受的能力;正是這些德行最終將人與機器,靈魂與機械,以及真正的人類與最巧奪天工的仿生人區分開來。
如果我們已經了解了貫穿菲利普·迪克整個寫作生涯的偉大主題和精神核心,那我們同樣能體會到這些小說中剛剛萌發的迪克獨特的文學技巧。他有力地運用多視點人物寫作手法,將故事深入到了隱秘而細膩的個人層面。
誠然,在這些早期的故事中,迪克對多視點人物寫作手法的運用并非始終完美。有時在某個單獨場景中,僅僅是為了敘述方便,他便不管不顧地轉換視點。有時他會在文中引入一個全新的視點角色,只是為了給出一個他用既有角色視點難以進行描述的場景。有時一個視點角色只出現在幾段話中,其后便消失不見了。
通過創作這些小說,迪克學習了多視點人物寫作手法,或者更準確地說,發明了這種寫作手法。因為在迪克之前,幾乎沒人運用多視點寫作手法。而對于所有在其后想運用這種手法的人,不管是否自覺地意識到,都應歸功于迪克。
運用迪克式多視點寫作手法,作者能夠不再局限于單一的人物視角,可以運用多名人物的意識、精神和內心講述故事。它賦予讀者親密感,讓讀者感同身受,在單一故事的篇幅內表現出人類復雜的精神世界。在像菲利普·迪克這樣的大師手中,它變成了窺探現實世界的抽象多樣性的一扇扇窗戶,實現了形式和內容的完美統一。
若說這二十七篇小說完美無缺,是作者日后成熟才華的全面綻放,則與事實不符,也有損菲利普·迪克的文學聲譽。但透過它們,我們能看到過去,看到一個偉大的思想者如何踏上漫漫征程的起點。我們也能看到未來,看到寫下這些故事的才華橫溢的科幻新人在日后注定成長為一代科幻大師的前景。
198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