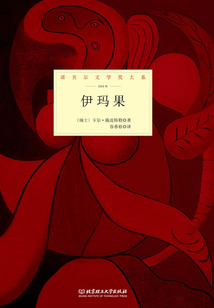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頒獎辭
“以表彰他杰出的史詩《奧林匹斯的春天》。”
瑞典學院諾貝爾委員會主席 哈拉德·雅恩
瑞典學院依照諾貝爾基金會的章程把去年未能頒發的191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瑞士作家卡爾·施皮特勒先生,以表彰他杰出的史詩《奧林匹斯的春天》。
對于這部作品,我們可以說它“大器晚成”。雖然,它的價值被認可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時間,但如今它在文壇上的地位已經穩如磐石。現在欣賞這本書已經不再是件異常辛苦和令人懷疑的事情了。因為它不僅有詩歌之美,也有詩歌之外的美,它在能明確地表達作者的主題的同時,又給人以藝術的美感。這種完美的結合來之不易,只有既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又對生活充滿美好理想的優秀的天才才能做到。
有人這樣評價這部詩說:“本詩的形成,不是來自作者明確又自由的自發的意識,而是來自一種矛盾的沖突,是我們和一種隱晦難懂的思想一直做斗爭,最后才產生的。”對于這種說法,我們不能茍同。在對作品的理解上,讀者和評論家本身就和詩人想表達的意圖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這種差距并不意味著誰對誰錯,只能說明這部詩歌的含義是豐富深刻的。我們只有多方理解,才能更完整地體會它的意思,對它做出客觀的評價。
之前,這部作品只在瑞士和德國流傳較廣,版本是1909年的改寫版。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特別是世界大戰結束后,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它,今年新版本預計會售出幾千冊,這個數字對于在市場上銷售的圖書來說已經非常驚人了,因為它的主題寫的是遙遠的奧林匹斯神祇的故事,而不是一部貼合我們實際生活的作品,更何況這部作品厚達六百多頁。因為這本書特殊的文學類型,所以,必須把它不間斷地全部讀完才能體會其意義。這就要求讀者有足夠的時間,并且非常專注。作者用了長達幾十年的時間來完成這部作品。寫作過程中,他刻意和當代紛亂的生活保持距離,不計較應得的物質得失,這么做可以說對自己是殘忍的。
對于本書的復雜性,作者從未想著把它簡化,甚至還有強化它的趨向,特意選擇這樣的題材和寫作方法。這種題材和寫作方法,無論是在哪種素養、性格、愛好、教育背景的讀者來看,都是難以理解的,特別是他們進入書中,準備了解這部作品展示的整個世界時,更是無所適從。而作者則非常有勇氣,從書的開頭,他就告訴了讀者們,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和耐心,才能跟著他的思路,看完他展示給我們的這個神奇的故事。這個故事,只有我們弄明白情節,鋪好各條脈絡,再加上主角的獨白和他們間的對話,才能整體讀懂它的深刻含義。這里面,主角的獨白和對話像戲劇一樣出彩,文學鑒賞力強的人甚至會發現,這部作品有荷馬的風格,盡管作者帶領讀者走的是一條完全陌生的、事先不知道其目的地在哪里的道路。
不過,從別的方面來說,施皮特勒的神話故事是他自己創造的,有明顯的獨到之處,與荷馬的奧林匹斯有著明顯的不同。有人質疑施皮特勒的目的,說他的寫作不過是用語言學家的文字游戲和其他學說的研究者慣用的伎倆,故意寫一些難懂的意象和細微的象征,目的是吸引那些學究們。他們這樣說對施皮特勒很不公平。他書中的奧林匹斯神祇、英雄,以及神話的內容、比喻,和那些古希臘詩人及哲學家區別很大,無論是從風格還是語氣上。他的作品既不是對晚期古典文學進行的詮釋,也不是詩人依賴、借助寓言的證明。有人說這部作品和《浮士德》的部分內容類似,我對此并不贊同。因為,施皮特勒沒有模仿任何作家,包括年邁的歌德。相對于歌德用浮士德和海倫來調和浪漫的熱情和古典,施皮特勒的神話只是他自己經歷的一種真實表達,來自于他自身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形成的對紛繁復雜的充滿斗爭的人生的認識。作者想通對一個理想國的描繪,力求將人類世界中的辛勞、希望與失望,人們各不相同的命運及自由意志與被壓迫之間的矛盾關系進行生動的再現。通過他的描寫,我們看到許多生動的角色,卻都在混亂中不停掙扎。他不會顧慮現代美學的規范,不會讓自己夢幻和現實相融合的世界受到影響,并且,還有各色神話角色的名字充斥其間。施皮特勒的作品是公認的晦澀難懂。
雖然我整理了很久,想摘錄一段能夠為人理解的《奧林匹斯的春天》的情節,但是,我依然不能給大家呈現出一幅完整的畫面,說出它的具體情況。我也描繪不出那些閃閃發光的、生動鮮活的插曲,以及作品中無時無刻不在的神的力量,也描繪不出那些插曲和整個作品之間無法分割的關聯。我只能大概地說,奧林匹斯的生命光輝如此高大,他和小宇宙一起,給人感覺既充滿歡樂,又包含著痛苦。但是人類不知感恩,肆無忌憚地犯下各種罪惡,既而痛苦,最后終于感覺一切都無法改變了,便陷入深深的絕望中。赫拉克勒斯作為宙斯的兒子,雖然他那做天神的父親和親朋已經賦予他全部的美德,但是,女王赫拉也把仇恨和詛咒加在了他身上,所以他不得不離開奧林匹斯,到人間去完成不會獲得任何回報且需要極大憐憫和勇氣才能完成的任務。
奧林匹斯諸神都做了很多偉大的事跡,他們敢于冒險,能打勝仗,彼此之間喜愛爭論,但是在詩人看來,這些超人們必須控制他們狂妄的想法以及膨脹的欲望,才能做到真正有價值。
“智者掌控命運,愚者被命運擺布。”[1]超越諸神之上的,由命運在掌控著,命運是一種肅穆無聲、捉摸不定的力量,它冷漠無情,是整個宇宙的運行法則;在諸神之下的,是離我們較近的沒有靈魂的、機械的自然之力。這個地方,無論是神還是人,都要做貢獻,為自己、為他人,但是自然已經被神和人的邪惡及傲慢侵蝕得遍體鱗傷,人和神的行為是愚蠢的,自己也會因此遭受毀滅。在這部史詩中,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荷馬詩中根本不存在的東西:飛船、尖端的發明創造、圓頂莊嚴的拱門等。但是在詩中,陰暗可鄙的扁平足民族,創造了人工太陽,替代了阿波羅的能力,使他喪失了宇宙權柄,并且,他們還使用功能陰毒狠辣的車子及毒氣,企圖在太空中殺掉阿波羅,這一切都說明了,物質力量帶給人們的已經不單是自信,它已經把人們引向歧途,使人們走向衰落。
施皮特勒除了描寫詼諧的情節,還描寫英雄們面對的傳奇般的考驗以及他們做出的偉大事業。他描寫詼諧的情節信手拈來,收放自如,這一點,很像阿里奧斯托[2]。他的風格變化頻繁,無論在語氣上還是在感情色彩上,有時嚴肅莊重、充滿傷感,有時又格外小心,變成了明喻寫意方式,有時又盡情生動地展示大自然的美。他筆下的大自然,都是自己的故鄉阿爾卑斯山區的景色,這和希臘的大自然景色不一樣。他對語言有超高的駕馭能力,詩的格律和輕重音都運用得既頻繁又恰當,文字華麗準確,又不乏活潑,并且是典型的瑞士風格。
瑞典學院非常高興能夠把獎頒給施皮特勒,因為他詩篇中所體現的獨立文化值得贊揚。施皮特勒因病未能前來參與領獎,此獎將由瑞士大使館代為轉交。
注釋:
[1]出自《奧林匹斯的春天》第3部第5章節。
[2]阿里奧斯托(1474—1533年),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著名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