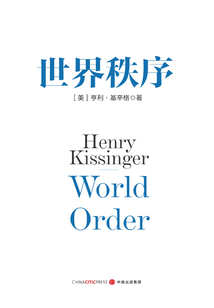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4評論第1章 序言(1)
對世界秩序問題的思考
1961年我作為一名年輕學者去堪薩斯城做講演時,拜訪了杜魯門總統。我問他,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哪件事最令他感到驕傲。杜魯門回答說:“我們徹底打垮了我們的敵人,隨后又把他們拉回到國際大家庭中。我認為,只有美國才會這樣做。”杜魯門總統深知美國擁有巨大的實力,但最令他感到驕傲的是這一實力所包含的人道和民主價值。他更希望后人銘記他是因為美國與敵人實現了和解,而不是戰勝了敵人。
杜魯門之后歷屆美國總統都做過類似的表述,他們都對美國在歷史進程中表現出來的類似品質感到自豪。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歲月里,他們致力于捍衛的國際大家庭反映了一項美國共識:不斷擴展合作型秩序,各國遵守共同的規則和Preface準則,實行自由經濟體制,誓言不再攫取他國領土,尊重他國主權,建立參與型的民主治理體制。來自兩黨的美國總統始終敦促——常常是雄辯地力促——他國政府同意維護和促進人權。在很多情況下,美國及其盟友捍衛這些價值觀,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境況。
然而今天這一“基于規則的”國際體系面臨諸多挑戰。我們頻頻聽到各方面的呼聲,促請各國在一個共同的體系內“盡自己應盡的一份力量”,遵守“21世紀的規則”,抑或充當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這反映了該體系沒有一個各國均認可的定義,對什么是“應盡的”力量也沒有一致的理解。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區在這些規則的最初制定上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它們對這些規則提出質疑,明確表示要推動修改這些規則。今天“國際社會”一詞在各種場合出現的次數之頻繁可能超過了任何一個時代,然而從這一詞中卻看不出任何清晰或一致的目標、方式或限制。
當今時代鍥而不舍,有時幾乎是不顧一切地追求一個世界秩序的概念。世界混亂無序,各國之間卻又史無前例地相互依存,從而構成了種種威脅: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擴散,國家解體,環境惡化,種族滅絕現象層出不窮,以及有可能將沖突推向人類無法控制或無法想象地步的新技術正在擴展。新的信息獲取和傳播方式把世界各地區前所未有地連接在一起,使人們從全球視角審視各種事件。然而這種狀況卻讓人無暇思考,使領導人不得不對任何事件都即刻做出反應。種種不受任何秩序約束的勢力是否將決定我們的未來?
不同類型的世界秩序
從來不存在一個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當今時代的所謂秩序源于近400年前在德國的威斯特伐利亞召開的一次會議。其他幾個大陸和多數人類文明國家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甚至不知道有這么一個會議。此前中歐地區的教派沖突和政治動亂持續了一個多世紀,最終釀成了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這是一場各種政治和宗教爭執相互交織的戰爭,卷入其中的各方針對人口稠密地區發動了“全面戰爭”。中歐將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戰火、疾病或饑餓。筋疲力盡的參戰各方于是召開會議,為制止流血做出一系列的安排。新教的存活和發展導致了一統宗教的分裂。打成平手的各種自治的政治單元并存,呈現出政治多樣化的特征。因此,當代世界的形態大致是在歐洲形成的:一批多元化政治單元探索用于管控自身行為、減緩沖突的中立規則,它們中間沒有一方強大到可以戰勝所有其他對手,很多政治單元信奉截然不同的哲學,或者有自己獨特的信仰。
威斯特伐利亞會議建立的和平反映了各方對現實的妥協,而不是一種獨特的道德洞察力。它以一個由獨立國家組成的體系為基礎,各國不干涉彼此的內部事務,并通過大體上的均勢遏制各自的野心。在歐洲的角逐中,沒有哪一方的真理觀或普適規則勝出,而是每個國家各自對其領土行使主權。各國均把其他國家的國內結構和宗教追求當作現實而加以接受,不再試圖挑戰它們的存在。既然均勢現在已被視為一種自然的、不無裨益的存在,各國統治者的野心因此受到相互制約,至少從理論上限制了沖突的范圍。歐洲歷史上偶然產生的分裂和多樣性構成了新的國際秩序體系的特征,具有自己獨特的哲學觀。從這個意義上講,歐洲為結束自己大陸上的戰禍所做的努力預兆并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對絕對價值做出評判,轉而采取務實的態度接受多元世界,尋求通過多樣性和克制漸漸生成秩序。
17世紀巧妙地締造了威斯特伐利亞式和平的談判者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為一個全球適用的體系奠定基礎。這些談判者根本沒想過把比鄰的俄國包括進來。經歷了噩夢般“動蕩時期”后的俄國當時正在重新鞏固自己的秩序。它推崇的原則與威斯特伐利亞均勢背道而馳:單一君主擁有絕對權力,信仰單一的東正教,奉行向四面八方擴張領土的計劃。其他各大權力中心也認為,威斯特伐利亞會議(如果它們聽說過有這么一個會議的話)與自己所在的地區無關。
當年世界秩序的概念只適用于那個時代的政治家已知的地理范圍。世界其他地區的世界秩序概念也是一樣,主要原因是當時的技術不鼓勵甚至不允許一個單一的全球性體系的運作。由于缺少可以不斷保持互動的手段,又沒有一個可以衡量不同地區實力大小的框架,每一個地區都把自己的秩序視為獨一無二,把其他地區視作“未開化之地”,這些地區的治理方式與自己的既有體系毫無相似之處,與既有體系的構想毫不相干,只是對既有體系的一種威脅。每一種秩序都把自己界定為合法組織人類社會的標準模式,好像自己在治理眼皮底下的領土時,就是在號令天下。
在歐亞大陸上與歐洲遙遙相對的另一端,中國位居自己建立的等級分明、理論上具有普適性的秩序中心。這一體系已經運行千年。早在羅馬帝國一統歐洲時期,中國已存在這一體系。它不是建立在各國主權平等基礎之上,而是基于自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不存在歐洲意義上的主權,因為皇帝統御“天下”。皇帝位居一個獨一無二的、全天下的政治和文化等級制度之巔。這一等級制度從位于世界中心的中國首都向外輻射到人類居住的所有地方。根據其他地方的人對中國典籍和文化體制的熟悉程度(這一宇宙觀一直延續到近代),分別把他們視為開化程度不同的蠻夷。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燦爛文化和繁榮經濟令其他社會拜服,吸引它們前來與之建立關系。中國可以通過掌控與它們的關系號令世界,進而達到“天下大同”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