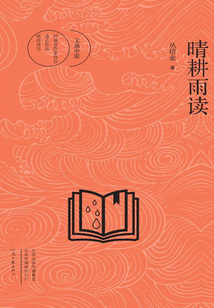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 第24章 端午節(jié):豐富多彩的文化氣象
- 第23章 五月的鮮花:禮贊勞動
- 第22章 最美人間四月天:四月的紀念
- 第21章 春天里的文化傳統(tǒng)
- 第20章 過好傳統(tǒng)節(jié)日 弘揚優(yōu)秀文化
- 第19章 童蒙養(yǎng)正與力行呈現——從《弟子規(guī)》想到的
第1章 蔡元培:古今獨步唯一人——由《教育在民國》說開去
《教育在民國》(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是智效民先生的一部學術隨筆集,被收錄在“百家小集”叢書中。
智效民先生以“教育在民國”為書名,竊以為或許至少向讀者傳遞了兩層意思:一是對民國教育場景的事實陳述,正如他在“后記”中所言,學術隨筆要做到“言必有據”。作者依據史料為讀者提供民國時期的教育現象,使讀者對民國時期的教育圖景有所了解。閱讀教育史料,洞察、品味那個時代教育人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與所作所為。二是對民國教育活動做價值判斷,對民國教育中所蘊含的人類文明與社會進步之元素,特別是能反映教育本真、彰顯教育智慧、恪守教育信念、追求教育理想等諸多特質——包括民國時期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改革以及師生關系等諸多可圈可點之處,予以褒揚和贊美。智效民坦言:“那個時代雖然歷經戰(zhàn)亂,卻涌現出無數大師級人物。這說明那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究其原因,我想,智效民所說的民國所具有的特征——“教育是獨立的,言論是自由的,軍隊是國家的,權力是有限的,君子是不黨的,地方是自治的,信仰是多元的,社會是開放的……”與“涌現出無數大師級人物”“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具有因果關系。同時,也是對曾經的歷史風貌的一種表達。在智效民看來,“民國年間的中小學教育與大學教育只是大同小異”。為何有如此結論?他認為,“這顯然與當年的教育獨立有關”。于是,他說,“因此我會得出‘教育在民國’的結論”。
對此,我們可以有所發(fā)現,“教育獨立”“獨立思考”在作者的思想譜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這也就不難理解智效民“始終堅持無一字無出處的學術傳統(tǒng)”,能以其言說有據的嚴謹,為我們還原民國教育的歷史真相。
《教育在民國》一書內有五輯:第一輯“教育理念”,13篇;第二輯“教育制度”,8篇;第三輯“教育改革”,9篇;第四輯“大學校長”,9篇;第五輯“師生之間”,8篇。如果再加上“自序”與“后記”,全書總計49篇。細讀這幾十篇文章,可以發(fā)現本書作者為我們展示的民國時期的教育現象或討論的民國時期的教育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民國時期的大學和大學校長,民國時期的教育流弊與教育改革,民國時期的教育價值觀和人才培養(yǎng),民國時期的師生關系與師者風范。這里廣泛涉及對教育本質和大學本質的理解,教育究竟要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學校教育的理念與課程模式的設計,對教育者即教師品格的要求,尤其是在教育與社會的關系中,如何使教育擁有獨立性,并能在制度層面予以保證。這樣的問題,即便在今天的教育生活中,依然為我們所矚目,需要我們予以回答。
教育問題,從根本上講,是人的問題。而在學校的場域里,它集中表現在師生關系中。民國時期的教育之所以精彩紛呈、激動人心,我以為,值得我們注意并應當為我們所珍惜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那一代學人、師者,尤其是老牌名校校長們所具有的獨特的人格魅力和追求真理的學術精神,他們在執(zhí)掌大學時,為中國大學教育的轉型和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發(fā)端所做出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奠定了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精神與理想,規(guī)制與模式。
1924年7月,陶行知先生在《半周歲的燕子磯國民學校——一個用錢少的活學校》中明確表示:“校長是一個學校的靈魂,要想評論一個學校,先要評論他的校長。”校長作為一個學校的靈魂,應當集中表現在校長的人格氣象和他的教育思想。當然,人格與思想兩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從思想層面看,陶行知先生希望校長能夠成為“第一流的教育家”,有“敢探未發(fā)明的新理”“敢入未開化的邊疆”的勇氣和膽略,有創(chuàng)造開辟的精神,有目光深遠的見地。從這個意義上講,校長作為學校的靈魂,就應成為學校發(fā)展的探索者和引領者;就應在審視歷史與把握當下的嬗變中,洞悉未來教育與社會發(fā)展的走向。校長的探索與引領是指向未來的,需要將高瞻遠矚與真知灼見相結合。民國時期的校長,如馬相伯、蔡元培、蔣夢麟、胡適、傅斯年、羅家倫、梅貽琦、張伯苓、竺可楨、晏陽初……這些教育大師可謂典范。他們書寫的民國教育史堪稱中國教育發(fā)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或許至今也無人能望其項背吧。
談及民國教育,蔡元培先生絕對是舉足輕重的重量級人物。而且,可以肯定地講,蔡元培先生的“道德學問和事業(yè),用不著我們標榜”。1912年,蔡元培先生執(zhí)掌教育部,出任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確定民國教育之方針,為民國教育定下了基調和走向。1912年2月8日,蔡元培在南京政府教育總長任內,發(fā)表了著名的教育論文《對于新教育之意見》(后改為《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作者注)。是時,《民立報》《教育雜志》《東方雜志》對此文都有刊載。文章中,他明確提出“共和時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標準,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圍繞“養(yǎng)成共和國民健全之人格”的思想,全面闡述了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舉的民國教育方針,以取代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與此同時,他進一步提出,將“五育”分別配置于不同的教科,并以它們所具有的特性,進一步規(guī)定其所占的比例和相應的權重:“本此五主義而分配于各教科,則視各教科性質之不同,而各主義所占之分數,亦隨之而異。國語國文之形式,其依準文法者屬于實利,而依準美詞學者,屬于美感。其內容則軍國民主義當占百分之十,實利主義當占其四十,德育當占其二十,美育當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觀則占其五。”
1912年7月10日,蔡元培主持全國臨時教育會議,征求全國教育家的意見,以謀教育事業(yè)之發(fā)展。在開幕式上,蔡元培作《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會詞》,在《開會詞》中,蔡元培揭露“利己主義”的教育本質,一針見血地指出,以利己主義為核心的君主時代之教育方針已不合用。而“民國教育方針,應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有如何能力,方能盡如何責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他重申教育家應遵循五種主義,“即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是也”。“五育”的核心是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說:“五者以公民道德為中堅,蓋世界觀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及實利主義,則必以道德為根本。”由此不難看出,蔡元培所要求的民國的受教育者,應隨時代的變化,形成新道德,并且應當在德智體美各方面獲得全面發(fā)展。蔡元培深刻分析了國人因無道德而產生的一系列問題,甚至是惡果:“我國人本以善營業(yè)聞于世界。僑寓海外,忍非常之困苦,以致富者常有之,是其一例。所以不免為貧國者,因人民無道德心,不能結合為大事業(yè),以與外國相抗;又不求自立而務僥幸。故欲提倡實利主義,必先養(yǎng)其道德。至于軍國民主義之不可以離道德,則更易見。我國從前有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之語。現在軍隊時生事端,何嘗非尚武之人由無道德心以裁制之故耳。”面對如此事實,作為教育者必須清醒地意識到自身的角色與使命,既要有指向將來的遠見,又要有矢志不渝之韌性。蔡元培認為,“教育者,非為已往,非為現在,而專為將來。從前言人才教育者,尚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說,可見教育家必有百世不遷之主義,如公民道德是”。公民道德教育的要旨即自由、平等、博愛。蔡元培以公民道德教育為核心的“五育”并舉思想,實質上是德智體美諸育和諧發(fā)展的思想,這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是首創(chuàng)。它適應了辛亥革命后教育發(fā)展的客觀需要,與當時社會變革的潮流相契合。遺憾的是,蔡元培做教育總長的時間很短,他所倡導的教育方針并未得到有效的實踐,他所追求的教育理想也并未實現。但是,他所提出的關于人的全面發(fā)展教育以及人的培養(yǎng)與社會需要之間關系的認識,卻是影響深遠的。
人們對蔡元培的評價,多以他在北大的教育改革最為重要。盡管事實如此,但這也只是外在的“表”而已,它不過是先生所恪守、崇尚、追求的內在核心價值觀的表征與彰顯,它應由更為深層的“里”予以導引和踐行,這也恰是蔡元培先生人格高尚與思想深邃,道德、學問和事業(yè)彪炳史冊的根本原因。這個“里”就是蔡元培對人的權利與義務的認識。蔡元培曾撰文《世界觀與人生觀》,以進化史的客觀事實為依據,表明自己的立場:“人類之義務,為群倫不為小己,為將來不為現在,為精神之愉快而非為體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而較著矣。”把這樣的思想、理解投放到教育世界里,則表現為對“教育獨立”“思想自由”的價值審視和判斷,以及由此進行的選擇與追求。早在1912年,蔡元培在《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中即對教育做“隸屬于政治者”與“超軼乎政治者”之區(qū)別,并指出“共和時代,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是為教育獨立之先聲。1922年,蔡元培發(fā)表《教育獨立議》,從教育要幫助被教育的人發(fā)展能力、完成人格而言,認為“教育事業(yè)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從教育是要個性與群性平均發(fā)達而言,認為“教育事業(yè)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黨以外”;從教育的進步而言,認為“教育事業(yè)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會以外”。為實現教育獨立,實行超然的教育,蔡元培在文中也擬定了相應的辦法,其中關于大學的事務,提出“都由大學教授所組織的教育委員會主持。大學校長,也由委員會舉出”。可以說,這是蔡元培教育獨立思想在大學教育體制改革中的集中反映,即倡導教授治校的原則。如果說,倡導教育獨立是對民國時期教育價值取向的一種選擇的話,而蔡元培先生的個人行為——人格獨立,則是對教育獨立價值取向的最好詮釋。
蔡元培先生從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十年有半”,對北京大學的改造,開創(chuàng)了中國教育的新紀元。但實際上他在校時間“不過五年有半”。而且,令人難以想象的是,從1917年7月3日始,直至1926年7月8日,他曾先后七辭北大校長而未獲準。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發(fā)布《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為了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便生出許多官僚的關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的公牘。”“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北京是個臭蟲窠。”從這“宣言”里,我們可以聽到蔡元培擲地有聲的立場和鐵骨錚錚的氣概;從這“宣言”里,我們可以看到蔡元培對教育獨立的捍衛(wèi),對思想自由的吶喊;從這“宣言”里,我們可以見出蔡元培不同流合污的高潔,對獨立人格的守護。
周恩來曾評價蔡元培,“從排滿到抗日戰(zhàn)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站在歷史的角度,蔡元培無疑是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民主平等、自由開放的先驅。思想自由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體系中有著獨特的地位和意義。在《大學教育》中,蔡元培明確提出,“大學以思想自由為原則”。而且,他認為思想自由唯有在大學方能得以實現,“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認,能完全實現之者,厥惟大學”。他進一步指出,大學教員擁有學術自由的權利是大學之所以能成為大學的根本所在。他說,“大學教員所發(fā)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掣。茍其確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同時并行,而一任學生之比較而選擇,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在北大,當時就有為鼓勵高深研究工作有效進行,并保證研究者學術自由權利的措施,“研究者進行學術討論有絕對自由,絲毫不受政治、宗教、歷史糾紛或傳統(tǒng)觀念的干擾。即使產生了對立的觀念,也應作出正確的判斷和合理的說明,避免混戰(zhàn)”。
由于蔡元培游歷歐洲,更有在德國學習與做研究的經驗,因此他受威廉·洪堡倡導“學術自由”思想影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讓人敬佩的是,在“素無思想自由之習慣,每好以己派壓制他派,執(zhí)持成見,加釀嘲辭”的中國,蔡元培將學術自由的思想扎根于北大,使其成為教育的理想與信條,成為追求真理的基石和動力,其產生的價值和意義可以任憑我們最大限度地去想象,去思考。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發(fā)刊詞》中,指明“所謂大學者,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
“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試看世界“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然而,“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常好以見聞所及,持一孔之論”。由此可見,若無學術自由,大學之價值何在?這就需要大學廣攬人才,接納不同的學術思想,自由發(fā)展。于是,如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周樹人、劉半農等倡導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如辜鴻銘、劉師培、黃季剛等政治上保守而學術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同處北大。著名歷史學家、北大教授鄭天挺曾撰文《網羅人才,領風氣之先》,對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做過介紹、分析。他認為,“大家常舉辜湯生、劉師培為例”,“但容易被人們誤解兼容并包只是包容反動落后人物”,“其實,這只是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一個小角,而且是極小的小角”。事實上,由于“過去中國學術上流派很多”,所以,“經學有今、古文學派的不同,蔡先生同時聘請了今文學派的崔適,也聘請了古文學派的劉師培”。“在文字訓詁方面,既有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黃侃、馬裕藻,還有其他學派的陳黻宸、陳漢章、馬敘倫。”“在舊詩方面,同時有主唐詩的沈尹默,尚宋詩的黃節(jié),還有宗漢魏的黃侃。”“在政法方面,同時有英美法系的王寵惠,也有大陸法系的張耀曾。”“其他學科,同樣都是不同學派兼容并包。”而這些正是“蔡先生在北大兼容并包的較多的一面”。還有如“章士釗創(chuàng)立邏輯的學名,北大就請他用《邏輯》開課;胡適和梁漱溟對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請他們同時各開一課,唱對臺戲。當時,很少學校開設世界語課程,北大開了,并附設了世界語講習班”。鄭天挺還特別提到,“1917年以后的幾年里,北大三十歲左右的青年教授相當多,其中不少人和蔡先生并不相識,而是從科學論文中發(fā)現請來的”。鄭天挺認為,“這是蔡先生兼容并包在北大的主要表現,也是最了不起的一面”。而且,有數據可以支持鄭天挺先生的說法,“據1918年初統(tǒng)計,全校(指北大)有教授90人,從可統(tǒng)計到的其中76個人的年齡看,35歲以下者43人,占56.6%,50歲以上者僅有6人,占7.9%。全校教授平均年齡30多歲,最年輕的文科新聞學教授徐寶璜,年僅25歲,劉半農、胡適,也僅二十七八歲。而這時北大本科生的平均年齡在24歲左右”。在鄭天挺看來,“北京大學所以能夠始終走在新思想新科學隊伍的最前面,未始不發(fā)韌于此”。
對延攬人才,蔡元培的確是不拘一格,梁漱溟先生顯然是親歷者——當然,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了。在《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一文中,梁漱溟說:“那時蔡先生以講師聘我亦非教授。不過我初到北大時,實只廿四歲,與諸同學年齒相若,且有比我大兩歲者。如今日名教授馮友蘭、顧頡剛、孫本文、朱謙之諸君皆當日相聚于課堂的。更有少時與我為同學友,而其時卻正求學于北大的。如雷國能(在法科)、張申府(崧年,在理科)諸兄是。”至于“當時蔡先生為什么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并且,“我既不屬新派(外間且有目我為陳、胡的反對派者),又無舊學,又非有科學專長的啊”。梁漱溟以為,“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覺到我富于研究興趣,算個好學深思的人,放在大學里總是好的。同時呢,他對于我講的印度哲學、中國文化等自亦頗感興味,不存成見”。梁漱溟認為,“這就是一種氣度。這一氣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學興趣相應而俱來的”。在梁漱溟看來,如果蔡元培“胸懷意識太偏于實用,或有獨斷固執(zhí)脾氣的人,便不會如此了”。無疑,“這氣度為大學校長所必要有的”。梁漱溟進一步指出,“老實說,這于一個為政于國的人有時亦同屬必要吧”!這或許就又有了另一層深意,也更耐人琢磨了吧。
正由于此,“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于后世”,梁漱溟先生如是說。
也正是這種兼容并包的胸懷與氣度,使北大各種人物、各種思想、各種聲音都可以同時并存,使北大形成了具有民主、開放、多元、自由、平等、包容等元素的現代大學教育范式,成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地標,并深刻影響了民國時期大學教育的風貌與樣態(tài),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提供取之不竭的寶貴資源。
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家約翰·杜威對蔡元培的評價可謂中肯:“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的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蔡元培先生教育獨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開民國教育之先河,樹民國教育之風氣,令人贊嘆。而蔡元培先生之人格與氣象,則令人景仰。毛澤東稱他為“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可見一斑。馮友蘭先生在《<蔡元培自寫年譜>跋——蔡先生的人格與氣象》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說到君子這個名詞,蔡先生可以當之而無愧。”他認為,“凡曾與蔡先生接觸過底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氣象,確可以此五個字形容之”。這里所謂的“五個字”,即孔子的君子氣象——溫良恭儉讓。馮友蘭最后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底表現”。此后,馮友蘭又在《我所認識的蔡孑民先生》中再次肯定蔡先生的儒家人格以及內在的精神境界——“極高明而道中庸。”蔣夢麟先生說:“蔡先生是中國文化所孕育出來的著名學者,但是充滿了西洋學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臘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中有記載,蔣夢麟在對北大學生演說時,講到了蔡先生的精神,謂:“(一)溫良恭儉讓,蔡先生具中國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蔡先生具希臘最好之精神。(三)平民生活,即在他的眼中,個個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來最好之精神。蔡先生這精神,是哪里來的?是從學問來的。”由于蔣夢麟與蔡元培之間的關系——先是師生(紹興中西學堂),后是同事(北京大學),我們選取蔣夢麟在《試為蔡先生寫一篇簡照》中的部分語段——
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兩字。知忠,不與世茍同;知恕,能容人而養(yǎng)成寬宏大度。
我們中國人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在不知不覺間不受老子的影響的,先生亦不能例外,故先生處事,時持“水到渠成”的態(tài)度。不與人爭功,不與事爭時,別人性急了,先生常說“慢慢來”。
在中國過渡時代,以一身而兼東西兩文化之長,立己立人,一本于此。到老其志不衰,至死其操不變。敬為挽曰:“大德垂后世;中國一完人。”
這些語段,進一步佐證了馮友蘭對蔡孑民先生的認識,也使我們看到人格氣象更為豐滿、完美的蔡元培先生。
在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里,追求“立德”“立功”“立言”是謂“三不朽”。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唐人孔穎達有對此三者的界定與詮釋,“立德謂創(chuàng)制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于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蔡元培先生之“不朽”,亦是實至名歸!
在《蔡先生不朽》中,蔣夢麟說:“先生死矣,而先生之精神不朽。”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學術自由之精神,“凡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悉聽其自由發(fā)展”;二是寬宏大度之精神,“先生心目中無惡人,喜與人以做好人的機會,先生相信人人可以成好人。先生非不知人之有好惡之別,但視惡人為不過未達到好人之境地而已”;三是安貧樂道之精神,“蔡先生安貧樂道,自奉儉而遇人厚,律己嚴而待人寬”;四是科學求真之精神,“先生嘗言,求學是求真理,惟有重科學方法后始能得真理。故先生之治北京大學也,重學術自由,而尤重科學方法。”
在蔣夢麟看來,科學求真的精神是蔡元培在“中西文化交接之際”“集兩大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學足以當之,其才足以擇之”。
重溫蔡元培先生的人生追求、教育理想,品讀蔡元培先生的人生境界、人格魅力,不能不感慨:世上當真已無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