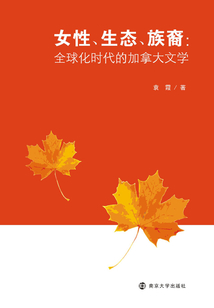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前言
作為一個“缺乏幽靈困擾”[1]的國家,加拿大在文學想象力方面似乎有所欠缺。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前的加拿大文學曾一度被視為一個缺失的概念,彼時許多加拿大人在談到文學時,要么把目光投向遙遠的宗主國英國,要么艷羨北緯49度邊境線以南的美國。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著名文學批評家諾思洛普·弗萊(Nothrop Frye)敏銳地觀察到,自己所解碼的深植于加拿大人意識深處的“邊哨心態”(garrison mentality)正在悄然瓦解,他已經或多或少意識到了“全球化”的萌芽以及加拿大文學的嬗變。弗萊在“《加拿大文學史》(1965年首版)的結束語”中寫道:
至少在過去的10年中,出現什么后美國文學、后英國作品,除了世界本身不能添上個“后”字外,什么東西都帶上個“后”了,我國的作家當然也在后加拿大文學的天地中從事創作。在飛機和電視的時代中,不再存在邊遠的省份,它們與所謂的文化中心也不再相隔開多少距離。人們的敏感不再取決于某個特定環境,甚至也不有賴于對經歷的感受。[2]
時間走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球化的腳步越來越近。作為一個有著多重意思的詞語,“全球化”成了一種“主要術語,用來命名、闡釋以及指導當代的社會和技術改變”[3]。“全球化”縮小的不僅是地理上的距離,還有文學與文學之間的差距。加拿大文學趁著全球化的東風,借助其特殊的地緣政治特色,開始走出邊緣角色。大批作家涌現了出來,首當其沖的是女性作家,她們鋒芒畢露,從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艾麗絲·門羅(Alice Munro)、艾麗莎·范·赫克(Aritha van Herk)到安妮·麥珂爾斯(Anne Michaels)等,其崛起之勢可謂銳不可當。這些女作家文風多變,或張揚或內斂,要么以厚重的文筆刻畫現代文明侵襲下的大都市里的人生百態,要么以小橋流水般的平淡筆觸描寫家長里短。她們書寫女性的故事,書寫人性的復雜,書寫自然與環境,書寫全球化時代欲望與倫理的交鋒。
加拿大文學的歷史雖然不長,卻有著關注自然環境的悠久傳統,加拿大聯邦詩人的自然詩就體現了人與自然的融合以及人對待自然的理性態度。琳達·哈欽(Linda Hutcheon)曾在其評論中指出,長久以來統治著加拿大文學的兩個話題是“身份及人與自然的關系”[4],可見自然和生態主題在加拿大文學中的重要性。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延續了對“人與自然”的探討,作家們用詩歌、小說和文集等多種形式來表達保護環境的愿望,同那些利用全球化的幌子掠奪他國文化和他國資源的行徑做斗爭,并借此告誡我們,人類對自己居住的星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只有與自然保持和諧的關系,我們才能擺脫危機的困擾,從腳下的土地獲得源源不斷的快樂。
在加拿大文學的發展軌跡中,“多元文化主義”法令的實施(1988年)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多元文化主義對重新闡述加拿大的身份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個最直接的后果是原先處于社會邊緣的少數族裔作家激增,作品中種族和民族等與身份有關的問題占據著重要地位,加拿大文學呈現出多樣化特征。這些變化一方面表明加拿大文化實現了一個較大的轉向(對族裔寫作政策更加寬松),另一方面意味著民族身份和加拿大文學構成等老問題正在經歷重新定位,在文明多樣性的全球化版圖中呈現出新的特征。
本書通過女性、生態和族裔三個層面,對全球化時代的加拿大文學進行探討。全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后殖民語境下的女性書寫的分析。該部分首先概述了當代英語女作家的崛起之路,從加拿大當代女作家發展的四個時期(20世紀六七十年代、80年代、90年代及2000年至今)入手,主要通過小說這種文體來探討她們在后殖民語境下所關注的問題,思索女性在后殖民社會中的生存環境。接著,該部分聚焦于加拿大兩位重量級英語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和艾麗絲·門羅,分別對她們作品中的“百衲被”意象和階級意識進行討論。阿特伍德利用“百衲被”這個重要的隱喻和意象探討了女性應該如何創建屬于“自己的語言”,指出了女性只有拋棄男性敘事霸權,才有可能堅持自身的主體性,建立女性之間的同盟。門羅鐘情于描寫生活在底層的女性,不少作品刻畫了“灰姑娘”、“乞丐女”和“幫傭女”形象,展現其最熟悉的中下階層群體的生活狀況,真實地體現了她的階級觀。該部分還通過文本細讀的方式,對《遠離埃爾斯米爾之地》、《帳篷》、《珀涅羅珀記》、《石床墊》、《最后死亡的是心臟》、《女巫的子孫》、《洛克堡的風景》和《太多快樂》展開分析,從“互文性與對話”、“女性主題”、“神話重述”、“家族史”等視角來探討兩性之間的倫理困境。而該部分最后一章提出了一個總結性的問題:“何處是歸宿”——敦促我們思考全球化語境下的性別議題。
第二部分著眼于人類世語境下的生態文本與動物書寫。2016年8月底,在南非開普敦召開了第35屆國際地質大會,地質專家依據核彈實驗放射物在巖石和沉積物中留下的印跡,將1950年定為“人類世”(Anthropocene)的肇端。這一術語的提出和應用意味著人類活動對地球生態系統的影響已達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對人類與地球以及文化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反思刻不容緩。這部分首先奏響了生態危機下的“四重唱”,介紹了唐·麥凱(Don McKay)、迪·勃蘭特(Di Brandt)、唐·多曼斯基(Don Domanski)和迪翁·布蘭德(Dionne Brand)這四位當代加拿大著名生態詩人。他們憑借敏銳的觸覺,用獨特的聲音為世人敲響了生態環境危機的警鐘。緊接著,該部分一一分析了《償還:債務與財富的陰暗面》、《一個拓荒者的漸趨瘋狂》、《洪疫之年》、《瘋癲亞當》和《最后死亡的是心臟》中的生態思想,批判現代社會崇尚技術、壓制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態度。該部分還總體闡述了加拿大文學中的動物倫理學思想及其當代價值,并針對艾麗絲·門羅的南安大略哥特式小說、《羚羊與秧雞》中的全球化危機以及《與狼共度》中的動物權利和環境保護進行探討,指出動物和女性一樣,是人類世語境下的弱勢群體,是需要關懷的對象。
本書第三部分主要關注多元文化語境下的民族敘事和族裔書寫。全球化時代(尤其在進入21世紀后)的加拿大文學繼續探討人口多樣化帶來的社會多元化和文化差異等問題,“這些作品直面法語與英語,北方與南方,土著、殖民者與移民文化,國家與個人,不同種族、性別和階層之間的沖突與融合”[5]。該部分首先展現了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在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植根故土,情牽世界”的民族情懷,接著通過《荒野小站》中的民族國家敘事、《冬日墓穴》中的家園意識、《蘇庫揚》中的加勒比流散、《龜背》中的環境種族主義以及《放血與神奇治愈》獲得吉勒獎之后引起的爭議,引出“多元文化主義何去何從”的話題。從這一時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主流作家關注的面變得更加寬廣;原住民文學更為重視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問題;移民作家利用其文化背景和體現其經歷的敘事范式,為文學傳統做出了貢獻。
此處需要聲明的是,本書的所有章節均來自筆者發表過的論文,筆者在每一章的引文部分做了說明,注明了原論文名、論文發表的期刊名、時間以及頁碼范圍。通過對這些論文的整理,筆者似乎看到了自己在學術之路上的修煉與堅持。有些早年發表的論文隱隱透出稚嫩的文筆,在此敬請各位讀者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