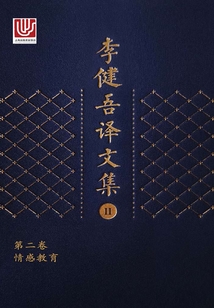
李健吾譯文集·第二卷
最新章節
書友吧 3評論第1章 初版譯者序[1]
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六日,福樓拜完成了《情感教育》的五年的持續工作,就在七月十八日,他的最好的朋友詩人布耶(Louis Bouilhet)過世。然而傷痛還在心里,緊接著十月十三日,批評的權威圣佩甫(Sainte-Beuve)也死了。眼看十一月十七日,這部期待甚久的現代生活的巨著就要在書肆應世,福氏寫信給朋友道:
又是一個去了!這一小隊人馬越來越少了!麥杜絲[2]木筏上的難得逃出性命的幾個人也不見了!
如今和誰去談文學?他真愛文學——雖說不就可以完全看做一位朋友,他的棄世讓我深深地難過。凡在法蘭西執筆為文的人們,都由他感到一種無可彌補的損失。
在文壇得到一位相知像圣佩甫那樣深澈、明凈、淵博而又公正、有分量,所以輕易也就不許給人,不是人人可以遭逢的機遇。他曾經把最高的評價許給《包法利夫人》和《薩郎寶》。對于前者,他唯一的指摘是“沒有一個人物代表善良”,他舉了一個他熟識的外省婦女,證明“外省和田野生活之中有的是這類好人,為什么不把她們寫給大家看?這激發、這安慰,人類的形象因之而更完整”。對于后者,他嫌它的背景太遠了,雖說“尊重藝術家的志愿,他的一時的喜好”,他要求作者“回到生活,回到人人可以目擊的范疇,回到我們的時代的迫切需要,那真正能夠感動或者引誘時代的制作”。所以臨到一八六四年,開始從事于《情感教育》的寫作,福氏牢牢記住前輩的指示或者熱望,回到他們共有的相關的時代,同時從自己的經驗另外發掘一個善良婦女作為參證。《情感教育》是作者虛心接受批評的出品。
但是圣佩甫偏巧早死了一步,所以福氏寫信給他的外甥女傷心道:
我寫《情感教育》一部分是為了圣佩甫。他卻一行沒有讀到就死了。布耶沒有聽到我念最后兩章。這就是我們的計劃!一八六九年對于我真夠殘忍了!
那位善良婦女應當就是《情感教育》里的阿爾魯夫人。她代表法國中產階級大多數婦女,也象征我們三從四德的荊釵布裙。她識字,她也讀書,不曾受過高等教育;她的品德是生成的,本能的,所以深厚;她有鄉婦的健康、愿愨,和鄉婦的安天樂命、任勞任怨。一個小家碧玉,然而是良家婦女。沒有包法利夫人的浪漫情緒,也沒有那種不識世故的非常的反動,她是一個賢內助,一個良妻賢母,而她的丈夫卻是一個粗俗淺妄又極不可信賴的畫商市儈阿爾魯。她會忍受風雨的摧殘,厄運的變易,和子女靜靜地相守,還要分心來慰藉男子的負疚的暴戾之氣。她是中產階級的理想,中產階級婦德的化身。
她在最后接受了一個情人,只是一個,因為她的丈夫的顢頇傷害她的信心,她的尊嚴,因為她的年輕的情人是那樣執著,那樣懦怯,那樣經久不凋,然而生性忠實,在不可能獲致物質與精神一致的時候,愛情可以析而為二,死生如一:平靜,沒有危險性,不感到矛盾,因而也就異常強韌永恒。她可以原諒丈夫有情婦,不原諒他毀壞子女的前途,她可以原諒情人有情婦,因為他們誰也不會屬于誰。男女之愛在這里具有更多的母愛、姊弟之愛和忠誠的友誼:只有靈魂在活動。物質的貪婪不息而自息,肉欲的沖動不止而自止,心在這里永久是潔凈的。
福氏用不著到遠地方尋找這樣一位善良婦女,如圣佩甫在一封給他的信里所形容,和包法利夫人“同樣真實的人物,而情愫卻溫柔、純潔、深沉、蘊藉”。老早,老早就有一位阿爾魯夫人密密護封在他的感情和生活之中。她的夫姓是施萊新格(Schlessinger),父姓是福茍(Foucault),名字叫做愛麗薩(Elisa)。施萊新格是一個德國人,在巴黎開了一家商店,專做音樂繪畫以及其他藝術上的交易,為人正如小說里的阿爾魯,可能比阿爾魯還要惡劣,曾經盜印羅西尼(Rossini)的《圣母痛苦曲》(Stabat Mater),福氏在上卷第五章為了點明時代(一八四二年一月)順手拾來做為一個標記。福氏和他們相識,是在一八三六年八月,不過十五歲,隨著父母在海濱的土鎮(Trouville)消夏。土鎮在當時是一個“荒涼的海濱,潮退下去,你看見一片廣大的海灘,銀灰的沙子,濕濕的和浪水一樣,迎著太陽熠耀。左面有些山石,貼著一層水草,全變黑了,海水懶懶地打著;往遠看,在熾熱的日光之下,是蔚藍的海洋,沉沉地吼號,好像一個巨靈哭泣”。他在這里遇見那所謂的施萊新格夫人,所謂,因為如翟辣·喀義(Gérard Gailly)所考據,她的真正的合法丈夫另有一個,不出面,也不抗辯,沒有人清楚是為了什么不得已的苦衷。直到這位姓虞代(Judée)的神秘的緘默的丈夫在一八三九年死后,施萊新格夫婦才算有了正式的名分[3]。
但是昧于一切,福氏陷入初戀的痛苦。他發狂地愛著這位諱莫如深的少婦。她最先走進他的情感,也最后離開他的記憶。這是純潔的:
我曾經愛過一個女人,從十四歲到二十歲,沒有同她講起,沒有碰她一碰;差不多之后有三年,我沒有覺得我是男子。[4]
這是命:二十年以后,施萊新格在巴黎站不住腳,去了故國,福氏在信里告訴施氏夫人:
命里注定,你和我的童年的最好的回憶連在一起。[5]
然而這是神圣的:
我如今依然是怯怯的,如同一個少年,能夠把蔫了的花藏在抽屜里面。我曾經在年輕時候異常地愛過,沒有回應地愛過,深深地,靜靜地。夜晚消磨于望月亮,計劃誘拐和旅行意大利,為她夢想光榮,身體與靈魂的折磨,因肩膀的氣味而抽搐,于一瞥之下而忽然蒼白,我全經過,仔仔細細經過。我們每人心里有一間禁室,我把它密密封起,但是沒有加以毀壞。[6]
這間禁室他終于換了一個藝術方式啟封,那就是他的《情感教育》。他從他的自身經驗尋求真實,并不違背他對于藝術作品的一貫的無我的主張。他拿自己做材料,然而在小說里面,并無一行字句出賣他的隱私。如若不是因為他的造詣卓越,如若不是由于后人苦心鉆研,我們止于表現本身的欣賞,這些加深了解的索引也許永遠湮滅。這里是“一個青年的故事”,這個青年并不等于作者,但是含有若干成分,即使清醒如福氏,往往不一定就能夠徹頭徹尾加以分析。
毛漏的情感教育在本質上即是福氏的情感教育。但是毛漏不就是福氏。這是一個天性不純,稟賦不厚,然而一往情深的習見的青年,良弱,缺少毅力。他追求理想,甚至于理想的憧憬,同時他可以縱情淫欲,這里是種種由反動而生的交錯為用的心理。正如福氏所謂的“若干力”:
你不見她們全愛阿道尼斯(Adonis)嗎?這是她們要求的永久的丈夫。寡欲也罷,多欲也罷,她們夢想愛情、偉大的愛情;要想醫好她們(至少暫時地),不是一個觀念就可以見效,而必須是一種事實,一個男子,一個嬰兒,一個愛人。你也許以為我太刻薄。然而人性不是我創造下來的。我深信最猛烈的物欲是由理想主義的飛躍于不知不覺之中組成,而最齷齪的肉的淫亂是由于一心指望不可能,仰望神貴的歡悅而產生。再說,我不懂(也沒有人懂)這兩個名詞的意義:靈魂與肉體,一個在這里完結,另一個在這里開始。我們感到若干力,如此而已。[7]
相為因果,互為消長,精神與物質并非兩種絕然不同的形體。所有福氏創造的男女主角,包法利夫人,薩郎寶,從這種心理的角度去看,環境個別,過程相同。毛漏屬于同型。阿爾魯夫人的指尖輕輕拂了他一下,毛漏立即盼望和他的妓女晤對,然而在一起了,心有所動,他馬上想起他的偉大的愛情。屬于常人,無論男女,活在“若干力”的迸擊之上,終為火花銷鑠。福氏的朋友杜剛(Du Camp)有一部小說叫做《力的浪費》(Les forces perdues)同樣可以移來作為《情感教育》的標題。毛漏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理性和獸性只是他的存在的真實的兩種應用。不是一個苦修僧精神全然向上,也不是紈绔子弟的純物質的沉溺。這里是一個中產階級的青年愛上一個中產階級的婦人:缺乏毅力沖出社會的囚籠,更其缺乏毅力跳出自己的溫情。他們接受人世的命運,念念不忘各自在人間應盡的職分。中產階級的品德是自私,愛也是自私。
福氏是一位理想主義者,所有大作家難得一個例外不是,然而深深打入他的時代和階層,卻又百分之百地現實,臨到具體攝取形象、綜合(不是象征,那可憐的沒有血肉的稻草人)是他的穎特的成就。典型就是這樣產生的,這樣活在世紀之中而不朽的。哈穆萊特(Hamlet)、哈巴貢(Harpagon)、白特(Bette)、奧布勞冒夫(Oblomov)……都含有各自的作者,然而含有更多的人性。
了解毛漏這樣的青年,等于了解中產階級。自私,然而卻不就是自私。毛漏一向慷慨,一向熱衷。許多人慷慨而又熱衷,具有經驗以及從經驗體會出來的處世哲理,并非毫無區別地兼善。毛漏不然,這是一塊軟面,隨心所欲,由人揉搓。他沒有鮮明的人格;他的人格富有彈性,像一張琴,人人可以彈出自己所需要的共鳴,然而不是毛漏自鳴。他會將別人的撥弄看做自主,天賦獨厚的音籟。不認識自己,他以為認識;他把一時的習染誤做天才的流露,因而自負過高。他逗留在事物的表皮,永久吸入現象,永久默默無聞,富有流動的接受性,沒有比他易與的人,仿佛河床的污泥,一波一波流過,依然故我,在河床沉淀、淤積。他在急湍之中回旋,以為是自己波動:他或許有動的意識,他當然有,而且很多,然而從來沒有形成一種意志,一種活力。他有計劃,也高自期許。他寫詩,因為他多少讀了一些浪漫詩歌;他學畫,因為阿爾魯是畫商;他想做新聞記者,因為戴樓芮耶向他借錢辦報;他想做議員,因為黨布羅斯慫恿。他“由于一種問心不過的榮譽觀念,保持著他文學的計劃。他想寫一部美學史,這是他和白勒南談話的結果;隨后又想把法蘭西大革命的各個時期寫成悲劇,另外制作一出大喜劇,又是由于戴樓芮耶和余掃乃的影響”。東沾西染,似有所悟,未能深入,便又見異思遷。像一個票友,有票友的怯怯的驕傲;他東張張,西望望,來到人生盡頭,發現自己一無所獲,受盡情感的欺蒙。然而這樣庸庸碌碌,旁觀者一樣放過花花綠綠的人生,于是和他的老朋友戴樓芮耶碰在一起,談到他們過去得意的辰光,幾乎只是一片空白。
狄德羅(Diderot)曾經在十八世紀創造了一個同樣落伍的人物,然而和毛漏一比,拉摩(Rameau)[8]顯然還有一點火氣,他可以撕破面具,無所顧忌。毛漏只是一個中小產階級,有廉恥,有虛榮,吃著小小的利息,決不忿而有所作為。他懣,然而他不忿,所以同是一事無成。拉摩近乎男性,陽剛、反抗,于是孤獨;毛漏近乎女性,陰柔、順受,不愁沒有朋友。一個怨恨,一個愛,而且被愛。從這一點來看,雖說沒有大觀園加以隔離,他也只是一個賈寶玉。他得不到男子的敬重,他爭到女子的眷顧:女子崇拜英雄,然而溺愛弱者。《紅樓夢》實際只是一部情感教育。和拉摩相近的倒是包法利夫人,挽不住狂瀾,然而追尋機會,失望、絕望、掙扎、自盡。毛漏不挽自住,失望、永久失望,但是無聲無臭地活下去,福氏序布耶《遺詩》道:
幻滅是弱者的本色,不要信任這些厭世者,他們幾乎永遠無能為力。
毛漏不會尋死,正如賈寶玉,至多一走了之。死也要用力。還有悲劇比這更其沉痛的?
還有人物比這更其起膩的?
所有批評家對于《情感教育》的指摘和誤解,幾乎都和毛漏本人有關。喬治·桑(George Sand)極力為作者辯護,仍然以為“錯處就在人物缺乏掙扎。他們接受事實,從來不想據為己有”。后人如法蓋(Emile Faguet),便直截了當以為《情感教育》起膩,由于主要人物本身無聊。布雷地耶(Brunetière)的攻訐更為徹底:
如今正相反,你想絕對現實,如左拉先生所謂:“你投到生存的庸俗的行列。”——為了你的報章英雄,為了你的傳記熱狂的殉難者,你選了一個人物,我承認,“在日常生活的簡單中,”我們一打一打地遇見,沒有職業,沒有地位,尤其是,缺乏個性;你選了這樣一個人物以后,即令你精于觀看與呈現,觀察與描繪,掘發事物與運用語言:你令人起膩。一切持續不斷的東西令人起膩。我用唯一光榮的例子來證明,只要念過福樓拜先生的《情感教育》的人們全都回憶一下就成了。你也許問,何以這種枝節的持續令人疲倦,何以不得不有這種選擇的必要?回答在如今并不難:因為在人生之中,理應如是的事務實際并不如是。我們需要一點理想。[9]
這種傳統的看法,把小說當做傳奇,把主人公當做英雄,雖說在民間一直流行,畢竟過于陳腐。現代小說所含的本質幾乎千百倍于《情感教育》的平凡,《情感教育》只是一個重要的開端。什么是現代小說的特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們不妨借用布雷地耶的詮釋:
是人生,共同的人生,附麗于環境的人生的表現,“未經選擇”的人生,假如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又不為任何學派的成見所限制;嵌在它的現實框架之中的人生,被觀察、被研究、被表現于你可以叫做人生的無限瑣細之中,猶如有時顛覆人生的重大危機之中;永久如一的人生,然而永遠被自身的發展的唯一無二的效果所修正,就外表看來是,而且將長時間是,小說的獨有的特殊的目標。[10]
假如布氏無以調和他的觀察和觀點,福氏在寫作期間未嘗沒有體驗到其間的矛盾:
這是一本關于愛情、關于熱情的書;一種可以生存于今日的熱情,這就是說,消極的熱情。所想象的主旨,我自信是十分真實,唯其如此,不大解悶也難說。有點兒缺乏事變和戲劇;而且時間過長,動作未免松懈。總之,我很不放心。[11]
在另一個時間,福氏說起他的苦悶,并不因而改變他對于近代生活的認識:
這樣的人物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嗎?偉大的效果需要簡單的事物、明顯的熱情。然而在近代的世界,哪里我也看不見簡單。[12]
他寫了一個尋常人,一個復雜人,一個活在繁復緊張的大時代的無名小卒。毛漏不是英雄。福氏也不是在寫傳奇。他似乎已經預感《情感教育》不易于被同代人士所接受,然而藝術良心不許他作偽,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如若他必須忠實于人生,忠實于藝術,忠實于近代,忠實于自己。他為這個大感苦惱。他往前多走了一步;他也許沒有想到這上面;然而他痛苦;然而他不認輸:
把我的人物和一八四八年的政變穿插在一起,我很感棘手;我害怕背景吞下全書的結構,這也正是有歷史性質的作品的毛病;和小說里的人物相比,歷史上的人物更易于引人注目,特別遇到前者的熱情不很激昂的時候;人家覺得拉馬丁(Lamartine)比毛漏有趣多了。再者,在現成的事實中間,選擇什么好呢?我簡直是心煩意亂,也就真夠苦的![13]
不僅毛漏沒有歷史的圓光相襯,全部小說的人物都是平常而又平常,渺小而又渺小,然而屬于時代,屬于生活。
無論如何,福氏如圣佩甫所囑望,在《情感教育》里,“回到生活,回到人人可以目擊的范疇,回到我們的時代的迫切需要”。他為自己選下一段他年輕時候親眼看見的第二次革命做背景,一個人人可以印證的曇花一現的浮動的大時代,對于法國有影響,沒有成就。他曾經就《力的浪費》指出道:
這有好些地方類似我的書。他這本書極其老實,對于我那一代人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因為我那一代人,和現在年輕人一比,變得真和化石一樣。一八四〇年的反動,挖了一道深溝,將法國隔而為二。[14]
他采用這動亂的時代,不是由于同情二月革命,而是從一個藝術家的眼里看來,由于革命本身的進行的形式的瑰麗。我們明白,福氏不相信任何革命。因為往長里看。社會主義者往往陷入同樣狹小、同樣只是人類進展之中的一個形體。這種哲理觀點,對于了解《情感教育》具有無比的重要性:
正因為我相信人類永久的演進與其無窮的形體,我恨所有的框架,拼命把它裝鑲進去;所以我恨一切限制它的程式,一切為它想出來的計劃。奴隸制度不是它最后的形式,封建制度更不是,君主政體更不是,便是民主政體也不見得。人眼所望見的天邊決不是盡頭,因為在這天邊以外,還有別的天邊!這樣以至于無窮。所以訪求最好的宗教,或者最好的政府,我以為是一種蠢極了的舉措。對于我,最好的也就是垂危的,因為要給別一個挪出位子來。[15]
悲觀是福氏一切寫作的基調。這不妨害他清醒,因為說到最后,理想主義的依據即是悲觀,對于藝術家,重要更在方法和態度的選擇。福氏的精神是謹嚴,選擇客觀和觀察作為敘述的準則:
你反對人世的偏私、它的卑鄙、它的暴虐,同生存的一切齷齪與猥褻。但是你認清它們了嗎?你全研究過嗎?你是上帝嗎?誰告訴你,人的裁判不會錯誤?誰告訴你,你的情感不會欺騙你?我們的感覺是有限的,我們的智慧是有窮盡的,我們如何能夠獲有真與善的絕對的認識?我們會有一天曉然于絕對的存在嗎?你要是打算活下去,無論關于什么,你就不用想有一個清晰的觀念。人類是這樣子,問題不在改變,而在認識它。[16]
這顯然只是一個藝術家的立場,而且正和傳統的帶有虛偽意味的學院論調違忤。你沒有權利刪削,假如人類原來就有這種形象。對于藝術家,丑陋猶如美麗,本身含有美麗。你觀察,你選擇,不是因為你有道學家或者宗教家的熱情,而是因為你活在現代,要有科學家的誠懇:
依照我,小說應理科學化,這就是說,追求或能的普遍性。[17]
政體搖動,物體瓦解,自然而然呈出一種復雜的崩潰局面,現象本身需要詳密的分析,現象與現象之間的關聯尤其重要。福氏自己曾有一個譬喻:
珠子組成項圈,然而是線穿成項圈;為難的,就在一只手要穿起珠子,不許一粒遺失,另一只手還要握住了線。[18]
藝術在這里和科學形成一個完美的整體。無善無不善,無大無小,在人類歷史的進行上,合成一股澎湃的氣勢,木石不分,連水帶泥,流向永生的大地。《情感教育》是在這樣的美學觀點之下切開的人類活動的片段,精神上永遠只是一個。
這是科學帶給我們的一種新的認識,一種對于浪漫主義的修正,把唯我心理從筆尖剔開,讓宇宙以本來面目在文字之間和我們重新接識。《情感教育》之不為傳統的批評所認可,這里劃著一條理解人生的鴻溝。福氏自己分析它的失敗:
這缺乏透視的虛偽。因為用心組合結構,結構反而消失。一切藝術品全有一個點兒,一個尖兒,和金字塔一樣,或者叫陽光射在球的一點。然而在人生里面,就沒有這回事。不過藝術不是自然。[19]
他的謙虛使他在最后駁斥自己。但是年輕人,一批又一批的后進,促成現代小說的大流,走出學院批評,正如他之走出傳統觀點,把《情感教育》看做他們進軍的指南。邦維勒(Banville)[20]紀念福氏去世,首先指出它在現代小說里占有的重要地位:
……然而他走的還要遠;在《情感教育》里,他必須先期指出未來的存在:我的意思是說,沒有小說化的小說,和城市本身一樣地憂郁、迷模、神秘,而且和城市一樣,以可怖的結尾為滿足,唯其結尾并非物質上地戲劇的。[21]
它把小說帶出一個陳舊的形體,走上另一個方向,一個現代小說共有的方向。這慢慢地,隱隱地,為現代開辟了一塊新土地。甚于《包法利夫人》,后進把《情感教育》看做他們的圣書,尤其是自然主義者群。古爾孟(Gourmont)贊美它:
在藝術上,只有小孩子和不識字的人們對于主旨感到興趣。什么是法國語言最美的小說——這部《奧狄賽》(Odyssée)——《情感教育》的主旨?[22]
沒有主旨,他一語道破福氏的小說趨勢,現代小說的趨勢。這在一九〇二年。三十年后,賴翁·都德[23](Léon Daudet),一個并不太喜歡福氏的晚輩,自問自:
什么是法國語言寫成的十九世紀小說,公認的杰作,美麗,而又有影響于文壇?
那是《情感教育》。它的名聲逐日上漲,臨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處處虛偽狂妄,欺人又欺己,人人如逢故友,批評家把《情感教育》看做作者最高的成就。
在這一八四八年貌似偉大的時代,多少人小產、流產,或者無所產!吃苦,受氣,沒有名,缺錢用,誰不想做出什么來,誰又做出了什么來!誰又敢說高誰一等,不負當年的夸口,友朋的推許?這樣、那樣,臨了還不都是一樣!形形色色,幾乎全有一個代表在小說里活動,一個一個,仿佛一堆漠不相干的群眾:你推搡我,我推搡你;你利用我,我利用你;你閃在我的身后,我閃在你的身后;我推翻你,踏過你的背脊,你扳轉我,登上我的胸脯;老實人被犧牲,狡黠者受擁戴。摔下來又爬上去,爬上去又摔下來;前趕后,后趕前,然而逃不出一個“踏步走”,動而不進。各人有各人的夢想,難得一個夢想成為事實。你想做這一件事,結果你做了另一件事。你愛這一個人,卻不得不睡在另一個人的枕畔。你以為害他,反而成全了他;你以為成全他,反而害了他……“你相信這會有什么結果嗎?不要做夢了,一天一天過去,幾件事是有結果的?”人生不是一出圓滿的戲。今天你在茶館遇見他,再去你就遇不見他,隔些年你忘記了,偏偏你又遇見他。什么樣平凡、幻麗而又正常的人生!怎樣的巧合!怎樣的巧離!肩摩肩,踵接踵,這一個從小巷溜出來,那一個從小巷溜進去,全又走在相同的單調而又喧豗的人行道上。
茫茫一片灰色,偶爾在這中間看見一點粉,一點綠。
福氏以一個藝術家的心情喜愛人群的騷動,因為這里有詩,有形象的美麗,有闊大的波瀾。然而往里看,這是一種力量,并不就是一種可靠的智慧:
人類愚蠢的舉動,同人類一樣永久。我相信人民的教育與窮苦階級的道德全是將來的事。致于群眾的智慧,我否認到底,因為無論如何,這永久是群眾的智慧。[24]
群眾并不堅牢,甚于水性楊花的婦女,甚于人情世故的友誼,最是接近忘恩負義。活在今天,福氏或許要相當地修正他的見解,然而他和易卜生(Ibsen)屬于同一時期,對于群眾和社會主義具有不小的戒心。為了寫作《情感教育》,他研讀所有社會主義者的書籍,得到的印象僅僅是:
有一件事觸目極了,把他們連在一道:就是憎恨自由,憎恨法國大革命與哲學。他們全是中世紀的老實人,陷于過去而不可自拔的人物。而且何等村學究氣!學監氣!好比道士喝醉了酒,掌柜樂暈了過去。如若一八四八年他們沒有成功,全因為他們來在偉大的傳統之流以外。[25]
如今讓我們回到《情感教育》,我們將在這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即使是在中國,也都熟熟的,似乎見過,聽說過。
誰不是見異思遷的毛漏?孩子氣十足的西伊?循規蹈矩的馬地龍?我們難道沒有戴勒瑪爾,裝模作樣,貌若無人,永久是“一只手放在心上,左腳向前,眼睛向天,他的鍍金桂冠套在他的風帽上,用力往他的視線放進許多詩意,來勾引貴夫人們”。小報回頭捧成了救國明星。我們難道沒有羅染巴,成天到晚,酒館一坐,借酒澆愁,滿腹牢騷,問急了,便是他的“萊茵河”的口號。我們難道沒有白勒南,開口藝術,閉口勢利,一幅畫三分不像人,七分活像鬼,高唱藝術革命,向臨時政府請愿,成立一個類似交易所的藝術公會。我們難道沒有余掃乃,浪子文人,專辦短命的蚊子小報。我們難道沒有法提臘斯女士,打起婦女參政的旗幟,捧無聊的戲子,而且睚眥必報,不愧一個婦女先進。像那搖身三變的老政客,老奸巨猾的黨布羅斯,我們難道沒有看夠!革命的前一日還是保皇黨,后一日連腮幫子都掛滿了主義。和他相反,和他一樣善變,我們難道沒有看夠比比皆是的賽耐喀,你可以罵他狼心狗肺,你可以夸他鐵面無私,一朝人民嫌他獨裁,踢他下臺,他會成為皇室走狗,刺死大好人杜薩笛耶,唯一可以稱為英雄的老百姓。
隔著萬頭攢動的人海,是貧賤與富貴兩岸,雖說波浪滔天,人從卑微到發跡辟了兩條航線,一個是金錢,一個是政治。承繼遺產的毛漏,勿須株守鄉間,勿須苦學博名,他可以回到都市,稱心如意,為所欲為,黃金一直鋪平黨布羅斯的高石階,笑臉和毛漏相迎。他有幸運不勞而獲。這正是他和窮朋友分手的因由。他滿足,他自足,革命對于他只是一首好聽的短歌,然而對于別人,唯有政治斗爭,唯有革命,才能補足命運的虧欠。是什么堵住了他們上進的道路,是誰這樣霸道,這樣殘酷?
他們彼此同情。先不說他們對于政府的憎恨達到一種不容討論的教義的高度。
他們不能不革命,這是他們唯一自救以救人的道路。我們看到賽耐喀,一個工頭的兒子,戴樓芮耶,一個衙役的兒子,另外杜薩笛耶,一個無家可歸的私生子,然而各不相同。毛漏承繼了一筆產業,杜薩笛耶道喜,賽耐喀認為墮落,戴樓芮耶居為奇貨,后兩位有若干地方相同,嫉妒是其中之一。他們需要統治,同樣失之于刻。得到我們敬愛的,只有一個,就是心地單純、見義勇為的學徒,傻小子杜薩笛耶。他沒有學問,尊重學問;他要革命,不是由于野心,由于欲望,是因為法國袖手旁觀,不援助弱小民族。他知道感激,賽耐喀一流革命家缺乏的美德。毛漏的朋友當中,不打他的算盤的,只有這么一個人。他愿人人成功,從不居功。他屬于《雙城記》里的賈爾通(Sidney Carton)一類的英雄,死于他的所愛,不是一個有夫之婦,而是整個被壓迫階級。他不投機,別人爬上去再跌下來,再爬上去,他永遠只是自己。他盼望革命,他支持革命,革命來了,停也不停變了質,又去了,他得到的只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夢想。賽耐喀變節了,戴樓芮耶變節了,這頭腦簡單的可愛的窮孩子陷入絕望,然而始終如一:
……長此以往,我會發瘋的。我倒情愿人家殺了我。
他終于叫一個警官、他舊日的同志賽耐喀,殺了,直到死,他喊著:
——共和國萬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