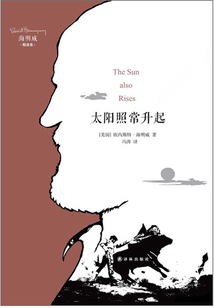
太陽照常升起
最新章節
書友吧 16評論第1章
第一節
羅伯特·科恩曾是普林斯頓的中量級拳擊冠軍。別以為我會拿一個拳擊冠軍的頭銜太當回事,不過這對科恩來說可就意義重大了。他并不喜歡拳擊,事實上他討厭它,可他滿心痛苦又一心一意地學著打拳,以此來抵消他身為一個猶太人在普林斯頓感受到的自卑和羞怯。知道能把任何一個瞧他不起的家伙打倒在地,讓他心底里覺得相當安慰,雖說他本身是個很害羞又很厚道的小伙子,除了在健身房里,從不跟人打架斗毆。他是斯拜德·凱利的明星學員。斯拜德·凱利把他手下所有的年輕紳士都照次輕量級[1] 拳擊手的模式來訓練,不管他們的體重是105磅還是205磅。不過這辦法看來很適合科恩。他的出拳速度確實很快。他進步如此神速,斯拜德于是馬上安排他跟高手過招,結果他終身落下了個扁鼻子。這使科恩更加厭惡打拳了,不過也給了他一種異樣的滿足感,而且他的鼻子確實也更好看了些[2] 。在普林斯頓的最后一年,他書讀得太多了,結果戴上了眼鏡。我碰到過的他的同班同學中,沒有一個記得他,他們甚至不記得他曾是什么中量級拳擊冠軍。
我對所有貌似坦率和單純的人統統信不過,尤其是他們的故事編得格外圓乎的時候。我一直就懷疑羅伯特·科恩從來就沒得過什么中量級拳擊冠軍,他那個鼻子也許是被一匹馬給踩扁的,要么也許是他媽媽懷著他的時候受了什么驚嚇或是看到了什么精怪,再要么也許是他小時候撞在了什么東西上,可最終還是有人向我證實了科恩的經歷并非是瞎編,此人正是斯拜德·凱利本人。斯拜德·凱利非但記得科恩,他還時常惦記著他這位得意門生后來到底怎么樣了。
羅伯特·科恩的父系是紐約最富有的猶太家族之一,母系又是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他進普林斯頓前的大學預科是在一所軍校讀的,他是校橄欖球隊出色的邊鋒,沒人使他產生什么種族意識,甚至沒人使他覺得自己是個猶太人,所以他也就沒覺得跟任何人有任何不同,直到他進了普林斯頓。他是個厚道小伙子,是個友善的年輕人,而且非常害羞,這就更使他覺得痛苦不堪。他就通過打拳來發泄,最后帶著痛苦的自我意識和一個被打扁了的鼻子從普林斯頓畢業,跟第一個好心待他的姑娘結了婚。他結婚五年,生了三個孩子,把父親留給他的那五萬美元揮霍殆盡,遺產的其他部分歸他母親所有。這些年來,跟一個富有妻子的不幸福家庭生活把他的脾氣消磨得相當討人厭;等他終于下定決心要離開他妻子了,她卻先一步把他給甩了,跟一個微型人像畫家跑了。好幾個月來他一直考慮要離開他妻子,卻又覺得就這么把她給拋棄未免過于殘忍,所以并沒有付諸行動。她這么一走雖大出他意外,卻也大有益處。
離婚手續辦妥以后,羅伯特·科恩動身去了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亞,他混跡于文人圈子里,他那五萬美元尚有少量剩余,很快他就拿來支持一家文藝評論雜志。這家雜志創刊于加利福尼亞的卡梅爾,在馬薩諸塞的普羅溫斯敦[3] 停刊。起先科恩純粹被視作一位贊助人,名字也只出現在版權頁上的顧問欄內,后來卻成了雜志唯一的編輯。這可是他的錢,而且他發現他很享受做編輯的權利。當維持這家雜志的開支變得過于龐大,他不得不放棄時,他還是頗有些惋惜的。
不過到了那個時候,他又有別的事情要操心了。他已經被一位想借那本雜志成名的女士給抓到了手心里。此人非常強勢,科恩根本就別想逃出她的手掌心。再說他還確定他愛她。等這位女士看明白了那本雜志成不了器了,她就有些厭棄科恩,于是決定在還有點東西可撈的時候趕快撈一把,所以她極力慫恿科恩到歐洲去,說是科恩可以在歐洲寫作。他們就這樣來到了歐洲——這里是那位女士就學的舊游之地,待了三年。這三年里,頭一年花在旅游上,后兩年在巴黎度過。羅伯特·科恩一共有兩個朋友:布拉多克斯和在下。布拉多克斯是他文人圈子里的朋友,我則跟他一起打網球。
把他捏在手心里的那位女士芳名弗朗西絲,在第二年年尾發現自己已經容顏不再,于是對羅伯特的態度也由過去漫不經心地占有他、盤剝他轉而斷然決定他應該娶她。在這時候,羅伯特的媽媽又給他安排了一筆津貼,每月三百美元。我相信在兩年半的時間里,羅伯特·科恩眼睛里根本就沒有過別的女人。他過得相當幸福,只不過跟住在歐洲的很多美國人一樣,他覺得還是住在美國好。他還發現自己能寫點東西,他寫了本小說,雖說相當差勁,也并沒有日后評論界批得那么糟。他讀了很多書,打打網球,還在當地的一個健身房打打拳。
我第一次注意到他那位女士待他的態度,是有天晚上我們三個一起用餐之后。我們先在大馬路飯店用過餐,然后去凡爾賽咖啡館喝咖啡。喝罷咖啡后又喝了幾杯fines[4] ,我就說我得走了。科恩剛剛說起我們兩個應該在周末的時候來次小旅行,他想出城去痛痛快快地來次遠足。我建議我們先飛到斯特拉斯堡[5] ,然后去爬圣奧迪爾山,或是阿爾薩斯地區[6] 別的什么鄉野地方。“我認識斯特拉斯堡的一位姑娘,她可以帶我們在城里好好轉轉。”我說。
桌子底下有人踢了我一腳。我以為是無意中碰到的,就繼續說下去:“她在那兒已經住了有兩年了,對那個城市可說是了如指掌,是個很棒的姑娘。”
我桌子底下又挨了一腳,仔細一看,發現羅伯特的那位女士弗朗西絲正繃著臉,下巴抬得老高呢。
“該死,”我說,“干嗎要去什么斯特拉斯堡?我們可以北上布魯日[7] ,要么去阿登高地[8] 也不賴嘛。”
科恩明顯松了一口氣,我也沒再挨踢。我道了聲晚安,就此告辭。科恩說他想買份報紙,可以陪我一起走到街道拐角。“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說,“老兄你干嗎要提斯特拉斯堡的那位姑娘?你沒見弗朗西絲是什
么臉色嗎?”
“沒有,我干嗎要看她的臉色?如果我認識一個住在斯特拉斯堡的美國姑娘,這干弗朗西絲什么鳥事?”
“沒任何區別。只要是姑娘都不成。我就不能去了,就這么回事。”
“別傻了。”
“你不了解弗朗西絲。只要出現什么姑娘就堅決不成。你沒見她剛才的臉色?”
“好吧,好吧,”我說,“那就去桑利[9] 得了。”
“別生氣哦。”
“我不生氣。桑利是個好地方,我們可以住在大雄鹿飯店,到森林里遠足,然后回家。”
“好,那挺好的。”
“好了,明天球場上見。”我說。
“晚安,杰克。”他說,回頭朝咖啡館走去。
“你忘了買份報紙了。”我提醒他。
“提醒得是。”他跟我一起走到拐角的報亭。“你沒生氣吧,杰克?”他拿著報紙轉身問我。
“我干嗎要生氣?”
“網球場上見。”他說。我看著他手拿報紙走回咖啡館。我挺喜歡他的,可她顯然讓他的日子很不好過。
第二節
那年冬天羅伯特·科恩帶著他的小說回了趟美國,小說被一家相當不錯的出版社接受了。我聽說出門前他們大吵了一架,我覺得弗朗西絲就是這么失去了他,因為紐約有好幾個女人都待他不錯,他回來以后也真是今非昔比了。他對美國更加熱衷,也不再那么單純那么友善了。有幾位出版商對他的小說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這也著實沖昏了他的頭腦。然后就有好幾個女人煞費苦心地討好他,這么一來他的見識可就大大改觀了。有四年的時間他的眼界就完全局限在他妻子身上。三年或者幾乎三年以來,他的眼里又只有弗朗西絲。我敢肯定,他這輩子都從來沒有戀愛過。
他在大學的那段日子實在糟心,心灰意懶之下逃到了婚姻里,而等他發現他并非第一任妻子眼中的一切時,弗朗西絲又趁虛而入,一把把他給抓在了手心里。他雖沒真正戀愛過,卻也認識到他對女人并非沒有吸引力,一個女人喜歡他并想跟他住在一起可不僅僅托賴神賜的奇跡。這使他的態度有所改變,變得不太那么容易相與了。而且,他在紐約的時候曾跟幾個親戚打過幾場很險的橋牌,下的賭注都超出了他的償付能力,好在他牌好,還贏了好幾百美元。這使得他對自己的橋牌技藝頗為自負起來,說過好幾回,一個人要是迫不得已,總歸還可以靠打橋牌為生。
還出了另外一件事。他一直都在讀W.H.赫德森[10] 。這聽起來像是一種無害的消遣,可是科恩把那本“紫色土地”一讀再讀。“紫色土地”如果讀得太晚就是本很危險的書了。它講述的是一位完美無缺的英國紳士在一片極富浪漫氣息的土地上經歷的一系列極具想象力的風流歷險,其中的風光描寫極為精彩。可是一個已經三十四歲的男人若是把它當作了人生指南可就很不安全了,這就好比一個同齡的男人抱著一整套比這個還實際些的阿爾杰[11] 的著作,從法國修道院直接奔赴華爾街一樣不靠譜。我相信,科恩把“紫色土地”里的每一字句都像是看R.G.鄧恩[12] 的報告一樣當了真。你懂我的意思,他當然也有所保留,不過這整本書在他看來是大有道理的。這本書正好成了促使他行動起來的觸發點。我起先沒意識到它對他竟有這么大的影響,直到有一天他跑到我辦公室來找我。
“嘿,羅伯特,”我說,“你來是讓我開開心的嘍?”
“你愿不愿意到南美去,杰克?”他問我。
“不愿意。”
“為什么不愿意去?”
“我不知道。我從沒想過去那兒。太貴了。反正你在巴黎也能看到你想看的所有南美人。”
“他們都不是真的南美人。”
“在我看來他們可都真得不能再真了。”
本周的通訊稿必須得趕這一班海陸聯運列車[13] 發出,可我才寫了有一半。
“聽到有什么丑聞沒有?”
“沒有。”
“你那幫尊貴的親戚里面有沒有鬧離婚的?”
“沒有。聽我說,杰克。要是我們倆的費用由我負擔,你愿意跟我一起去趟南美嗎?”
“干嗎一定要把我拉上?”
“你能講西班牙語。而且咱們倆一道也更好玩。”
“不行,”我說,“我喜歡巴黎,而且我一直是去西班牙消夏的。”
“我這一輩子就盼著能來這么一趟旅行。”科恩說。他坐了下來。“我怕還沒來得及動身就已經老朽了。”
“別傻了,”我說,“你愿意去哪兒就能去哪兒,你有的是錢。”
“我知道。可我總是下不了決心。”
“開心點,”我說,“哪個國家看起來還不都像是電影鏡頭嘛。”
我挺替他難過的。他感覺很糟糕。
“一想到我的人生在飛快地消逝,而我都還沒有真正生活過,我實在受不了。”
“除了斗牛士,沒有任何人的人生是一路高歌猛進的。”
“我對斗牛士可不感興趣。那種人生不正常。我想回到南美的鄉間去走走。我們的旅行肯定會很有意思。”
“有沒有想過到英屬東非[14] 去打獵?”
“沒有,我不喜歡這個。”
“我愿意跟你一起去。”
“不,我對這個不感興趣。”
“那是因為你從沒讀過這方面的書。去找本通篇都是描寫跟黑得發亮的美麗公主談情說愛的書看看就是了。”
“我想去趟南美。”
他真有猶太人那種典型的固執脾氣。
“咱們下樓去喝一杯吧。”
“你不是在工作嗎?”
“不干了。”我說。我們下樓來到底層的咖啡館。我早發現這是把朋友給打發掉的最好辦法。一杯酒下肚后,你只消說一句“唉,我還得回去發幾份電訊”就結了。干新聞這一行,極其緊要的一點就是應該顯得整天都沒事干,所以能找到類似得體的脫身之計是非常重要的。總之,我們一起下樓來到酒吧,喝了杯威士忌加蘇打。科恩望著墻邊堆的一箱箱酒。“這地方不錯。”他說。
“酒水真不少啊。”我同意道。
“聽我說,杰克。”他俯身在吧臺上,“你從沒覺得你的人生正在溜走,而你根本就沒享受過生活的樂趣嗎?你沒意識到你已經虛度了將近半輩子了嗎?”
“有啊,每隔一段時間都會這么想。”
“你知道再過個三十五年我們就該死了嗎?”
“扯這些有用嗎,羅伯特,”我說,“扯這些干嗎?”
“我是認真的。”
“我從來不為這種事瞎操心。”我說。
“你應該操操心。”
“我隨時隨地操心的事情已經夠多的了。我什么心都不想操。”
“我就是想去南美。”
“聽我說,羅伯特,跑到另一個國家去不會有任何區別。這一套我都試過了。你從一個地方跑到另一個地方,但你還是你。你沒辦法從自己身體里面逃離出去。”
“可你從來沒有去過南美啊。”
“南美你個頭!你要是就抱著現在的想法,就算去了,也還是一個熊樣。巴黎是個好地方。你為什么就不能在這里開始你的生活呢?”
“我煩透了巴黎,煩透了這個區[15] 。”
“那就離開這個區。自己四處溜達溜達,看能碰上什么新鮮事兒。”
“我什么事兒都碰不上。有天夜里我獨自走了一整夜,屁事都沒發生,只有一個騎自行車的警察攔住我要看我的證件。”
“巴黎的夜晚不是很美嗎?”
“我根本不在乎巴黎什么樣。”
問題就在這里。我為他感到難過,可是又根本幫不上忙,因為你一上來就會碰上他那雙重的固執:南美能救他的命,還有他不喜歡巴黎。第一重固執來自一本書,我猜第二重固執也來自一本書。
“好了,”我說,“我得到樓上去發幾份電訊了。”
“你一定得去嗎?”
“是呀,我得把那幾份電訊發出去。”
“要是我跟你一起上去,在你辦公室坐一會兒,不會妨礙你吧?”
“不會,上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