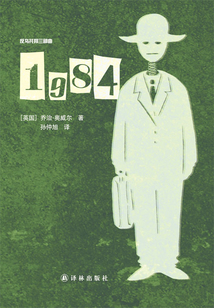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85評論第1章 代譯序(1)
喬治·奧威爾的《1984》是一種情緒的表達,同時也是一種預兆。他表達的是一種對于人類未來近乎絕望的情緒,同時也預兆,除非歷史的進程改變,否則全世界的人都會在不知不覺中失去大部分人類的特質,變成沒有靈魂的機器人。
這種對人類未來絕望的情緒與西方思想中最基本特征之一,即對人類進步以及人類創造正義與和平世界的能力懷有堅定的信念,形成鮮明的對比。這種信念來源于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思想,以及基督教《舊約全書》中提倡的救世主觀念。《舊約全書》中的歷史哲學觀念認為,人類會在歷史的長河中成長和發展,并最終會實現他們所有的潛能。它假設人類會充分發展理性與愛的能力,并因此理解這個世界,從而能和同伴以及自然共存,同時他們也能保留個性和完整性。普遍的和平和正義是人類的目標,先知們堅信錯誤和罪惡即使有得勢之時,“末日審判”([德國]埃里希·弗羅姆)最終還是會到來,救世主便是這種信念的象征。
先知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人類最終會找到一種完美的狀態。基督徒將這轉變成超越歷史的、純粹精神層面上的觀念,但并沒有放棄它與道德規范和政治之間的聯系。中世紀的基督教思想家強調,盡管“上帝之國”不可能在當世實現,但是社會秩序必須符合和實現基督教的精神原則。基督教派在宗教改革前后,用更加急躁、更加積極和更加革命的方式來強調這種觀念。隨著中世紀的結束,人類的感官和信念,已經不只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更加完美的社會,這種觀念開始以新的力量和新的形式出現。
其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從文藝復興開始發展的新型寫作方式,首次應用這種方式的是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字面意思是:烏有之鄉),這個名字后來適用于其他所有的同類作品。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對他自己所處的社會提出了最尖銳的批判,同時他也構建了另一個社會圖景,盡管它可能并不十分完美,這個設想解決了大部分他同時代人聽起來無法解決的人類問題。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和其他同類作品的特點是:他們不會去說籠統的理念,但是他們會給出一個符合人類最深層次的需求、帶有具體細節的社會愿景。與先知們的預言不同,這些最完美的社會形態并不是存在于“末日審判”,而是在當下就已經存在——盡管這有著地理上的距離,但并不是時間上的距離。
緊隨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之后,還有兩部同類作品,分別是修道士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德國人文主義者安德里亞的《基督城》。后者是三者之中最具現代性的作品。烏托邦三部曲之間有著不同的觀點和創意,但是與它們的共同點相比起來,這些差異就顯得十分渺小。此后幾百年,經常會有各種描寫烏托邦的作品問世,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近來最具影響力的烏托邦作品當數愛德華·貝拉米1888年出版的《回溯過去》。它與《湯姆叔叔的小屋》和《賓虛》一樣,成為世紀之交最受歡迎的書。它在美國出版了幾百萬冊,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貝拉米的烏托邦是惠特曼、梭羅和愛默生所描繪的偉大美國傳統的一部分,它是美國對當時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看法最強有力的表達。
18世紀的啟蒙運動哲學家和19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思想家,從哲學和人類學的角度出發,在他們的作品中清晰地表達了對人類個體與社會完整性的美好愿景。這種愿景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這場戰爭,盡管給人一種為和平和民主而戰的假象,但卻有數百萬人死在歐洲列強的疆域擴張野心之下。就在這么短的時間之內,兩千多年來西方社會充滿希望的傳統被摧毀,并開始轉化為一種絕望的情緒。一戰時在道德上的麻木不仁僅僅是個開端,其他同類性質的事情相繼發生:背叛了社會主義愿景的斯大林反動的國家資本主義;20世紀20年代末嚴峻的經濟危機;暴虐的勢力在最古老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德國取得了勝利;20世紀30年代瘋狂的蘇聯肅反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的參戰國家都喪失了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還存在的道德考量;由希特勒開始無限制地對無辜的民眾進行屠殺,后來更多的是直接完全摧毀諸如漢堡、德累斯頓、東京這樣的城市,最后對日本使用了原子彈。從此以后,人類面臨著更大的危險——整個人類文明甚至是所有人類都會被現有的而且比例還在不斷增多的熱核武器毀滅。
然而,大部分人不會自覺意識到這種威脅和自身絕望的境地。一些人堅信正因為現代戰爭具有如此大的毀滅性,所以戰爭不會發生;另外一些人宣稱即使有六七千萬人在核戰爭的頭兩天被殺,在克服起初的震驚之后,生活依舊會繼續。在這種彌漫在我們這個時代新的絕望情緒變得明顯和緊緊控制住人們的意識之前,奧威爾揭示了它,這恰恰是他作品的意義所在。
奧威爾并不是做這種嘗試的唯一一人。另外兩個作家,俄國的扎米亞京在他的書《我們》和阿道斯·赫胥黎在他的《美妙的新世界》中,都用跟奧威爾作品非常相似的方式表達了當時的這種情緒并對未來提出警示。這三部寫于20世紀中葉的作品被我們稱為“反烏托邦”三部曲,這是為了和上文提到的寫于16、17世紀的“烏托邦”進行對應[1]。就像早期烏托邦作品描述充滿自信的情緒和充滿希望的后中世紀的人一樣,反烏托邦描述的是一種無能為力的情緒和絕望的現代人。這種轉變是歷史上最大的悖論:在工業時代早期,實際上人們還沒有解決吃飯的問題,他們生活在一個為了經濟效益而實行奴隸制、發動戰爭和充滿剝削的世界里。人們只會將新的科學應用到技術和生產上——盡管如此,在現代化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們還是充滿著希望。四百年后,所有的這些愿望都可以實現;人類可以為每一個人生產足夠的物品;技術的進步可以帶給國家比征服領土更多的財富,戰爭變得不再需要;全世界正在變得像四百年前那樣統一。就在人們感受到所有的希望即將實現的這一刻,他們開始失去了它。這就是反烏托邦三部曲的核心,它們不僅僅描述了我們的未來走向,同時也解釋了歷史的悖論。
反烏托邦三部曲在細節和側重點上各不相同,相比于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扎米亞京寫于20世紀20年代的《我們》,與《1984》有更多的相似點。《我們》和《1984》都描述了社會的完全官僚化,人只是一個數字并且失去了所有的個性。這是由于無限的恐怖(在扎米亞京的書中,對于人腦的操縱最終發展到在身體上進行改造)聯合意識形態和心理操控引起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應用集體催眠暗示是將人變成自動機器的主要手段,這避免了恐怖行動。你可以說扎米亞京和奧威爾的作品與斯大林主義和納粹的獨裁統治類似,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展示的是發展中西方工業世界的圖景——假如它只是繼續跟隨目前的趨勢,而沒有在根本上做出改變。
盡管反烏托邦作品有如此多的不同,但是在一個基本問題上它們是一樣的,這是一個哲學的、人類學的、心理學的、可能也是宗教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人類是否可以這樣轉變,變得忘記自由的渴望、尊嚴、完整性、愛——也就是說,人類是否可以忘記他是一個人?或者人類本性是否有一種推動力,可以對違背這些人類基本需求的事做出反應,然后通過努力去將這個野蠻無人性的社會變成一個有人性的社會?我們必須注意到,反烏托邦的三個作者并沒有采取現在在很多社會科學家中普遍流行的心理相對主義這種簡單的觀點,他們并不認為:沒有所謂的人性;沒有一種對人類必不可少的品質;像許多社會學者寫到的人剛生下時什么也不是,就像一張白紙一樣。他們認為人有一種強烈的渴望去謀求愛、公平正義、真理、團結,在這方面他們與相對主義者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事實上,他們斷言,正是他們描述的這種通過一切手段去爭取的思想充滿了力量和強度,所以它們必須被摧毀。在扎米亞京的《我們》中,大腦控制與腦前葉切除手術類似,都是為了擺脫人對于人性本質的索取;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中,則利用了人工選擇物種和毒品;在奧威爾的《1984》中,他們更是無限制地使用酷刑和洗腦。三個作者中任何一個作者都不應因認為摧毀人性易如反掌而受到指責。他們三個都得出了同一個結論:通過現有的普通技術和手段,這完全可以實現。
盡管與扎米亞京的作品有很多相似點,奧威爾的《1984》對于“人類本性可以如何被改變”這個問題有著獨到的見解。下面我就談談一些更具體的“奧威爾式”的概念。
奧威爾最直接的貢獻是在《1984》中假設了1961年和隨后的五到十年之間的事情,并將獨裁社會和原子戰爭聯系了起來。在《1984》中,原子戰爭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出現;一場大規模的原子戰爭在大概十年之后爆發,數百顆炸彈被投到了歐陸俄羅斯、西歐和北美洲的工業中心。在這場戰爭之后,所有國家政府開始確信,如果繼續這樣的戰爭必定會使組織化的社會和他們的政權走向末日。出于這樣的理由,沒有更多的炸彈被引爆。而現存的三個大國集團“全都只是繼續制造原子彈并儲備起來,等待決定性機會的到來,他們都相信那一天遲早會來。”執政黨的目標仍然是找到“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于幾秒鐘內消滅上億人口”的辦法。奧威爾在寫《1984》的時候,熱核武器還沒有發明,而在20世紀50年代,所有我們剛剛提到過的目標都已經達到,這只能作為一個歷史的注腳去解釋了。相對于熱核武器可以在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徹底消滅一個國家的90 甚至100 的人口來說,丟在日本城市的原子彈似乎威力太小,還沒達到效果。
奧威爾關于戰爭的概念的重要性在于他一系列敏銳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