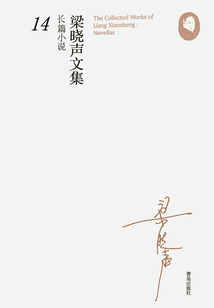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自序
屈指算來,我這一本書,業已出版整整二十個年頭了。
二十年來,它一直被讀者認為是我的代表作之一。
我自己亦愿這么承認。
一九八七年它初版時,曾引起方方面面的關注。也曾被方方面面調審過。在當年,它無疑是一本已經寫到了審查“邊緣”的書,因而也可以說是一本僥幸出版的書。
不久前,它已在臺灣出版,并有幸印上了臺灣最權威的出版業刊物《成品》之封面,而且是《成品》向臺灣讀者重點推薦的大陸文學作品,好評多多。這也令我欣慰。
按說,一部對“文革”進行尖銳批判的文學作品,若出版于“文革”期間,才更有它的價值和意義。
但,那又怎么可能?
如果在“文革”期間我就居然敢于白紙黑字寫下這一本書中的任何一章;如果還不幸被發現被揭發的話,那么今天我也就斷不能坐在家里為它的再版寫序了。
在“文革”期間,即使我不顧自己死活,為家人著想,也是沒有絲毫勇氣闖下那一種鐵定的殺頭之禍的。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自己重讀它,也還是會被書中所寫的林林總總的“文革”現象所震驚。盡管書是我寫的;那些現象是我親歷的;而且還算不上是“文革”中最為駭人聽聞的現象。
身為作家,我為我在三十七歲時寫出過這樣一部書尤其感到欣慰。
畢竟,作為“文革”的親歷者,我留下了我的一份文字見證。
我欣慰于我不僅僅是一個善于以“故事”娛樂大眾甚或取悅于大眾的作家;我畢竟還多少奉獻了我的一些思想。
我欣慰于我不僅批判了“文革”;我對自己的心理剖析、言行批判,也是同樣坦蕩和尖銳的。
我欣慰于我不僅剖析和批判了“文革”時期的自己,還以同樣的勇氣剖析和批判了“文革”中的所謂“革命群眾”的愚惡和邪狂……
但我還是要強調,我的這一部作品盡管具有“紀實”的色彩,但左不過就是在風格上呈現了那么一種色彩而已;歸根到底,它是小說,而非“紀實”。
比如書中的“班主任老師”,并非現實生活中的我的班主任老師。“她”實際上表現出的是眾多老師在“文革”中身不由己的行狀。
實際上我的班主任老師孫桂珍她對我是極其關愛的。當年她作我們班主任時,僅大我們六歲。在我下鄉前的許多個夜晚,特別是一九六八年冬季的許多個夜晚,我常到她的家里去,向她傾訴我內心的苦悶。那苦悶既是個人命運的,家愁的,也是關乎社會正義的,人道主義的,國家前途的……
有時我們師生二人竟至于長談至夜里十一點多。她的丈夫趙老師對我也很關愛,每次我離開時他們都把我送到樓外,送到馬路上,目送我走出很遠。
從老師家到我家,要走半個多小時。踏厚雪,頂寒風,一路走,一路思想……
如今回憶起來,覺得倒有了詩意似的。
想想吧——一名已畢業兩年,既不能升學也找不到工作的十八歲的中學男生,與他的二十四歲的女班主任老師,在非常年代交談非常話題,而且每至深夜,個中憂己憂國憂民的情愫,真是一言難盡!……
在當年,我的思想自然是反“文革”的;我的許多言論自然是極其“反動”的。倘我和我老師的交談被暗中錄了音,那么我肯定被打成小“反革命”無疑,我的老師也肯定將從學校里被“掃地出門”……
但我在當年實無勇氣發出公開的反對吶喊。父親遠在四川工作;哥哥患精神病;弟弟妹妹尚小;母親體弱多病……
少年的我便崇敬沙俄時期的“十二月黨人”,崇敬那些敢于指出“俄羅斯病了”因而被發配往西伯利亞的俄國知識分子……
然而在“文革”中,十八歲的我卻絕不敢便學我所崇敬的那些人……
是以苦悶更成苦悶。
我是當年的一個“憤青”,但與今天的“憤青”大有區別。今天的“憤青”們,也許還憤怒于別人怎么就成了名人;當年的我,卻是特別同情那些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的名人們的。哈爾濱市的他們中的某些人,在“文革”后期成了與我相差二三十歲年齡的忘年交……
在我的班主任老師家里,在我下鄉前幾天的一個夜晚,老師囑我下鄉以后,不要記日記;不要與人談“政治思想”;不要在各種會議場合主動地作率直的發言……
老師最后說:“你這個學生啊,看書太多了點兒。只看看也就罷了,還太愛想。我不擔憂你任何方面,只擔憂你犯政治錯誤……”
她的目光中既有愛護,也有理解……
同學們湊錢為我買了些生活用品,但是卻沒有也送我一支筆。
后來我知道,是老師不許……
此書初版面世后,老師也是看過的。因為我寫了自己真實的母校,卻寫的非是一位真實的班主任老師——想來,我的老師她一定因而頗受過無端猜疑……
然而我的班主任老師以及她的丈夫趙老師每次到北京來,照例擠出時間與我一晤。
他們從未對我說過一句責備的話。
但與我關系親密的幾名中學同學是責備過我的——“你這家伙,怎么能那么寫?”
是啊,怎么能那么寫?
當年輕薄,不知文字落在紙上,一旦印成為書,再改就難了……
索性保持原貌吧。
但這點是心有懺悔的,幸而老師依然關愛我這個學生,不忍言責。
補記以上,才像個學生的樣子。
至于“吳叔”,有老鄰居盧叔的某些性格影子。但也只不過就是影子,非現實生活中當年的盧叔本人。當年的盧叔對我及我全家也極友善,而且是全院最喜歡和我討論“天下興亡”的一個長輩。書中所寫的關于“吳叔”的那一種悲慘下場,是真實發生在哈爾濱市某工廠的事件。我將那事件嫁接在“吳叔”身上了……
大小二小是盧叔的兩個兒子。
二小已不幸身亡——干臨時工出鍋爐灰不慎從跳板上摔下,磕裂了頭顱。可憐我這一個鄰家的弟弟,死時才四十來歲,并且在財產方面一無所有,連穩定的住處也沒有……
我曾以《關于二小》一篇文章祭奠過他。
大小至今一逢難事,仍打電話或親自到北京來向我求助。
我是一名建筑工人的兒子。在當年,我的出身屬于“紅五類”。
當年我已頗善文字,倘有什么野心,靠一支筆,是很可以為自己向“革命”撈到些實際的人生好處的。
然而我沒有用筆那樣過。
故我對自己的當年比較滿意。有時,甚至比對現在的自己還滿意。
這我要感激書。感激文學。感激作家。在我所感激的作家中,雨果、司湯達、哈代、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是我最愛。
他們是我的人性的教誨者。
正是由于有幸接受了他們的早期教誨,我雖曾是紅衛兵,但從不曾兇惡過。
倘沒有他們那樣一些偉大的人性教誨者,當年的我也許會是另一個“張鐵生”。
這就是我何以會一談到文學,動輒十八、十九世紀西方文學的原因。
我是喝那種“奶”才成為作家的。
我對政治其實毫無興趣;我只不過被我所接觸的文學影響成了一個人道主義者而已。
我的文學理念,幾乎不曾從人道主義立場移動過。
這固然膚淺,卻也無害。
我只不過是一個膚淺又無害的作家而已。
我已沒了再深刻點兒的可能。
最后我要說,二十年間,此書每隔五六年必有幸再版一次。這對我是勉勵。
我非干部子弟,非名人之后,亦無書香血統。我是老百姓的一個兒子。呈現中國一個老百姓的兒子在“文革”時期的行為和心理的狀態,是我寫此書的初衷,也是它的一點點價值。
情懷漸覺成衰晚,鸞鏡朱顏暗驚換。
現在的我,看我當年寫的書,幾乎一向是既欣慰又沮喪的——因為,總不滿意……
梁曉聲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五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