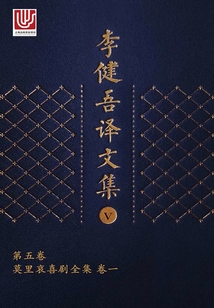
李健吾譯文集·第五卷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序[1]
莫里哀是法國現實主義喜劇的偉大創始人。他的喜劇向后人提供了當時的風俗人情,向同代人提出了各種嚴肅的社會問題。這里說“現實主義”,因為這最能說明他的戰斗精神。他又是法國唯物主義喜劇的第一人,他以滑稽突梯的形式揭露封建、宗教與一切虛假事物的反動面目。他不賣弄技巧,故作玄虛,而能使喜劇在逗笑中負起教育觀眾的任務。
莫里哀(Molière)是他參加劇團以后用的藝名。他的真名姓是約翰-巴狄斯特·波克蘭(Jean-Baptiste Poquelin)。他在家庭中是長子,1622年1月15日受洗禮,可能就是這一天生的。他的父親約翰·波克蘭是一個生意興隆的掛毯商。外祖父克勒塞(Cressé)也是掛毯商。兩家很可能有作坊。父親還是宮廷陳設商。這是一種小貴人身份,有機會接近國王。宮廷陳設商一共有八名,每兩名跟隨國王一季,國王去什么地方,他們就先行一步,布置他的行宮。父親對長子期望殷切,在莫里哀十五歲上,就給他取得了繼承權。據說1642年,莫里哀曾經為路易十三去過南方的納爾榜(Narbonne)布置行宮。
他十歲喪母,外祖父疼他,經常帶他去玩新橋。新橋類似舊北京的天橋。當時有一個人叫達巴欒(Tabarin),幫一個江湖郎中叫賣,說俏皮話,演小鬧劇,轟動巴黎,小市民很愛聽他逗哏。那時正式劇場只有一個布爾高涅(Bourgogne)府,平時演悲劇和悲喜劇,也演鬧劇。祖孫兩個也常到劇場看戲。臨到莫里哀上學前后,達巴欒和名丑先后死去,鬧劇也就只在外省還有。
1635年,他進貴族學校克萊孟(Clémont)的期間,法國文壇出了一件大事,在首相黎希留推動下,成立了法蘭西學院。院士逐漸增加到四十人,成為文化人最高的國家榮譽。文藝理論家布瓦洛(Boileau)當了院士,據說他私下里勸說莫里哀放棄演丑角這個行當,莫里哀謝絕了他的好意。后來莫里哀去世后,據說路易十四有一天曾問布瓦洛,誰給他統治期間帶來最大的文學光榮?布瓦洛回答:“陛下,是莫里哀。”不過莫里哀非學院的院士,后來學院在大廳為他立了一尊石像,下面寫著這樣自我調侃的話:
“他的光榮什么也不少,我們的光榮少了他。”
黎希留成立學院,是和他統一法蘭西的雄心分不開的。他希望用三一律來束縛戲劇家的頭腦。莫里哀后來寫喜劇雖然沒有受到什么妨礙,也不能說一點沒有受到影響。
學院成立的第二年,旅居國外的笛卡兒發表了他的《方法論》,推崇見識和理性,后來莫里哀寫戲,正面人物帶有類似的論點。理性主義是古典主義的基本原則。其實,莫里哀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他更接近反駁笛卡兒的唯心觀點的伽桑狄(Cassendi)。后者好幾年充當他的同學沙派耳(Chapelle)的家庭教師,據說,他一同聽過課。自由思想者沙派耳一直是莫里哀的朋友。莫里哀曾經翻譯過拉丁唯物主義詩人盧克萊修(Lucrèce)的《物性論》,其中關于愛情一段,他在《憤世嫉俗》(Le Misanthrope)中引用過,其余譯稿都散失了。莫里哀喜歡哲學,父親卻要他成為自己的接班人,還幫他從外地買了一張法學學士證書。
就在路易十四登基這一年,1643年(路易十四才五歲,由國母攝政),莫里哀卻和統治階級決裂了,同十幾個青年,特別是貝雅爾(Béjart)一家兄妹,簽訂合同,組織“盛名劇團”(IllustréThéatre)。1649年6月28日,在一位公證人的文件里,他第一次用莫里哀這個后來舉世聞名的名字簽字。他放棄宮廷陳設商的繼承權,把它讓給他的兄弟,自己去做一個被教會驅逐出教的“戲子”。但是他們的演出完全失敗了,劇團出面人是莫里哀,債主把他送進監牢,拘押了三五天,由父親作保,應許分期償還。劇團解散了,但他不回頭,和貝雅爾兄妹幾個人參加了另外一個劇團,離開巴黎,到西南一帶去流浪。一去就是十二年。這位學生出身的有產者,放棄產業,放棄榮譽,放棄現成的社會享受,到人民中間扎了根,擺脫書生氣,仗著他的人品與才具,鍛煉成為一位戲劇事業活動家,成為受團員愛戴的劇團領導。他學習人民喜愛的鬧劇,學習靠演技取勝的意大利職業喜劇。西南各省原歸孔提(Conti)親王統治,1653年從巴黎監獄出來,跟黎希留首相的后繼人馬薩林的侄女結了婚,成為劇團的保護人。
劇團的根據地是里昂。1655年,莫里哀在這里上演他的詩體喜劇《冒失鬼》(L'Etourdi),劇情輕快,風格清新,喜劇正式產生了。1656年,他在貝濟埃(Béziers)上演他的詩體喜劇《愛情的怨氣》(Dépit Amoureux),同樣得到好評。可是劇團的保護人變成一位“虔誠的”信士,1657年5月,正式禁止劇團使用他的名義。他后來還以信士的名義攻擊莫里哀的喜劇。他可能是莫里哀接觸的最早的一位偽君子。但是劇團的名譽蒸蒸日上,國王的兄弟出面支持劇團,1658年10月24日,劇團在巴黎宮廷演出,他和路易十四見面,國王把盧佛宮劇場撥給莫里哀劇團。
但是道路并不平坦。1659年11月18日,他上演他的《可笑的女才子》(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演了一場,受到阻撓,便停演了。這時國王不在巴黎,很可能貴族中有人搗亂,經過疏通,終于在12月2日繼續演出,票價提高了一倍,觀眾如舊。據說有一位老軍人在池座大叫:“勇敢,勇敢,莫里哀,這出喜劇真棒!”1660年,國王已經看過兩次,第三次又扶著他的首相馬薩林的座椅看了一遍,還賞了劇團三千法郎。輿論改口了。莫里哀在巴黎站住了腳。
1661年,馬薩林去世,國母不再攝政,路易十四把政權集中在他一人手中。就在英國資產階級鬧革命的年月,法國出現典型的君主專制。政府靠賣官鬻爵來增加收入,官吏有繼承權與轉賣權,成為長袍貴族。路易十四自比太陽,生活豪華,窮兵黷武,唯我獨尊。莫里哀趕上他有所作為的早年時期,為了爭取他的保護,不得不博取他的歡心。1660年,莫里哀的兄弟一去世,莫里哀就收回宮廷陳設商的職位。
這時盧佛宮改建門廊,劇團沒有了劇場。幸而有國王兄弟從中幫忙,要求把黎希留用過的王宮劇場賞給劇團使用,路易十四同意了。從1661年6月24日,莫里哀上演他的《丈夫學堂》(L'Ecole des Maris)起,直到最后的《沒病找病》(Le Malade Imaginaire)止,他的喜劇都是在這里演出的。他在《丈夫學堂》里提出女子教育問題。劇中描繪弟兄兩個分擔教養兩個孤女的義務,嚴加管教的失敗了。當年8月17日,劇團參加財政總監福該(Fouquet)舉行的盛大游園會,他寫出了《討厭鬼》(Les Facheux),寫一個人要赴愛人的約會,不斷受到各種相識者的打攪。戲自然而有趣。可是,福該的財富引起路易十四的妒忌,一個月以后,福該被送進了監獄。
莫里哀沒有受到福該的影響。他寫出了五幕詩體喜劇《太太學堂》(L'Ecole des Femmes)。這是性格喜劇,也是社會問題喜劇。他把婦女教育和修道院掛上了鉤。女孩子在修道院待了十三年,十七歲出來,成了一個什么也不懂的“白癡”。路易十四從此把莫里哀看成喜劇作家,每年津貼他一千法郎。
妒忌的人們不放過莫里哀,用種種流言蜚語來中傷他。他寫了《太太學堂的批評》(La Critique de l'Ecole des Femmes)來回答。他在這個戲里談到他的喜劇理論,他揶揄無理取鬧的“侯爵”與裝模作樣的“學究”。敵對劇團接著上演攻擊莫里哀的戲。他當即用《凡爾賽宮即興》(L'Impromtu de Versailles)一戲來取笑對方的戲。他在這里要求演員要把戲演得自然。他正式宣告,“侯爵”是當代的丑角。他在《達爾杜弗》的序中說:“人容易受得住打擊,但受不了揶揄,人寧可做壞人,也不肯做滑稽人。”莫里哀攻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特別是經院哲學和經院醫學;他攻擊官方一再禁止而無法禁止的高利貸;他攻擊富商不擇手段的上升欲望;他特別攻擊天主教的危害多端的良心導師。
他居然敢在天主教的國家攻擊天主教,天主教把他當做“魔鬼”看待。事情發生在1664年5月12日,宗教界激烈攻擊的《達爾杜弗》前三幕演給路易十四看。這驚動了國母,激怒了路易十四的師傅和巴黎大主教佩里費克斯(Péréfixe)。在天主教的壓力下,路易十四傳詔給莫里哀,《達爾杜弗》停止公演,等全劇寫完了再作決定。當年11月,莫里哀第一次在路易十四的弟媳的別墅演出了全戲五幕。直到1666年,國母去世,頑固派失去靠山,形勢才逐漸好轉。第二年,路易十四口頭上應允解禁,但他隨即率領大軍北征,這事又擱了下來。莫里哀把戲的題目改成《騙子》,把人物的服裝也改了,在八月上演,但是第二天,代理國政的巴黎最高法院院長又禁止繼續公演。隨后,巴黎大主教張貼告示,禁止教民閱讀或者聽別人朗誦這出喜劇,并以取消教籍相威脅。直到1669年2月5日,教皇頒發“教會和平”詔令,各種教派停止活動之后,莫里哀才得到這出戲解禁的正式通知。他恢復《達爾杜弗》的面貌,正式和市民繼續見面。從法蘭西喜劇院成立(1680年)起,到1960年止,這出喜劇演出2654場,還不算其他劇團的演出和外國的演出。在法國著作中,它的演出占第一位。
這個喜劇表現一個近代上層資產階級家庭,家庭的室內生活密切配合。但是把戲搬到街頭,偽教士不敢再調戲人,少婦不再賣色相,兒子不再偷聽……,一切都變了另一種樣子。家長由于迷信他的良心導師,如果路易十四不出面干預的話,就必定陷于家敗人亡。因為法律是站在惡人方面的。宗教界之所以全力反對《達爾杜弗》,因為偽教士和真教士是很難區別開的。
莫里哀在《達爾杜弗》禁演期間,還寫出了許多其他喜劇杰作。
為了表示反抗,他上演他的《石宴》或者《堂·璜》(Dom Juan)。“窮人”一場戲,人們一看就明白是諷刺篤信之士的。既然篤信,還怎么會淪為乞丐呢?他在外省還充分領會了孔提親王的假冒為善的浮浪生活,他在宮廷也見慣了那些目中無人、自以為是的權貴人物。他把西班牙傳說中的人物寫成法蘭西貴族。戲里的父親申斥兒子,說:“沒有人品,門第不值一文。”他還讓堂·璜在父親面前撒謊,又對聽差說:“撒謊已經變成時髦風尚了。”演出的第二天,莫里哀取消了“窮人”這場戲,壓低了全戲的調子。連續十五場,場場客滿。路易十四不希望莫里哀加深宗教界對他的仇恨,暗示他把戲停演了。
為了表示寵信莫里哀起見,國王向他兄弟把劇團要過去,改成“國王劇團”,每年津貼六千法郎。
1666年6月4日,他上演他的喜劇杰作《憤世嫉俗》。這是一出精致的貴族世態喜劇。詩體、五幕,受到布瓦洛在《詩的藝術》中的特別稱贊,被看做莫里哀的最高成就。就語言藝術來說,他把宮廷社會的虛偽和妒忌寫到淋漓盡致的地步,但情節單薄,沒有力量吸引一般觀眾。他在這里創造了兩個人物:一個是男的,叫阿耳塞斯特(Alceste);另一個女的,是寡婦賽莉麥娜(Célimène),愛在背后評頭品足,說朋友的壞話。他恨這個社會,要她拋棄這種虛妄生活,而女方卻割舍不下她所誹謗的社會。他們分了手。阿耳塞斯特是喜劇人物,又是悲劇人物,后人為之一直爭論不休。
這出戲的票房價值并不高。莫里哀馬上換了一出性質不同的鬧劇,背景放在農村,主人公是一個樵夫,吃盡當光,成天打老婆。老婆生了氣,把他說成是名醫,于是就被無知的鄉紳請去給他忽然變成啞巴的女兒看病。他成全了啞女的愛情。這是莫里哀有名的《屈打成醫》(Le Médecin malgré lui),它上演的記錄僅次于《達爾杜弗》。
他在1668年寫了題材不同的三出喜劇:《昂分垂永》(Amphitryon),《喬治·當丹》(George Dandin),《吝嗇鬼》(L'Avare)。《昂分垂永》明寫天帝裘彼特,實際影射路易十四。天帝變化成昂分垂永模樣,和后者的愛妻過了一夜。膽小的聽差最后以幽默口吻道破:“關于這類事,頂好還是永遠什么也不說為是。”《喬治·當丹》是慶祝路易十四凱旋的,在凡爾賽宮演出。一個外省富商,娶了一位貴族小姐,發現她接受一位宮廷貴人的調戲,他每次稟告岳父母,都遭到女方愚弄和岳父母的欺凌。他最后說:娶了這么一個女人,不如投河死掉。
《吝嗇鬼》和《昂分垂永》一樣,題材是舊有的,他加入新矛盾,讓矛盾激化了。盧梭認為這是敗壞人倫的壞戲。歌德在《談話錄》(1825年5月12日)中說,德國人演這出戲時,把父子之間的沖突改成親戚之間的沖突。這出戲證明金錢被神化后所起的巨大破壞作用,即使是溫情脈脈的家庭關系。吝嗇在這里變成一種絕對欲望。
懷著一種喜悅心情,莫里哀接著寫了兩出獨具一格的喜劇——舞劇,兩劇都由路易十四寵愛的意大利人呂里(Lulli)譜曲:《德·浦爾叟雅克先生》(Monsieur de Pourceaugnac)和《貴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前者寫一個外省的土財主到巴黎同一位小姐結婚,小姐早已有了情人,一群男女流氓起來反對他的奢望。土財主把禍害他的人當作救命的大恩人,膽戰心驚,落荒而逃,還依依難舍地和他告別。《貴人迷》寫巴黎一位大富商,由于富有而一心妄想當貴人,他被人耍弄,出盡洋相,還自以為樂,當不成本國貴人,他就做土耳其的假貴人。
1671年,他寫了一出鬧劇《司卡班的詭計》(Les Fourberies de Scapin)。背景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司卡班原來是意大利職業喜劇的一個定型人物,膽子小,惹了事就溜之大吉。莫里哀完全改變他的性格:他愛打抱不平,為此常服勞役,他把性命置之度外,而且睚眥必報,老爺說他壞話,他把老爺裝在大口袋里臭打一頓。他不再是小丑了。“下等人”在莫里哀的筆下有了奇異的光彩。
1672年,他完成了喜劇《女學者》(Les Femmes Savantes)。現在看來,這出喜劇的主題有局限性,他諷刺婦女在科學上不能取得成就。他在這里寫了兩個滑稽詩人,還有一個不慌不忙的幽默的丈夫,令人很感興趣。他的目的是不要人做那些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的事。
這期間,野心勃勃的音樂家呂里如愿以償,當上了王家音樂學院院長,對一般的商業演出在樂器上有所限制,莫里哀不能和他合作了。他覺得路易十四不肯支持他了,他寫的《沒病找病》,本來預備進宮廷獻演,也打消了這個念頭。他在公演三場之后,感覺異常疲憊,他對他的夫人和一位青年(由他培養后來成為大演員的巴隆Baron)講:“我這一輩子,只要苦、樂都有份,我就認為幸福了,不過今天,我感到異常痛苦。”他們勸他身體好了再主演,他反問道:“你們要我怎么辦?這兒有五十位工作者,單靠每天收入過活,我不演的話,他們該怎么辦?”他不顧肺炎,堅持繼續主演。他勉強把戲演完,夜里十點鐘回到家里,咳破血管,不到半小時或三刻鐘,就與世長辭了。這一天是1673年2月17日。
他的去世震動巴黎。天主教不給他行終敷禮,也不給他墳地。莫里哀夫人只得向國王請求。路易十四認為巴黎大主教有些過分,可能引起人民公憤。最后,大主教勉強批準了出殯,限制在天黑以后,把他埋葬在一個小孩子的墓地。據說,后來再找莫里哀的墳頭就找不到了,因為早已讓教會挖掉,把骸骨不知拋到什么地方去了。
歌德在他的《談話錄》里說:“莫里哀如此偉大,每次讀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驚奇。他是一個獨來獨往的人,他的喜劇接近悲劇,戲寫得那樣聰明,沒有人有膽量想模仿他。”(艾克爾曼(Eckermann)的《談話錄》,1825年5月12日)。歌德講他自己“從青年時期就讀、就愛莫里哀,我一生向他學習了許多東西。我每年一定要讀他幾出戲,好叫自己保持一種經常和美好事物的接觸。我不僅喜歡他的完整的藝術手法,還喜歡詩人那種可愛的自然、高尚的心靈。”(1827年7月28日)。
歌德的談話對了解莫里哀有很大幫助。歐洲整個十八世紀的喜劇都是從他這里派生出來的。丹麥的霍爾貝格(Holberg),英國的謝里登(Sheridan),意大利的哥爾多尼(Goldoni)……都因師法莫里哀而見稱于世,但是形象總不及他那樣高大。
首先,他敢于把生活寫透。第二,他敢于把矛盾寫透。第三,自然而然,是他敢于把性格寫透。第四,他善于把戲寫透,這和他敢于把矛盾寫透是分不開的。他的喜劇使人有悲劇之感,未嘗不是這個緣故。第五,他特別重視自然面貌,許多不合理的情節,他能讓它自自然然地出現在觀眾面前,像《昂分垂永》那樣的神仙戲,膽小的聽差在口語上處處給人一種平易之感。他總是水到渠成,順水推舟,不給人以勉強之感。第六,他親近他的觀眾,他所嘲笑的行為、人物,都扎進觀眾的心里,和他有同感。據說,浦爾雅克裝成女人,逃出巴黎,在觀眾席上出現,向流氓招手感謝,也說明這個道理。最后,他之所以能把性格寫透,他在創造人物上能使觀眾滿意的,是戲里每一個人物,無論資產者、貴人、農民、少爺、小姐、用人、流氓,無論什么樣的人,都說合乎各自地位的話。他的主要人物都有階級性格做底子。這最后一點也可以說是補充第三點的。據說,布瓦洛給他起了一個“靜觀人”的外號,他確實不辜負這個外號,他的敵人也說他:“我先見他靠著柜臺,姿勢像一個人在做夢。他眼睛盯住三四位買花邊的貴人,表示用心聽他們說話;看他的眼睛移動,他似乎一直要看透他們靈魂的深處,聽出他們心里的話來。我簡直相信他有一個記事本,藏在大衣里面,不讓人看見,在記他們說的最入耳的話。……這是一個危險人物。”這是布爾高涅府劇場上演一出糟蹋他的戲里的話。但是,在刻劃“靜觀人”這一點上,卻幫助人們說明了他愛觀察的習慣。一般人認為他遠在資產階級革命一百多年以前,就點起了資產階級革命之火。總之,像他那樣勇敢的喜劇作家,后來的喜劇作家和他一比,資產階級的烙印反而深了,也膽怯多了。所以法國人說起他來,總愛用“無法模仿的莫里哀”(inimitable Molièrè)來評價他。
莫里哀不僅是一位杰出的劇作家,一位出眾的導演,還是一位成就極高的優秀演員,他還培養了一代群星燦爛的表演藝術家。他是法國戲劇歷史上貢獻卓越的戲劇家,也是整個歐洲戲劇事業發展的推動者。
莫里哀總共寫了三十三出戲,其中有最早兩出小鬧劇,不具名姓,和他后來的戲都有類似處,估計是他早年流浪江湖時寫的。一般人歸在他的名下,我也如法炮制。此外,他約年老的高乃依(Corneille)合寫的神話劇Psyché,我不譯了。另外五出,全是宮廷的喜劇或舞劇,不為一般人所重視,我也不譯了。我一共譯了二十七出,都是他現實主義的輝煌收獲。我勉強譯出,錯誤在所難免,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又,在付印此書時,我有幸讀到1963年《莫里哀百年研究成果》一書,作者是法國國家文獻局局長瑪德蘭·玉爾讓(Madeleine Jurgens)與美國哈佛大學博士伊麗莎白·馬克思費爾德·米勒(Elizabeth Maxfield Miler)兩位女士。后來又有幸讀到喬治·蒙格賴狄焉(Georges Mongrédien)的詳盡的年表,書名是《莫里哀》,這是他把十七世紀的有關莫里哀的材料和原文全部搜集在一起,多年精心之作的兩卷大書,由“科學研究國家中心”印出。仗著這本書,我又補進了一些十七世紀著名作家對莫里哀的看法的材料。最后,我更有幸讀到法蘭西學院院士彼耶·嘎克掃特(Pierre Gaxote)的《莫里哀》大作,里頭提出了許多新的看法。書是1977年出的,彩印者是夫拉馬瑞央(Flammarion)書店。我借用了他幾幅插圖。此外各劇的插圖是1682年全集本彼耶·布立薩爾(Piere Brissurt)的最早影印的版畫。全集本共分四冊,由杜爾(Touchard)先生編輯,于1958年成書。這里也選用了一些有關的插圖。謹在此對他們各自的重大成果表示感謝。
李健吾
1981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