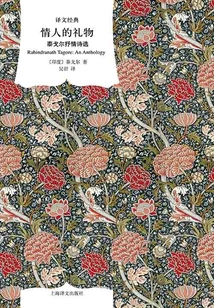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本序
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1861—1941)是印度著名的詩人、小說家、藝術家、社會活動家。于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生在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市,那是當時英印帝國政治和經濟的中心。他的祖父德瓦爾格納特,以生活豪華而又樂善好施聞名,成了商業時代的“王子”;他的父親戴溫德拉納特對吠陀和奧義書很有研究,生活簡樸純潔,在社會上被稱為“大仙”。
“大仙”生了十四個子女,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是他最小的兒子。這小兒子八歲時寫了他的第一首詩,以后經常在一個筆記本上寫些詩句,總要朗誦給長輩們聽,“像長出新角的牝鹿,到處用頭去碰撞一樣。”“大仙”喜歡在喜馬拉雅山區旅行。羅賓十一歲時,“大仙”把孩子也帶出去走了一趟:白天,高山叢林目不暇給,孩子“總擔心,別把那兒的美景遺漏了”,晚上,兒子給父親唱他所喜歡的頌神曲,父親給兒子講天文學。羅賓十四歲時,在大學雜志《知識幼苗》上發表了第一部敘事詩《野花》,長達一千六百行,便是以喜馬拉雅山為背景的。
一八七八年,羅賓赴英國學法律,興致索然,改入倫敦大學學英國文學,并研究西方音樂。一八八〇年,奉父命中途輟學回家。他對國內外的學校教育都不怎么喜歡,覺得收獲不大。他的家庭植根于印度哲學思潮,浸潤于印度文學、藝術的傳統,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羅賓主要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的熏陶下自學成才的。一八九一年,奉父命下鄉管理祖傳田產,常泛舟漫游,同佃戶有些接觸,因而觸發了改造農村、“更合理地分配財富”的幻想。為此,一九〇一年在圣諦尼克坦創辦了一所學校(一九二一年發展成為“國際大學”)。二十世紀初,參加反英的人民運動,以詩歌抨擊殖民主義者。他反對暴力,也反對妥協;逐漸與群眾運動格格不入時,便退隱了。一九一三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一五年結識甘地。一九一九年發生阿姆利則慘案,泰戈爾憤而放棄英國政府封他的“爵士”稱號,從此重新面對現實,關心印度的命運和世界大事。他幾次出國,訪問過中國、日本、英國、美國、拉美、西歐和蘇聯,他贊美社會主義的蘇聯,譴責法西斯主義的猖獗。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寫下《文明的危機》,控訴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深信祖國必將獲得民族獨立。同年八月七日,泰戈爾在加爾各答去世。
泰戈爾多才多藝,一生創作了五十多部詩集,十二部中、長篇小說,一百多篇短篇小說,二十多個劇本,一千五百多幅畫,以及大量的歌曲和文學、哲學、政治方面的論著。從總體看來,他首先是個詩人;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主要是由于他的詩歌創作,特別是《吉檀迦利》。
泰戈爾自己曾經說過:“我覺得我不能說我自己是一個純粹的詩人,這是顯然的。詩人在我的中間已變換了式樣,同時取得了傳道者的性格。我創立了一種人生哲學,而在哲學中間,又是含有強烈的情緒質素,所以我的哲學能歌詠,也能說教。我的哲學像天際的云,能化成一陣時雨,同時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裝點天上的筵宴。”[1]這段夫子自道給了我們一把鑰匙:要懂得泰戈爾的詩,詩中的哲理,多多少少得知道一點兒泰戈爾的哲學思想和宇宙觀。
季羨林先生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盡管泰戈爾也受到西方哲學思潮的影響,但他的思想的基調,還是印度古代從《梨俱吠陀》一直到奧義書和吠檀多的類似泛神論的思想。這種思想主張宇宙萬有,同源一體,這個一體就叫做“梵”。“梵”是宇宙萬有的統一體,世界的本質。人與“梵”也是統一體。“‘我’是‘梵’的異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實質同自然實質沒有差別,兩者都是世界本質‘梵’的一個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關聯。”泰戈爾以神或“梵”為一方,稱之為“無限”,以自然或現象世界以及個人的靈魂為一方,稱之為“有限”,無限和有限之間的關系,是他哲學探索的中心問題,也是他詩歌中經常觸及的問題。泰戈爾跟印度傳統哲學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點放在“人”上面,主張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認為只有在人中才能見到神。
季羨林先生還指出:“既然梵我合一,我與非我合一,人與自然合一,其間的關系,也就是宇宙萬有的關系,就只能是和諧與協調。和諧與協調可以說是泰戈爾思想的核心。”泰戈爾認為“完全的自由在于關系之完全的和諧”。泰戈爾從這種哲學觀點出發,宣傳愛的福音,認為“真正增強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進步的是協作和愛,是互信和互助”。不過,泰戈爾也并不否認矛盾的存在,他的思想里多少有些辯證法的因素,他承認自然、社會、人的思想都是在流轉變化的。“又要和諧,又要流轉不息,又要有一些矛盾(泰戈爾所了解的矛盾),那么結果只能產生一種情況,用泰戈爾的術語來說,就是‘韻律’,有時候他也把‘比例均衡’同韻律并列。只空洞地談和諧,沒有流轉,沒有高低之別、長短之別,也就無所謂‘韻律’。只有流轉,沒有和諧,也無所謂韻律。只有這些條件具備,才產生‘韻律’。在泰戈爾的思想中,‘韻律’占極高的地位,這是他的最高理想,最根本的原理,是打開宇宙奧秘的金鑰匙。”[2]
我國學者大多認為大詩人泰戈爾的思想發展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至二十世紀初印度反英運動止,是泰戈爾思想發展的前期。那時泰戈爾是個深情的愛國者,思想明朗,情緒飽滿,以詩歌、小說鼓舞人民爭取民族的獨立,反對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宗教偏見、封建禮教以及其他愚昧落后的現象。后來,因意見分歧而退出群眾斗爭,轉向自我思想的清理和凈化,這就是泰戈爾思想發展的中期。那時泰戈爾陷入孤獨、痛苦、憂愁、矛盾之中,思想是復雜的,愛國主義、宗教觀念、人道主義是詩人思想上的三根弦,三弦譜成了中期的樂章。從一九一九年起至一九四一年詩人逝世,是泰戈爾思想發展的后期,重新面向世界和斗爭。那時,他走訪世界各國,熱情支持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的解放斗爭,反帝、反殖的情緒更加明朗、強烈,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從俄國的革命中看到了人類的希望……
一般都認為泰戈爾的詩歌創作是和他的思想發展同步的,因此相應地把他的詩歌創作也分成前期、中期和后期。大多數研究者認為:前期是泰戈爾一生詩歌創作最豐富的時期,那時他風華正茂,思想敏捷活躍,感覺豐富多彩,寫下了不少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都很高的、耐讀的詩篇。后期,泰戈爾在思想上更上一層樓,作品的戰斗性更強了,因而博得了不少稱贊。中期的詩歌比較復雜,有的也比較費解,因此評論家們往往見仁見智,有的甚至頗有微辭。我是贊同周爾琨先生的觀點的:“作為現實主義者,泰戈爾總結人生的經驗,清理思想,準備繼續戰斗;作為‘愛’的宗教崇奉者,他愛人,愛神,追求‘梵’‘我’合一。在他表面平靜的思想的海洋里,潛伏著通向現實生活的、壓抑不住的激流。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思想滲透在他的泛神論的宗教中,成為他中期思想的中心支柱。這也就構成了他后期思想飛躍的基礎。”[3]正如轉變過程中的泰戈爾思想及其發展需要分析研究,相應地對這個時期的詩歌創作也不宜簡單化,同樣需要仔細研究和品味。
泰戈爾從英國讀書回來寫了不少抒情詩,一八八二年集為《暮歌》出版,這部詩集展示了詩人的才華和獨創性,但有點兒“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晨歌》(1883年)的情調迥異,表現了青春活力和歡快心情。《畫與歌》(1884年)開始從個人情感的天地里解脫出來,色彩斑斕。詩人自己也承認,早期的詩篇“夢幻多于現實”。《剛與柔》(1886年)的題材多樣化了,標志著詩人開始面向人生、面向現實生活,他已經走完了他的詩歌創作的序幕階段。
《思緒集》(1890年)是泰戈爾第一部成熟的詩集。內容大致可分五類:愛情詩,自然風景詩,社會題材的詩歌,宗教和神秘主義的詩歌,借自然現象、歷史故事或神話傳說闡明哲理的詩歌。這五類也是泰戈爾后來詩歌創作的主要內容,只不過不同時期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尤其重要的是:這部詩集表現了質的飛躍,表明泰戈爾的詩歌創作已經形成了它自己的獨特的藝術風格。思想的廣度、優美的抒情和魅力,使最嚴厲的批評家折服,也認為“這是他成熟的鮮明標志”。泰戈爾的民主主義思想和人道主義思想,就是在九十年代鄉村生活的過程中形成的,反映在詩歌創作上,連年都有碩果豐收,計有:《金舟集》(1894年)、《繽紛集》(1895年)、《收獲集》(1896年)、《碎玉集》(1899年)、《夢幻集》(1899年)、《剎那集》(1900年)、《故事詩集》(1900年)。從《思緒集》起的這八個詩集中,除《碎玉集》為格言詩、《故事詩集》為敘事詩外,其余六部都是優美的抒情詩。正如別林斯基所說的,青春是“抒情詩的最好時期”,那時泰戈爾風華正茂,他繼承了印度古典文學和中世紀孟加拉民間詩人抒情歌曲的優秀傳統,推陳出新,寫出了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個人特色的抒情詩篇,往往譬喻新穎,意境深遠,魅力奇幻,耐人尋味。據說泰戈爾前期的詩歌大多節奏鮮明,音韻和諧,格律嚴謹,可惜我不懂得孟加拉文,難以從英譯本去品味原作的格律美和音樂美。感謝詩人在《吉檀迦利》的英譯本問世后,又回過頭去陸續把他前期的詩歌譯成英文,一一編集出版,如《園丁集》、《新月集》、《采果集》、《飛鳥集》、《游思集》等。劉建先生在他的論文《泰戈爾前期詩歌創作淺論》中指出:“這些英文詩集與孟加拉文原作的關系,可以《園丁集》為例。《園丁集》中大部分詩歌譯自《剎那集》、《夢幻集》、《金舟集》、《繽紛集》等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孟加拉文詩集。《飛鳥集》除了有些是詩人一九一六年訪日時的即興英文詩作外,相當一部分選譯自《碎玉集》。《游思集》的情況也差不多。”[4]據此,這部《泰戈爾抒情詩選》所收前期詩歌,多從上述各英譯本選譯,以《園丁集》的人生和愛情的抒情詩為重點,兼顧《飛鳥集》這樣的哲理小詩,并有意識地從《采果集》中選譯了一些故事詩,也就是敘事詩,借一斑以窺泰戈爾前期詩歌的全貌。
《吉檀迦利》是泰戈爾中期詩歌創作的代表性作品。克里希娜·克里巴拉尼在她寫的《泰戈爾傳》里說:“以樂觀開朗的王子身份開始自己生活的羅賓德拉納特,在本世紀頭十年里忍受了內外的種種痛苦和折磨,離別和侮辱,斗爭和打擊。這一切最后都融合和純化在那些抒情詩歌里,這些詩歌于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從他壓抑和完美的心靈中噴瀉出來,一九一〇年收在題為《吉檀迦利》的詩集中出版了。他后來從這一百五十七首詩中選擇了五十一首放進英譯本《吉檀迦利》,從此揚名四海。”[5]這個譯本是泰戈爾親自一首又一首地譯成英文的,他自己說:“從前,某種情感的和風喚起了心中的歡愉情趣;如今,不知為什么又通過其他語言的媒介,焦急不安地體驗著它。”[6]可見泰戈爾的翻譯是一種再體驗和再創作。有的學者認為英譯本有時有所濃縮或刪節,弄得支離破碎、失掉了孟加拉文原著的美;這種評論多少有點兒道理,可是失之過分。詩人畢竟最了解自己的詩歌,他自己的譯文但求傳神,他重新體驗、創造了那份思想感情,并不刻板地嚴守形式的移植。卻說詩人自己翻譯的《吉檀迦利》,經過羅森斯坦,送到了葉芝手里。葉芝一讀這部詩稿就著迷了。他說:“這些抒情詩……以其思想展示了一個我生平夢想已久的世界。一個高度文化的藝術作品,然而又顯得極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燈心草一般。”葉芝對譯稿作了極個別的文字潤飾。一九一二年十月倫敦印度學會初版《吉檀迦利》時,葉芝還特地給詩集寫了“序”,[7]盡管初版只印了750冊。大詩人E·龐德曾在七月間參加葉芝家里詩人和作家們的一次聚會,聽葉芝朗誦泰戈爾的抒情詩,發現葉芝“為一位偉大的詩人,‘一個比我們中間任何一個都要偉大的詩人’的出現而感到激動不已”。龐德事后評述道,“這種深邃的寧靜的精神壓倒了一切。我們突然發現了自己的新希臘。像是平穩感回到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一樣,它使我感到,一個寂靜的感覺來到我們機械的轟鳴聲中。”“我在這些詩中發現了一種極其普通的情感,使人想起在我們西方生活的煩惱之中、在城市的喧囂之中、在粗制濫造的文藝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廣告的旋渦之中常常被忽視的許許多多東西……”“如果這些詩有什么瑕疵——我不認為它們有瑕疵——即有脫離普通讀者的傾向,它們確實太神化了。”[8]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泰戈爾因《吉檀迦利》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泰戈爾得獎之前,瑞典科學院是經過一番爭論的。當時瑞典詩人瓦爾納·馮·海登斯塔姆大力推薦:“我讀了這些詩歌,深受感動。我不記得過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讀過如此優美的抒情詩歌,我從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遠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飲著一股清涼而新鮮的泉水。在它們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顯示的熾熱和愛的純潔性中,心靈的清澈,風格的優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種完整的、深刻的、罕見的精神美。他的作品沒有爭執、尖銳的東西,沒有偽善、高傲或低卑。如果任何時候詩人能夠擁有這些品質,那么他就有權得到諾貝爾獎金。他就是這位泰戈爾詩人。”[9]泰戈爾獲獎時,冰島小說家拉克斯奈斯才十五歲,這位到了一九五五年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作家,追述當年泰戈爾的影響道:“這個奇異的、細膩的和遙遠的聲音立即進入了我年輕的精神耳朵的深處。從那時起,我時時刻刻在自己心靈的深處體會它的存在。像對西方讀者一樣,在我們國家里《吉檀迦利》的形象及其芳香產生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優美花朵般的影響。由于它的巨大影響,不少詩人進行創作散文詩的新實驗。”[10]盡管我國是在東方,我國最初介紹泰戈爾的詩歌時的情況,倒是有點兒同斯堪的納維亞的國家相似。
《吉檀迦利》是泰戈爾中期詩歌創作的高峰,所以這部《泰戈爾抒情詩選》從其中選譯的詩篇數量較多,比重較大。石真先生是懂得孟加拉文的,據她的調查研究,《情人的禮物》和《渡》這兩個英譯本,主要選自《宗教頌歌》、《鴻鵠集》、《擺渡集》、《歌之花環》、《吉檀迦利》和《剎那集》,凡此都是屬于中期的創作,所以我從這兩個英譯本中也酌量選譯了一些。泰戈爾在《流螢集》的卷首說:“《流螢集》來源于我的中國和日本之行:人們常常要求我親筆把我的思想寫在扇子和絹素上。”他是一九一六年五月間到達日本的,逗留了三個月,他在日記里寫道:“這些人的心靈像清澈的溪流一樣無聲無息,像湖水一樣寧靜。我所聽到的一些詩篇都是猶如優美的畫,而不是歌。”他還舉了一首青蛙跳進古池塘的俳句為例。他的這些小詩顯然是受了日本俳句的影響;有人認為“這些詩沒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我倒有所偏愛,所以也選譯了一些。《鴻鵠集》是根據泰戈爾的學生奧羅賓多·博斯的英譯本轉譯的,選的詩篇比較多一些,一是因為他是從孟加拉文逐字逐句譯過來的,不像泰戈爾自己翻譯時那樣自由地進行再創作,有所濃縮或刪節。《采果集》、《情人的禮物》、《渡》中好些詩篇都是選自《鴻鵠集》的,我都沒有采擇,如果覺得哪幾首有必要選譯的話,就從博斯的英譯本轉譯,讓讀者借此也多少看到泰戈爾用孟加拉文寫的詩歌是什么模樣的。例如《情人的禮物》第一首是寫泰姬陵的,較短,也簡化了,現在選譯的是《鴻鵠集》的第七首,長了好幾倍,接近結尾的十多行朦朧晦澀之至。二是從思想內容上考慮的。據博斯說,泰戈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寫下了《鴻鵠集》中大部分詩篇。泰戈爾在給他的朋友的信中說道:“我寫《鴻鵠集》時在我內心激發起來的感情仍舊活在我的心里。它們像鴻鵠翱翔似的涌來,像鴻鵠似的從詩人的心靈飛向未知的世界,懷著一種難以表達的、迫不及待的、不平靜的感情。……它們的翅膀不僅擾亂了子夜的寂靜,而且在我的心里喚醒了無限的聲音——那才是真正的意義……因此我把這卷詩集命名為《鴻鵠集》……也許有一個看不見的內在鏈環把詩篇聯系在一起。……我內心里明確起來的思想,也不光是那些關于戰爭的思想。……通過戰爭,傳來一種呼喚,叫我去參加一個四海之內兄弟友誼的節日……我感到人性已經到達了十字路口——在我們的后面躺著過去,黑夜正在臨近盡頭,而穿過死亡和苦惱,一個新世紀的紅色黎明正在破曉。因此,由于一種并不明顯的緣故,我的心靈十分激動!”泰戈爾的思想發展到了一個轉折點,他逐漸向當年高舉“超越戰爭”的旗幟、宣傳兄弟友愛之誼和國際主義的羅曼·羅蘭一邊靠攏了。他自己說得很清楚:“這種感情在我內心里的初次發育成長,我已表達在《鴻鵠集》里。有一段時間,我是在沿著邀我就道的那模糊道路摸索前進的;在這種感情的沖動下,雖然當時我并沒認識到,這些詩篇便產生了。這些詩篇像許多旗幟,標志著我要旅行的途徑。當時不過是一種感情,在詩里的表達也是不明確的,今天可成了一種堅定的認識,我帶著這種認識達到了一個明確的目標。”泰戈爾自己的話替我闡明了從《鴻鵠集》中多選幾篇的緣故,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和品味這些詩篇。
一般的說法是:到了第三階段,隨著泰戈爾重新生氣勃勃地參加政治活動,他的詩歌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一些變化,主要是調子慷慨激昂,洋溢著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的熱情,充滿了反對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正義感。季羨林先生認為,泰戈爾的詩歌,既有“光風霽月”的一面,又有“金剛怒目”的一面。早期和中期以前者為多,晚期以后者為多。詩人去世以后,他生前的朋友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編選了一本共收一百三十首詩的《詩集》,編選的意圖,看來是側重于反映泰戈爾“金剛怒目”、慷慨陳詞那一面。編者對泰戈爾的詩歌創作,按四個時期,分為四輯,即(一)1—57首(1886—1914年);(二)58—87首(1916—1927年);(三)88—112首(1928—1939年);(四)113—130首(1940—1941年)。那個分期,顯然和一般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法是大不相同的。具體記錄如上,一則供研究者參考,二則至少可以據此推算哪些詩是大致在哪些年月里寫作的。從這本《詩集》看來,“光風霽月”和“金剛怒目”這兩個因素,存在于泰戈爾任何時期的詩歌創作里,不過是在某一特定時期里某一因素占主導地位罷了。這部《泰戈爾抒情詩選》,從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編選的《詩集》里采擇了不少政治抒情詩,著重于選譯各個不同時期的那些“金剛怒目”式的詩篇,以補充從《園丁集》、《吉檀迦利》等選譯之不足。《詩集》的(二)、(三)、(四)輯,基本上都是泰戈爾晚期的詩歌,因而選譯的比重大一些,以顯示泰戈爾晚年政治抒情詩的特色。順便說一句,泰戈爾“光風霽月”式的抒情詩固然有些比較晦澀難懂,但“金剛怒目”式的詩,有些也并不好懂,晦澀之處實在參不透的,我就沒有敢選譯,盡管人們經常論及的那些政治抒情詩是基本上都譯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間詩人生了一場大病,真是九死一生,奇跡似地救活了。但他從此一直是病懨懨的,始終沒有完全康復。一九四一年五月朋友們為他慶祝了八十歲生日;同年八月七日,詩人便溘然長逝了。
吉爾伯特·默里教授是泰戈爾生前的朋友,他稱贊泰戈爾“是個真正的詩人,而且是個新型的詩人,他能使東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我頗有同感,因而選譯了這部《泰戈爾抒情詩選》。除了我不懂孟加拉文、掌握的資料不多之外,我在欣賞、理解、采擇和表達等等方面,都有我的局限性,都有力不從心的地方,所以,盡管主觀上自以為是藝苑掇英,很可能實際上卻把偌大花園的好些色彩和芳香留在外面了。這是我必須向讀者致歉的。好在泰戈爾許多詩集的一個又一個的全譯本,仿佛一個又一個的花園,我們國內有的是單行本。例如,我的老師和前輩鄭振鐸先生和冰心先生、精通孟加拉文的石真先生、我的老同事湯永寬同志,都譯過不少泰戈爾的詩篇,有的在我青少年時期就培養了我的審美趣味,有的給了我不少啟發和教益,我至今還是很感激的。
這部抒情詩選,許多是新譯的,舊譯選入也重新作了斟酌或訂正,最后定稿時又得到譯文出版社老編輯的認真校訂,謹致衷心的感謝之情。
吳巖
一九八六年夏
序詩
我在這兒把我的詩篇獻給你,
密密地寫滿這個本子,
仿佛一只籠子里擠滿了鳥兒。
我的詩句成群地飛過的
那蔚藍的空間,那環繞星辰的無限,
可都留在詩集外邊了。
從黑夜的心頭摘下的繁星,
密密地串成一條項鏈,
也許可在天堂近郊
珠寶商手里售個高價,
然而眾神會惦記、懷念
那神圣而不分明的空靈價值。
且想像一首詩歌,像飛魚,突然
從時間的靜默深淵中閃爍地一躍而起!
你可想把它網住,
把它同一群俘獲的魚兒
一起陳列在玻璃缸里?
在公子王孫悠閑的豪華時代里,
詩人天天在慷慨的君王面前
吟詠他的詩篇;
當時沒有印刷機的幽靈
以喑啞的黑色
涂抹那音調鏗鏘的閑暇的背景,
詩篇倒在不相干的自然伴奏下生氣勃勃,
當時一節節詩句
也不是排成一塊塊整齊的字母,
叫人默默地囫圇吞下去的。
唉,專供耳朵靜聽細聽的詩篇,
今天在主人挑剔的眼前給束縛住了,
仿佛一行行用鐵鏈鎖起來的奴隸,
被放逐到無聲紙張的蒼白里去了;
而那些受到永恒親吻的詩歌,
已經在出版商的市場上迷失了道路。
因為這是個匆忙而擁擠的亡命時代,
抒情女神
不得不乘電車和公共汽車
去赴心靈的約會。
我嘆息,我恨不生在
迦梨陀娑[11]的時代,
而你是——這種胡思亂想
又有什么用處?
我絕望地生在繁忙的印刷機時代
——一個姍姍來遲的迦梨陀娑,
而你,我的情人,卻是全然摩登的。
你躺在安樂椅上,
懶洋洋地翻閱著我的詩篇,
而你從來無緣半閉著眼睛
靜聽低吟詩歌的韻律,
聽罷還給詩人戴上玫瑰花冠。
你付出的唯一代價,
就是在大學廣場上
付給那書亭售貨員
幾枚銀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