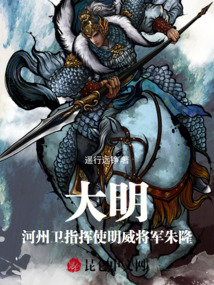
大明河州衛(wèi)指揮使明威將軍朱隆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歸附大明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閏七月,大都城垣已在明軍炮石下斑駁如鱗。朱隆踞坐淮安官署,案頭羊皮地圖上,紅筆圈注的“應天”二字洇開墨痕,恍若滴血。窗外傳來馬蹄聲,副將李安推門而入,甲葉相撞聲里混著血腥氣:“元相孛羅帖木兒率軍西遁,大都四門已開。”
朱隆撫過腰間九環(huán)刀——這是世祖忽必烈親賜的“忠勇”佩刀,刀柄包漿里嵌著半片殘甲,那是十年前他隨王保保征高郵時留下的印記。案頭攤開的《大元通制》被夜風吹得嘩嘩作響,“忠君”二字在燭影里扭曲成荒誕的墨團。他忽然想起三個月前在瓜州見過的明軍:旗號上“山河奄有中華地”六字獵獵,士卒過處,竟無一人踐踏田禾——這與元軍“掠民為糧”的做派判若云泥。
“備馬。”朱隆解下佩刀,換了身青布直裰,將官印用黃綾裹了系在腰間。李安欲言又止,他知道這位提督學道雖掛文職,卻在淮安練了三年鄉(xiāng)勇,麾下五千子弟皆能彎弓貫甲。五更天,朱隆率部開城時,明軍先鋒康茂才的火把已照見護城河上浮冰。
“來者何人?”康茂才橫刀立馬,盔纓上結著霜花。
“元淮安路提督學道朱隆,率部歸明。”朱隆踏前半步,官印在月光下泛著冷光,“所部五千人皆愿棄暗投明,唯求將軍約束士卒,勿驚百姓。”
康茂才審視他片刻,忽然笑道:“早聞淮安有儒將,能治民亦能治軍。某這就修書稟報大將軍,明日渡江,還望朱大人引路。”
渡江那日,朱隆的青布船行在中軍。長江水濁浪翻涌,他望著南岸插滿的“明”字大旗,想起二十年前在汴梁太學讀《春秋》,先生說“王者無敵,言仁厚也”。如今看來,這“仁厚”二字,終是應在了朱元璋的義軍身上。船至中流,忽有漁船破浪而來,漁民們舉著荷葉包的炊餅,向明軍船隊拋擲——這是他從未在元軍中見過的景象。
入應天后,朱元璋在奉天殿召見歸降諸將。朱隆跪在丹墀下,聽著殿角銅鈴與皇帝的話語交疊:“聞卿在淮安,令行禁止,秋毫無犯。今授武德衛(wèi)指揮僉事,仍領舊部,隨徐達將軍掃平江南。”抬頭時,正撞見朱元璋眼底的灼灼鋒芒,那是比刀劍更鋒利的威懾與期許。
歸營后,李安摸著新賜的明軍校尉腰牌嘆道:“大人真信這朱皇帝能容我們這些前朝舊臣?”朱隆擦拭著新領的柳葉刀,刀身映出他鬢角的星霜:“元朝氣數已盡,百姓需要的是能讓他們安居樂業(yè)的朝廷。至于你我……”他忽然望向轅門外,那里有幾個明軍士卒正幫百姓修補被元軍燒毀的茅屋,“只要手里的刀是為護民而揮,何愁沒有容身之處?”
第二章江南平叛
吳元年(1369年)春,朱隆率部隨湯和征討浙東。方國珍的殘部踞守黃巖,憑借濱海地勢負隅頑抗。明軍水師初戰(zhàn)失利,湯和急召諸將議事,帳中氣氛如受潮的弓弦般緊繃。
“賊軍善用海船,我軍舟師不習水戰(zhàn)。”副將皺著眉指向沙盤上的潮汐線,“若強攻,必損折過半。”
朱隆卻盯著地圖上的“桃渚”——那是個被礁石環(huán)繞的小港灣,潮間帶生長著大片蘆葦。他忽然想起在淮安時,曾見漁民在淺灘用“埕塢”困住游魚:“末將請領兩千步卒,趁夜從桃渚登陸。”他抽出佩刀,在沙盤中劃出弧線,“潮漲時賊軍船高,必難察覺淺灘動靜;待潮退,彼船擱淺,我軍可焚其舟。”
湯和擊節(jié)稱善:“好個‘以潮為計’!”當夜,朱隆命士卒褪去甲胄,裹著牛皮泅渡。水冷如刀,他踩著礁石前行,腳底被牡蠣殼劃出血痕卻渾然不覺。四更天,潮水退去,三十六艘賊船果然擱在灘涂上,水手們正蜷縮在艙中酣睡。
“點火!”朱隆一聲令下,蘆葦捆的火油潑向船板,剎那間火光映紅海天。方國珍部驚醒時,已如困在淺灘的魚,被明軍步卒砍瓜切菜般屠戮。朱隆持刀立在船頭,看著賊首的首級在火光中滾落,忽然聽見不遠處傳來啜泣——艙底竟藏著十幾個被擄的百姓。他解下披風裹住瑟瑟發(fā)抖的孩童,柔聲說:“別怕,明軍來了,你們回家。”
此戰(zhàn)后,朱隆“儒將”之名在江南傳開。攻常州時,他嚴禁士兵踏入文廟,親自率人用布幔遮住孔子像;過蘇州時,又下令將繳獲的官糧分一半給災民。有老儒跪在馬前獻詩:“將軍下馬拜先師,卻令豺狼化雨絲。”他卻只是一笑,將詩稿收進兵書,繼續(xù)琢磨如何破張士誠的“鐵騎兵”。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明軍合圍平江。朱隆部負責攻打閶門,張士誠的弟弟張士德在此布下“飛天弩”,箭矢可及三百步。朱隆命人收集百姓的棉被,浸滿泥漿后制成盾牌,又在弩箭射程外堆砌土臺,架起火炮轟擊城樓。十日后城破,他率部入城時,見路邊有婦人抱著襁褓哭泣,襁褓中嬰兒的襁褓上繡著“隆平”二字——那是張士誠當年的年號。他下馬將隨身的干糧分給婦人,輕聲說:“天下很快就會太平,孩子該有個新名字了。”
第三章北伐建功
洪武三年(1370年)春,大漠尚未解凍,朱隆已隨徐達踏上第二次北伐之路。雁門關外,積雪沒過馬腹,他望著遠處忽起的黃塵,知道那是王保保的“精騎營”來了。
“列‘鴛鴦陣’!”朱隆一聲令下,五千步卒迅速結成小陣,長槍與短刀相護,盾牌如鱗甲般密合。王保保的騎兵沖至百步內,忽然馬蹄陷入明軍預先挖好的陷馬坑,慘叫聲中,鐵蹄濺起的血花染紅白雪。朱隆趁勢揮刀:“斬馬足!”士卒們伏地出刀,專砍戰(zhàn)馬前蹄,騎兵紛紛墜地,被亂槍刺死。
這一仗,明軍斬首八千級,王保保僅率數騎遁走。捷報傳至應天,朱元璋親書“忠勇可嘉”賜給朱隆,擢升他為弘農衛(wèi)指揮使,世襲罔替。班師回朝時,朱隆在汴梁遇見了當年的太學同窗——如今的河南布政使宋訥。酒酣耳熱間,宋訥指著他鎧甲上的新傷:“當年你若留在元廷,此刻怕是要在大漠喝風了。”朱隆舉杯飲盡:“元廷失了民心,便是有十萬精騎,又能守得住幾時?”
次年,朱隆隨鄧愈西征吐蕃。出涼州后,地勢漸高,空氣稀薄得讓人喘不過氣。某日行軍至烏鞘嶺,忽有吐蕃騎兵從山隘沖出,箭如雨下。朱隆急令部隊退入峽谷,卻見前方峭壁上刻著“漢將班超西征處”幾個大字,斑駁的字跡在夕陽下宛如血痕。他忽然福至心靈,命人將火把系在山羊角上,驅趕千只山羊向敵營沖去。夜色中,滿山火光晃動,吐蕃人以為明軍伏兵盡出,竟自相踐踏,潰不成軍。
戰(zhàn)后,鄧愈拍著朱隆的肩膀大笑:“都說你是儒將,我看你這腦子,比刀還快!”朱隆卻望著遠處的雪山,想起《漢書》里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話——如今他西征,又何嘗不是在重走前人的拓土之路?只是班超為漢家,他為朱家,卻都是為了讓邊疆百姓不再受戰(zhàn)火之苦。
洪武五年,朱隆班師回朝,在應天城遇見了剛滿十歲的長子朱芾。孩子抱著他的腿,仰頭望著他鎧甲上的血銹:“父親,戰(zhàn)場上的刀,真的能讓天下太平嗎?”他抱起兒子,看著宮墻上的琉璃瓦在暮色中泛著柔光:“等你長大就會明白,有些刀必須揮,才能讓更多人放下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