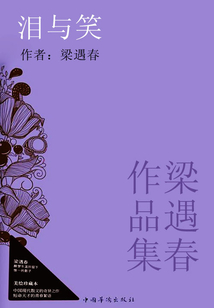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8評論第1章 梁遇春:春醪集 (1)
序
那是三年前的一個夏天,我正在北大一院圖書館里,很無聊地翻閱《洛陽伽藍記》,偶然看到底下這一段:
劉白墮善釀酒,飲之香美,經月不醒。青州刺史毛鴻賓赍酒之藩,路逢劫賊,飲之即醉,皆被擒獲。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但畏白墮春醪。”
我讀了這幾句話,想出許多感慨來。我覺得我們年青人都是偷飲了春醪,所以醉中做出許多好夢,但是正當我們夢得有趣時候,命運之神同刺史的部下一樣匆匆地把我們帶上衰老同墳墓之途。這的確是很可惋惜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又想世界既然是如是安排好了,我們還是陶醉在人生里,幻出些紅霞般的好夢罷,何苦睜著眼睛,垂頭嘆氣地過日子呢?所以在這急景流年的人生里,我愿意高舉盛到杯緣的春醪暢飲。
慚愧得很。我沒有“醉里挑燈看劍”的豪情,醉中只是說幾句夢話。這本集子就是我這四年來醉夢的生涯所留下惟一的影子。我知道這幾十篇東西是還沒有成熟的作品,不過有些同醉的人們看著或者會為之莞爾,我最大的希望也就是如此。
再過幾十年,當酒醒簾幕低垂,擦著惺忪睡眼時節,我的心境又會變成怎么樣子,我想只有上帝知道罷。我現在是不想知道的。我面前還有大半杯未喝進去的春醪。
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午夜于真茹。
講演
“你是來找我同去聽講演嗎?”
“不錯,去不去?”
“嚇!我不是個‘智識欲’極旺的青年,這么大風——就是無風,我也不愿意去的。我想你也不一定是非聽不可,盡可在我這兒談一會。我雖然不是什么名人,然而我的嘴卻是還在。剛才我正在想著講演的意義,你來了,我無妨把我所胡思亂想的講給你聽,講得自然不對,不過我們在這里買點東西吃,喝喝茶,比去在那人叢里鉆個空位總好點吧。”
來客看見主人今天這么帶勁地談著,同往常那副冷淡待人的態度大不相同,心中就想在這里解悶也不錯,不覺就把皮帽圍巾都解去了。那房主人正忙著叫聽差買栗子花生,泡茶。打發清楚后,他又繼續著說:
“近來我很愛胡思亂想,但是越想越不明白一切事情的道理。真合著那位坐在望平街高塔中,做《平等閣筆記》的主筆所謂世界中不只‘無奇不有’,實在是‘無有不奇’。Carlyle這老頭子在Saitor Resartus中‘自然的超自然主義’(Natural Supernaturalism)一章里頭,講自然律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解的神秘,所以這老頭子就覺得對于宇宙中一切物事都糊涂了。我現在也有點覺得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比如你是知道我怕上課的,自然不會愛聽講演。然而你經過好幾次失敗之后,一點也不失望,還是常來找我去聽講演,這就是一個Haeckel的《宇宙之謎》所沒有載的一個不可思議的事。哦!現在又要上課了,我想起來真有點害怕。嚇!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從前我們最高學府是沒有點名的,我們很可以自由地在家里躺在床上,或者坐在爐邊念書。自從那位數學教授來當注冊部主任以后,我們就非天天上班不行。一個文學士是坐硬板凳坐了三千多個鐘頭換來的。就是打瞌睡,坐著睡那么久,也不是件容易事了。
怕三千多個鐘頭坐得不夠,還要跑去三院大禮堂,師大風雨操場去坐,這真是天下第一奇事了。所以講演有人去聽這事,我抓著頭發想了好久,總不明白。若說到‘民國講演史’那是更有趣了。自從杜威先生來華以后,講演這件事同新思潮同時流行起來。杜先生曾到敝處過,那時我還在中學讀書,也曾親耳聽過,親眼看過。印象現在已模糊了,大概只記得他說一大陣什么自治,磚頭,打球,……后來我們校長以‘君子不重則不威’一句話來發揮杜先生的意思。
那時翻譯是我們那里一個教會學堂叫做格致小學的英文先生,我們那時一面聽講,一面看那潔白的桌布,校長的新馬褂,教育廳長的臉孔,杜先生的衣服……我不知道當時杜先生知道不知道How we think。跟著羅素來了,恍惚有人說他講的數理哲學不大好懂。羅素去了,杜里舒又來。中國近來,文化進步得真快,講演得真熱鬧,杜里舒博士在中國講演,有十冊演講錄。中間有在法政專門學校講的細胞構造,在體育師范講的歷史哲學,在某女子中學講的新心理學總而言之普照十方,凡我青年,無不蒙庇。所以中國人民近來常識才有這么發達。泰戈爾來京時,我也到真光去聽。他的聲音是狠美妙。可惜我們(至少我個人)都只了解他的音樂,而對于他的意義倒有點模糊了。
“自杜先生來華后,我們國內名人的講演也不少。我有一個同學他差不多是沒有一回沒去聽的,所以我送他一個‘聽講博士’的綽號;他的‘智識欲’真同火焰山一樣的熱烈。他當沒有講演聽的時候只好打呵欠,他這樣下去,還怕不博學得同哥德,斯忒林堡一樣。據他說近來很多團體因為學校太遲開課發起好幾個講演會,他自然都去聽了。他聽有‘中國工會問題’,‘一個新實在論的人生觀’,‘中外戲劇的比較’,‘中國憲法問題’,‘二十世紀初葉的教育’我問他他們講的什么,他說我聽得太多也記不清了,我家里有一本簿子上面貼有一切在副刊記的講演辭,你一看就明白了。
他怕人家記得不對,每回要親身去聽,又恐怕自己聽不清楚,又把人家記的收集來,這種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模仿的,不過我很替他們擔心。講演者費了半月工夫,遲睡早起,茶飯無心,預備好一篇演稿來講。我們坐洋車趕去聽,只恐太遲了,老是催車夫走快,車夫固然是汗流浹背,我們也心如小鹿亂撞。好,到了,又要往人群里東瞧西看,找位子,招呼朋友,忙了一陣,才鴉雀無聲地聽講了。聽的時候又要把我們所知道的關于工會,憲法,人生觀,戲劇,教育的智識整理好來吸收這新意思。講完了,人又波濤浪涌地擠出來。若使在這當兒,把所聽的也擠出來,那就糟糕了。
“我總有一種偏見:以為這種Public-lecture-mania是一種Yankee-disease。他們同我們是很要好的,所以我們不知不覺就染了他們的習慣。他們是一種開會,聽講,說笑話的民族。加拿大文學家Stepken Leacock在他的My Discovery of England里曾說過美國學生把教授的講演看得非常重要,而英國牛津大學學生就不把lecture當作一回事,他又稱贊牛津大學學生程度之好。真的我也總懷一種怪意思,因為怕挨罵所以從來不告人,今日無妨同你一講。請你別告訴人。我想真要得智識,求點學問,不只那東鱗西爪吉光片羽的講演不濟事,就是上堂聽講也無大意思。教授盡可把要講的印出來,也免得我們天天冒風雪上堂。真真要讀書只好在床上,爐旁,煙霧中,酒瓶邊,這才能領略出味道來。所以歷來真文豪都是愛逃學的。至于Swift的厭課程,Gibbon在自傳里罵教授,那又是紳士們所不齒的,……”
他講到這里,人也倦了,就停一下,看桌子上栗子花生也吃完,茶也冷了。他的朋友就很快地講:
“我們學理科的是非上堂不行的。”
“一行只管一行,我原是只講學文科的。不要離題跑野馬,還是談講演吧,我前二天看Mac Dougall的《群眾心理》,他說我們有一種本能叫做?愛群本能’(Gregarious instinct),他說多數人不是為看戲而去戲院,是要去人多地方而去戲院。干脆一句話,人是愛向人叢里鉆的。你看他的話對不對?”他忽然跳起,抓著帽和圍巾就走,一面說道:
“糟!我還有一位朋友,他也要去三院瞧熱鬧,我跑來這兒談天,把他在家里倒等得慌了。”
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于北大西齋。
寄給一個失戀人的信(一)
秋心:
在我這種懶散心情之下,居然呵開凍硯,拿起那已經有一星期沒有動的筆,來寫這封長信;無非是因為你是要半年才有封信。現在信來了,我若使又遲延好久才復,或者一擱起來就忘記去了;將來恐怕真成個音信渺茫,生死莫知了。
來信你告訴我你起先對她怎樣鐘情想由同她互愛中得點人生的慰藉,她本來是何等的溫柔,后來又如何變成鐵石心人,同你現在衰頹的生活,悲觀的態度。整整寫了二十張十二行的信紙,我看了非常高興。我知道你絕對不會想因為我自己沒有愛人,所以看別人丟了愛人,就現出卑鄙的笑容來。若使你對我能夠有這樣的見解,你就不寫這封悱惻動人的長信給我了。我真有可以高興的理由。在這萬分寂寞一個人坐在爐邊的時候,幾千里外來了一封八年前老朋友的信,痛快地暴露他心中最深一層的秘密,推心置腹般娓娓細談他失敗的情史,使我覺得世界上還有一個人這樣愛我,信我,來向我找些同情同熱淚,真好像一片潔白耀目的光線,射進我這精神上之牢獄。最叫我滿意是由你這信我知道現在的秋心還是八年前的秋心。八年的時光,流水行云般過去了。
現在我們雖然還是少年,然而最好的青春已過去一大半了。所以我總是愛想到從前的事情。八年前我們一塊游玩的情境,自然直率的談話是常浮現在我夢境中間,尤其在講堂上睜開眼睛所做的夢的中間。你現在寫信來哭訴你的怨情簡直同八年前你含著一泡眼淚咽著聲音講給我聽你父親怎樣罵你的神氣一樣。但是我那時能夠用手巾來擦干你的眼淚,現在呢?我只好仗我這枝禿筆來替那陪你嗚咽,撫你肩膀低聲的安慰。秋心,我們雖然八年沒有見一面,半年一通訊,你小孩時候雪白的臉,桃紅的頰同你眉目間那一股英武的氣概卻長存在我記憶里頭,我們天天在校園踏著桃花瓣的散步,樹蔭底下石階上面坐著唧唧噥噥的談天,回想起來真是亞當沒有吃果前樂園的生活。當我讀關于美少年的文學,我就記起我八年前的游伴。
無論是述Narcissus的故事,Shakespeare百余首的十四行詩,Gray給Bonstetten的信,Keats的Endymion,Wilde的Dorian Gray都引起我無限的愁思而懷著久不寫信給我的秋心。十年前的我也不像現在這么無精打采的形相,那時我性情也溫和得多,面上也充滿有青春的光彩,你還記著我們那一回修學旅行吧?因為我是生長在城市,不會爬山,你是無是不在我旁邊,拉著我的手走上那崎嶇光滑的山路。你一面走一面又講好多故事,來打散我恐懼的心情。我那一回出疹子,你瞞著你的家人,到我家里,瞧個機會不給我家人看見跑到我床邊來。你喘氣也喘不過來似講的:“好容易同你談幾句話!我來了五趟,不是給你祖母攔住,就是被你父親拉著,說一大陣什么染后會變麻子……”這件事我想一定是深印在你心中。憶起你那時的殷勤情誼更覺得現在我天天碰著的人的冷酷,也更使我留戀那已經不可再得的春風里的生活。提起往事,徒然加你的惆悵,還是談別的吧。
來信中很含著“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的意思。這差不多是失戀人的口號,也是失戀人心中最苦痛的觀念。我很反對這種論調,我反對,并不是因為我想打破你的煩惱同愁怨。一個人的情調應當任它自然地發展,旁人更不當來用話去壓制它的生長,使他墮到一種莫名其妙的煩悶網子里去。真真同情于朋友憂愁的人,絕不會殘忍地去撲滅他朋友懷在心中的幽情。他一定是用他的情感的共鳴使他朋友得點真同情的好處,我總覺“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這句話對“過去”未免太藐視了。我是個戀著“過去”的骸骨同化石的人,我深切感到“過去”在人生的意義,盡管你講什么,“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后種種譬如今日生”同Let bygones be bygones;“從前”是不會死的。不算形質上看不見,它的精神卻還是一樣地存在。“過去”也不至于煙消火滅般過去了;它總留下深刻的足跡。理想主義者看宇宙一切過程都是向一個目的走去的,換句話就是世界上物事都是發展一個基本的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