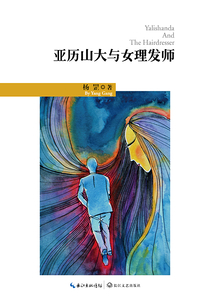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詩人要有“猛禽殺”之心——序楊罡詩集《亞歷山大與女理發師》
周瑟瑟
楊罡近年的寫作我較為熟悉,他每當寫出一首詩就會發給我看。我會及時表達我的意見,好或不好我們無所不談。我的意見他聽得進,他不固執,有時他把一首詩改了多遍,但我卻固執地認為最初那一稿最好,我會說出我的理由,好在哪里,他改掉的是一首詩最能打動我的寫法,而變成了一首在我眼里沒有特點的壞詩。他本來很興奮,被我潑了一通冷水后,也不沮喪,我也有耐心,我說服他改回原詩。下面這首《猛禽殺》就被他差點改掉了我欣賞的寫法,這次他要出版詩集,我看還是保持了原樣。
我恨不得親手殺死它
那只可惡的黑色的猛禽
它不停啄食我的妹妹
它來去無蹤
它來的時候
總是破窗而入
在北方之北,每一回
我都能聽到
玻璃被瞬間擊碎的尖叫
從贛西北,遠遠傳來
然后我看到我的妹妹
蹲在她的小屋里
大聲哭泣
那雙在春天種下玫瑰的手
鮮血直流
她以鮮血直流的顫抖的雙手
掩面哭泣
她手上的血,一滴到地上
就變為花瓣
那只黑色的猛禽
來了又去,去了又來
它總是時不時地
啄食妹妹那張秀美的臉
并留下暗紅的疤痕
啄食她那雙清澈的眼眸
現在,那里已空洞無光
它還啄食她那顆善良的心
如今,那顆善良的心
早已分不清
何為善良,何為邪惡
何為幸福,何為希望
它甚至感覺不到痛
也感覺不到愛
它只能偶爾感覺到悔恨
當她悔恨的時候
它啄她的心就更為猛烈
它不停啄食我的妹妹
那只邪惡的黑色的猛禽
我恨不得親手殺死它
——《猛禽殺》
楊罡的作品大部分我都讀過,還不止一次讀,這首《猛禽殺》第一眼就抓住了我。楊罡處理情感、語言與敘述的手法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的敘述直接,不繞彎,第一句上來就是:“我恨不得親手殺死它”,沒有任何鋪墊,正是由于他的直接,全詩一開始就有了兇狠的效果。
楊罡這首詩無疑為現代詩寫作提供了一個樣本,如何讓詩直接進入詩的核心,而不在詩的邊緣打轉,直接有效地進入,不讓詩停頓,他做到了。“那只可惡的黑色的猛禽/它不停啄食我的妹妹”,很快他就給出了詩的基本事實。這就是全部真相,但楊罡沒有一味陷入對真相的闡述,而是拋開詩之外的邏輯去創造屬于詩本身的那一部分——詩的想象在楊罡的寫作里上升到了現實之外的高度。
猛禽與妹妹是詩的兩個對立主體,而我是誰?我是在詩的開始與最后強調的“我恨不得親手殺死它”的那個人。猛禽是“邪惡的黑色的”,這是詩人的敘述策略,給出一個喻體,然后不再回避喻體的本來面目,它是“邪惡的黑色的”猛禽,它的“破窗而入”撕開了妹妹的善,“啄食”的動作反復出現,增加了詩的殘忍與血腥。
善與惡的對立,詩的敘述在一個基本的事實里進行,善惡廝打卻不混亂,楊罡有條理地講述,讓讀者明白了詩的現實。他制造了一個巨大的隱喻,這首詩之所以寫得驚心動魄,是因為楊罡抓住了損害與被損害之間的沖突,當損害到一定的程度,損害變得更加的兇猛。
楊罡的寫作一直在口語的快感中狂歡,而這首詩卻是在損害中達到了痛苦的狂歡。“當她悔恨的時候/它啄她的心就更為猛烈”,損害才是詩的真相。而善良、幸福與愛卻已經麻木,或者沉溺于被損害的快感。
“我”目睹這場損害與被損害的游戲,“我恨不得親手殺死它”是作為哥哥的真實意愿。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寫下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生活的事實。楊罡顯然將詩從生活中拯救出來,高于生活不是什么技巧,詩的高度取決于詩人內心的情感有多熾烈。
從這首詩可以看出,詩人心靈的角斗場有多大,詩的內部空間就有多大。楊罡營造了現代詩緊張的氣氛,“它來去無蹤/它來的時候/總是破窗而入/在北方之北,每一回/我都能聽到/玻璃被瞬間擊碎的尖叫/從贛西北,遠遠傳來/然后我看到我的妹妹/蹲在她的小屋里/大聲哭泣”,我們沉浸在詩的緊張氣氛的擴張之中時,會以為他所寫的是真實的生活,其實詩就是詩,詩與生活可以是兩碼事,只是這首詩在虛構中獲得了真實的效果,讓人誤以為楊罡在寫一段痛苦的故事,差點忘記了他虛構的細節,這正是詩人將虛構營造出真實氛圍的策略。
讀完全詩,我們不僅要追問:“猛禽”到底是什么?而妹妹又是誰?楊罡把形而上的寫作引向何方?
對美的破壞,對善的侵害,對生活的占有,這樣的遭遇我們常常面對,卻無能為力,“我恨不得親手殺死它”也只能是對惡的回應。站在恐怖主義向人類發出挑戰的時代來理解這首詩,或許我們能讀出更多真實的痛苦,詩中妹妹“鮮血直流的顫抖的雙手”與她“掩面哭泣”的場景無不令人動容。
但楊罡不是一個煽情的詩人,或者他把自己的本來面目隱藏了起來,他堅持以一種冷卻的手法處理熾烈的情感,堅持以客觀的敘述表達愛恨。正是這樣客觀的寫作方式讓這首詩達到了情感沖突與壓抑的巔峰。
楊罡的虛構又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如今,那顆善良的心/早已分不清/何為善良,何為邪惡/何為幸福,何為希望/它甚至感覺不到痛/也感覺不到愛”,這樣的表述如果在別處會顯得輕淺,而在此處則有了沉重與無奈,讓我們看到了被損害后的善,善永遠在善應有的地方,“它只能偶爾感覺到悔恨”,而惡也在惡應有的地方,“當她悔恨的時候/它啄她的心就更為猛烈”。
楊罡難道藏有詩的秘密?他第一次發這首詩給我時是征求修改意見,他改了幾稿均被我否定了,我相信他的第一稿是最好的。
“猛禽”是邪惡的力量,是黑暗的象征,而妹妹是美好與善良,是我們人類共同的妹妹。形而上的寫作包含了道德、正義與良知,更是人性深處對美與善的保護,對邪惡與黑暗的咬牙切齒。我們見多了這樣宏大的人類主題式寫作,但楊罡這首詩卻寫出了與眾不同的效果。
楊罡并不是一個持續寫作的詩人,他應該有多年不寫或離開詩歌現場很久了,他與我聯系上后,才有一定的創作量。一個人如果離開詩歌現場太久,要想盡快恢復對詩歌的敏銳感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喪失掉了詩歌的敏銳感覺,要找回來很難。
在我的印象里楊罡的寫作并沒有多大困難,他對詩歌的敏銳感覺一直在,并且還很強勁。這主要體現在他與語言的順暢關系上,他不是一個為難自己的詩人,他的詩歌態度在有話要寫的層面,這是一個把腦子里所想付諸詩歌寫作的人,不繞彎,直接寫下他想寫的詩歌,他把詩歌變成舒服的或者與生活平等的表達。不像有些人把寫詩這件事弄得神乎其神,陷在其中不能自拔,小到讓自己變得痛苦不堪,大到丟了性命。
而楊罡的寫作在我看來是生命里自然溢出來的一種狀態,包括我特別欣賞的《猛禽殺》都是自然溢出來的作品,與他這個人的寫作狀態是貼身的,是一體的,不把自我的敏銳感覺與詩歌分離,而是緊緊貼在一起,是一個好詩人的寫作習慣,或者說是一個人能否成為好詩人的前提。不為難自己或許是外在的,但楊罡本質上關注的是個體的真實感受與他內在的生命經驗。
楊罡的作品還有一個自然的屬性:吟唱與憂傷。他很大一部分作品呈現了一個中年男人暢快淋漓的吟唱與無所顧忌的憂傷。
他的詩骨子里有一股歡快或憂郁在涌動,他在《向日葵》一詩最后寫道:“在燦爛笑容的背后/你心中那深埋的悲傷”,無論是憂傷情緒還是吟唱風格,都不屬于當下詩歌的流行元素,但我相信這是楊罡骨子里的本來面目。通常我們說什么人寫什么詩是有一定道理的,楊罡說他從小多病,他溫文爾雅,我看他骨子里是憂傷的。他屬于有自己的寫作路數的人,這一點不讓人擔心。
北方的煉丹爐
高聳著,直指蒼穹
冒著接天的乳白的濃煙
在凜冽的寒風中
寂寞燃燒
——《煉丹爐》
“煉丹爐”又是一個絕妙的詩歌喻體,而我要說的是楊罡敏感的心,他寫的是懷鄉病,但在異鄉人的憂傷里滲進了小小的超脫,甚至在他的詩里有不少嘻戲與幽默。尤其是他近兩年的作品越來越試圖消解生活的壓抑,而在消解中去創造詩歌的價值與意義。
再看他的吟唱:
蟋蟀把歌聲撒在花下
螢火把燈籠掛在草間
青蛙撲通跳進荷塘
黃狗趴在地上支棱著耳朵
爺爺咕嘟咕嘟抽著水煙
奶奶有一陣沒一陣搖著蒲扇
梨樹下橫著那張竹榻
竹榻上躺著那個少年
那個小小的少年啊
正仰望著星空
——《梨樹下》
典型的鄉村謠曲,透出淡淡的少年的生命體悟。楊罡本人好像也偏愛這類作品,這可能與一個從小多病的鄉村少年的生活有關,也可能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少年的成長有關,其實我們都有過類似的生命體驗與成長過程中的人文影響。
記錄個體生命的人文感受,包括生活與歷史場景的記憶,是詩歌作為人類情感的載體不可回避的路徑。楊罡在少年時浸染的憂傷之美延續到今天,恰是他忠于個體生命從而回應命運的體現。
而楊罡的嘻戲與幽默消解了生活的無聊,與我所說的“卡丘主義”美學原則保持了一致。他作為“卡丘主義”詩歌群體中的一員,創造了他的認知與有趣。
電剪的吱吱聲一會兒就停了
女理發師把白色的圍布輕輕一掀
白頭發與黑頭發一股腦掉到地上
中年男人頂著光頭走出了發廊
鋪天蓋地的夜色,如此溫柔
立刻還了他一頭濃密的黑發
——《亞歷山大與女理發師》
《亞歷山大與女理發師》一詩還原了生活的現場,有趣的對話讓生活變得不那么沉重與壓抑,從一個角度消解了《猛禽殺》的痛苦與無奈,讓詩歌在形而上與形而下兩個支點中找到了平衡。他已經形成了一種后現代性“卡丘”式敘述與形而上的隱喻式批判。
從這部詩集看來,楊罡既有痛苦的批判,又有歡快的吟唱,更有無邊的嘻戲與幽默。為什么我沒有建議這部詩集叫做《猛禽殺》而建議叫《亞歷山大與女理發師》,因為我覺得他這部詩集更多時候是在生活的現場表達他的態度,而不是在隱喻中批判。雖然我很欣賞一個詩人常懷“猛禽殺”之心,保持對生活的懷疑、消解與批判的態度,但楊罡畢竟屬于他自己,任何評論都只能佐證他在某一階段的寫作。
楊罡還會寫出什么好玩與有趣的作品?或者他還會拿出更猛的“猛禽殺”?對于他這樣把寫作與自我貼身的人,二者都有可能。
2015年11月15日于北京樹下齋
周瑟瑟,湖南人,現居北京。著名詩人,小說家,卡丘主義詩歌主要倡導者,紀錄片導演。著有詩集《塵世的禮物》《私有制》等9部,長篇小說《曖昧大街》《中關村的烏鴉》等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