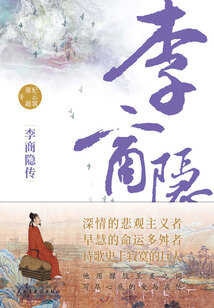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欲問孤鴻向何處》:借山為名
李商隱聰穎早慧,曾自述“五年誦詩書,七年弄筆硯”,他接受的文學啟蒙很早。但父親早逝,他自幼便飽嘗世情炎涼,因而特別多情、重情。
名于其人,可以是一根錚錚鐵骨,不負道義不負自己;也可以是一根刺,扎在“一生襟抱未曾開”的心頭。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商山,位于陜西商洛之南,因商鞅封邑而得名。
商鞅變法把秦國送上了戰國七雄之一的位置,也為日后秦王嬴政掃蕩六國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只是歷史風云莫測,王朝的更迭一如山間草木的枯榮,秦朝僅傳二世而亡,天下很快陷入楚漢之爭。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如今側耳傾聽,山風過處,似乎還有曾經的刀光劍影,鐵馬爭鳴。
相傳,東園公唐秉、綺里季吳實、夏黃公崔廣、甪里先生周術四人有大才,曾被劉邦屢召之而不得。原來這四人皆是秦時的博士。后來,因不滿秦始皇“焚書坑儒”,唐、周、吳、崔四位博士相約隱居商山,不問世事。當時四人皆已年過八旬,須發皓然,飄然若仙,便被人稱為“商山四皓”。白云深處,巖洞之中,四皓與松柏為友,采紫芝療饑,甘守清貧,不為繁華易素心,并作《紫芝歌》明志——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
樹木莫莫,高山崔嵬。
巖居穴處,以為幄茵。
曄曄紫芝,可以療饑。
唐虞往矣,吾當安歸。
再后來,劉邦打敗項羽,得了天下,多次派人以重金聘請四皓出山,皆被拒絕。
直到有一天,劉邦欲廢太子劉盈,改立戚夫人之子劉如意,劉盈生母呂后托張良獻計,四皓才愿意出山輔佐太子。
宴席上,劉邦見四皓站在劉盈身后,方才意識到劉盈乃民心所向,羽翼已豐,遂作詩感嘆:“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再不提廢太子之事。
功成之后,四皓拂衣而去,又隱入商山,深藏身與名。
從此,商山與四皓,一并名垂青史。
商山兩個字,落在歷史的冊頁上,也如白云照春海,仙氣與古意徐徐而來。
“商山隱士,高義如山”,這便是李商隱名和字的由來。
因為李商隱璀璨的詩文,在許多人心中,商山,除了是一種精神,一種文學的意象、志趣的指向之外,又多了一份溫柔的情感聯結,帶著滄海凝成珠淚的浪漫與美玉生煙的清愁,也帶著宿命的啟示與因緣。
隴西李氏,世代冠族,門第高華,有說法當時天下言李者,必稱來自隴西。
只是造化弄人,自李暠而下分支,其子李歆一脈扼住了權力命門,建立龐大的帝國,延綿近三百年;其子李翻后裔像是被命運下了詛咒,雖天資聰穎,卻人丁單薄,年壽不永,鮮有高官……
沿著家世一路溯源,順著名字抽絲剝繭,我們可以看到——
李商隱的高祖名叫李涉,正是李翻的后人。李涉擔任過的最高行政職位是美原縣令。涉,有博涉書記之意。李商隱的曾祖李叔恒少年得志,十九歲即考取進士,且有詩名,無奈二十九歲早逝,官職僅止于安陽縣尉。恒,“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寓官運亨通,生命力強盛。李商隱的祖父李俌明經及第,任邢州錄事參軍,奈何英年離世。李商隱的父親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獲嘉縣令,卻在李商隱十歲時猝然離世,命喪江南異鄉。嗣,繼承之意也。
李商隱,拖著多愁多病的身,登上了晚唐詩壇的巔峰,卻一直科舉不順,仕途坎坷,生活困頓,郁郁不得志。命運,就像帶著某種遺傳的基因,已刻進了他的骨子里,寫在了他的血脈中。
他有致君堯舜之志,有妙筆生花之才,也有皓然如山的高義,玉壺冰心的品格,奈何是非成敗,皆緣于此。
西諺云:性格決定命運。然也。
他屢試不第,一生輾轉幕府,從未真正接近權力的中心,擔任過的最高官位也就是一個從五品上的幕府憲職。
在時代的洪流中,在黨爭的刀劍中,他漂泊無定,形同斷梗浮萍,回歸故鄉時已是一身愁病,終年不過四十七歲。
李商隱是家中長子,是李嗣在生下兩個女兒之后期盼多年的麟兒,也是繼承李家香火、承載家族希望的人。
商山隱士,高義如山——顯然,李嗣借山為長子名,其實是把自己的政治寄望與家族心愿,都放在了長子的肩膀上。
李商隱一歲時,他的弟弟羲叟出生。從羲叟的名字不難看出,李嗣對下一代的寄望與心愿,已近乎執念——羲,堯時掌天文的官吏;叟,即老人,代表著長壽。
而商山四皓,不僅知識淵博,名滿天下,進一步有擔當帝王顧問、定國之才的能力與高義,退一步有歸隱山林、堅守素心的自由與灑脫,身體里,還有李嗣家族不常有的耄耋高壽。
人生若此,夫復何求?
那么李商隱的子孫們呢?
唐代筆記小說中說李商隱有兩個兒子,一子名曰“白老”,因為他的忘年之交白居易有一心愿——“若來世投胎,但愿成為李商隱的兒子”。可惜白老資質平平,與仕途無緣。一子名曰“袞師”,自小聰慧,有鳳雛之姿,“袞師我驕兒,美秀乃無匹”,從李商隱的詩句中也可以看出,這位“驕兒”很是討人喜愛。袞,天子禮服,也可引申為帝王。
但實際上,李商隱的詩文中并沒有任何關于“白老”的記錄,倒有旁枝末節表明,袞師這個名字寄托了李商隱對于孩子的美好祝福。他一定想著這個孩子能夠成為“美秀乃無匹”的代表。不過,袞師到底只是一個未被錄入史冊的名字,可謂泯然眾人矣。
幸焉?不幸焉?
帝王之師確實榮耀,卻難免陷入伴君如伴虎的境地,行走于朝堂,無異于行走于刀尖,個中冷暖,當如人飲水;若為平民百姓,布衣蔬食、無災無病過一生,也未必就是辱沒和失敗——當然,前提是生在和平年代。
李商隱祖籍懷州(今河南沁陽市),祖上遷居鄭州滎陽(他的祖父、父親都在那里出生成長),但他的出生地又回到了懷州獲嘉。
唐憲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商隱出生在懷州獲嘉的縣令官舍里,當時他的父親李嗣正在獲嘉任上。
那是歷史上的元和中興時期,唐憲宗有心重振朝綱,試圖把帝國的政治拉回正軌,然而,安史之亂的后遺癥已是入骨之毒,憲宗平定了部分藩鎮的叛亂,終究還是無法根除種種沉疴。
所謂中興,不過是夕陽下山前的余暉罷了。
而在僅僅八年之后,歷史上偉大的唐帝國就陷入了宦官毒殺皇帝、任意更換天子的局面。憲宗被身邊的宦官殺害后,大唐的命運就急轉直下、迅速墜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覆亡,其間偶有中興之光,卻再也無人可以力挽狂瀾,讓帝國重回盛年。
暮色將近,大廈將傾,唐王朝江河日下。
多年后,李商隱寫道:“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似乎可以從詩句中窺見一個帝國的命運。
或許,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命運,不可避免地被帝國的命運裹挾著,就像漠漠斜陽下的晚霞,滾滾逝水里的浪花。
從這滾滾逝水里,我們又將看到,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的名字,通常代表著另一個人秘而不宣的精神的寄寓。
如李商隱,或如千千萬萬人。
名于其人,可以是一根錚錚鐵骨,不負道義不負自己;也可以是一根刺,扎在“一生襟抱未曾開”的心頭。
名于其人,可以是一盞燈,為人生指引方向;也可以是一個魔咒,一生為名所累,就像西西弗斯永遠推不上山的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