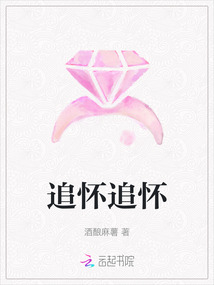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感情的事只需等待
這座城市剛剛度過漫長又潮濕的雨季,隨之而來的是熬人的酷暑,浸在蟬鳴里,卻眼見著要慢慢干涸。我把水杯正過來又倒過去,試圖制造一股風暴。紀鳴就透過這半透明的杯壁從細小的漩渦中向我走來。好像電影里被囚禁于黑暗里的獵物,正歇斯底里之時,超級英雄從天而降。至于他是因什么而來,已經不重要了。
直到現在,已經過去很多年,我還是會想起這個畫面。
因為不想要再次成為遺憾的主角,所以一開始我是想要用他人的名義來敘述的,就像一本小說,以至于多年后的自己再次閱讀到不會過于窘迫,但是紀鳴說,如果有可能,他還是愿意從頭再來一遍。
2020年秋天,我剛剛結束一段長達三年的戀愛關系,只身從墨爾本回國。在飛機上的這幾個小時,腦海里像走馬燈一樣,不停以倒序的形式循環播放著這五年里的點點滴滴,雙眼卻是疲憊的,只要想到顧西南就會覺得吵鬧。這種吵鬧讓我暈眩,像暈車暈船一樣,已經變成了一種生理不適。我已經不記得剛剛確定這段感情的時候我們彼此之前確認過什么,又另外做了什么承諾,以至于顧西南會像一塊嚼過了的口香糖一樣死死粘在鞋底,然后完美地和鞋底的凹槽融合在一起,他本人還不覺得突兀。
真的很病態。
曾經自己也是這樣病態。雖然不想承認。
從18歲到21歲,我將全部的熱烈投入到一個會用感情綁架和壓制自己的人身上,而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鋪張和毫無節制。
從高中談到大學畢業,我感覺自己長大了不少,但顧西南卻好像還是一樣,還是那個嬌生慣養的小孩,覺得世界都應該把自己當作中心,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多么的糟糕透頂。無論文學作品把愛情吹捧地多么純潔高尚,但事實是,不管是出于哪一種原因的愛,都是有條件的,或是才或是色,又或是金錢地位,情緒價值,不至于種種條件需要達到多么優越的程度,但也不至于讓對方認為你毫無優點。但和顧西南在一起的這三年里,兩個人逐漸走入感情的死胡同里,又像是兩個人手腳束縛在一起墜入深海。
他常常讓我感到我們并沒能令彼此變得更好,反而一次次地陷入無盡的內耗之中。
那么這樣下去必定會有一個人覺得很疲勞很受傷。
于是某次爭吵過后,我突然清醒過來,一改往日的擰巴,決定不再死磕下去。
“我們分手吧,我要回國了。”
“你說什么?”
在這句話脫口之前,顧西南的目光和意識都游離在話題之外。這是他自己既定的相處模式,從開始嘗試到真正實施不超過熱戀期的兩個月,關系剛穩定下來時他就聰明地察覺到這種模式屢試不爽,并且這段感情自己占據上風。江暖愛我,離不開我,那么她就活該要聽從我。
“我說,我們分手吧。”
我深吸一口氣,一字一頓地重復。
意識到我并不是在開玩笑之后,顧西南從沙發上站起來,眼神由震驚轉為憤怒。三步并兩步地沖過來單手掐住我的脖子,惡狠狠地問我是否已經想清楚。
我感覺心臟正急速地在胸膛里跳動,但此時此刻能做的只是面無表情地和他對視,這是唯一一次,或許也是最后一次在這段關系里占據上風。
我低下頭看著顧西南纖細修長的左手,此刻因為憤怒而血管擴張,一條條青筋像縱橫的溝壑夸張地橫在上面。
那只手上戴著去年生日我送他的情侶戒。
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叫莫比烏斯環。寓意無盡的愛。
不論從哪里開始,都能重新與你相遇。
這是我用來墨爾本讀書之后得到的第一筆獎學金買的。本來這筆錢剛下來時,計劃買一副新的助聽器,可是恰逢戀愛周年紀念日,我猶豫了一整天,還是決定用這筆錢來紀念愛情。
我記得當時我說:顧西南,我會永遠愛你。表情誠懇。
只是沒想到這也變成了落下的話柄,我們倆心里的一根刺。
“你有沒有想過,除了我,還有誰會把你保護得這么好?”
保護。
我覺得諷刺。這幾年只要同居,顧西南的內褲都是我手搓的,他就這樣坦坦蕩蕩地臥在沙發里刷微博動態,換洗衣物丟了一地。從前有情飲水飽,哪怕吃糠咽菜也覺得是為愛情付出,但突然有天我就開始對著滿手的泡沫發怔,內褲上隱隱的氨味讓人忍不住干嘔,我回頭看了眼顧西南,突然意識到我倆之間的這些年,痛苦是比幸福要多得多的。
我很怕他會一時沖動做出傷害自己的事情,但我知道隱忍是沒有盡頭的。面對望不到邊的未來,需要適時地勇敢一下。
于是我沒再說話,只是用力地點點頭。
顧西南愣了愣,然后大聲咆哮:
“我,除了我,誰還能把你保護得這么好?”
五分鐘之后,我被揪著頭發扔出了公寓。甚至沒來得及收拾行李。墨爾本的秋天很愛下雨,風也大,牛仔褲沾了水,緊緊貼在皮膚上。我唯一的一件風衣還掛在臥室的衣柜里,顧西南說這是他過年帶我回家的時候在長沙萬達買的,屬于他的私人財產,手機里還有消費記錄。于是我只能衣著單薄地拎著好朋友徐度送的行李箱站在公交站等車,眼前的這些就是我的全部家當。加上一臺屏幕剛剛被他摔碎的三星手機。
這個狼狽不堪的畫面,我在之后很多很多年都沒能忘掉。
那天雨下得很大。在等車的半個小時里,我已經漸漸喪失拿定主意的能力,好在兜里還有昨天在便利店買東西找的幾枚硬幣,于是沒有目的地地坐了幾站,在確定顧西南沒有跟上來之后才壯著膽子下了車,用公用電話打給徐度。
“江暖你****為啥不接電話?你***”
徐度是我關系最鐵的哥們兒,從幼兒園到大學,從江寧到墨爾本,幾乎是一路互相扶持過來的,只是我命中有一劫,看上了瘋起來像野狗一樣的顧西南,徐度縱然想繼續保護我,也會被他們之間的關系隔絕在外。
剛接通,我全家就被集體問候了一遍。
“誒,停停停!”
我緩了口氣,不疾不徐地向他公布這條喜訊,
“普天同慶,我下個月準備回國了。”
“什么意思?”
電話那頭明顯地停頓了一下。我知道徐度能明白,只是想聽到確切的答復。
“我和顧西南結束了,我要離開墨爾本了。”
“你在哪?我來接你。”
二十分鐘后,一輛白色斯巴魯停在我面前,徐度緩緩降下車窗。
“來得還挺快。”
我朝他招手,三步并兩步跑進車里。
徐度卻無心打趣,下車把行李塞進后備箱。
“又被他趕出來了?”
“嗯。”
這是最后一次。我在心里暗下決心。我是戀愛腦,但我可不是受虐狂。
徐度看看我,沒有再多問,只是抬手把空調溫度打高。從小到大,他都是最會照顧我情緒的人。我屬于很容易破防的那種性格,脆弱而不自知,每每遇到這種情況,徐度就會再三告訴我,不必強顏歡笑。
“我就說你倆不合適,你倒好,硬要吊死在一棵樹上。”
徐度和顧西南接觸不多,但卻對這個人的印象極其不好。記憶我和顧西南談戀愛的這三年里,他們正兒八經地坐下來吃飯聊天只有四次,有三次都狠狠戳中了徐度的雷點,用徐度本人的話來說,就是有違自己做人的原則。我一直以為道不同不相為謀,這正常得很,直到后面復盤起來才覺得非常離譜。
“我這不是幡然醒悟了。”
顧西南不能說人品惡劣,但為人真的非常霸道和奇怪。他們剛到墨爾本的時候還沒有同居,顧西南和在國內高中時期就認識的好朋友合租,而我住在學校宿舍,周末沒有課的時候才會偶爾過去小住兩天。剛開始一切都很正常,直到小半年之后才讓人感到有點奇怪,每次我去的時候,那位室友都不在家里,而且是一整個周末都不見人影。后來顧西南自己說漏了嘴,事情的真相是他和室友約法三章,周末我來的時候,室友都必須出去住,不準回家。
從此之后,我再也沒有去顧西南那里住過。即使是他再三邀請,亦或是疫情那年的除夕,我也沒有再去過。
相對于室友超高的隱忍力,我更加驚訝的是,為什么顧西南身邊可以充斥著如此多的受氣包和窩囊廢。
這段感情于是從耿耿于懷的耿,變成了梗,顧西南這兩天在微信里給我發了至少三次長達八百字的小作文,淋漓盡致地表達了他的懊悔,以及改變自己的決心,但我一直沒有看,也沒有把他拉黑。因為我知道,以顧西南這種偏激的性格,如果我這樣做,那么這幾天他掘地三尺都要找到我,暫且這樣讓他感到一線希望,對彼此都好。
顧西南或許會疑惑我為什么就這樣很突然地提出分手,甚至懷疑是否有他人介入的可能,但他從始至終沒有看到我的隱忍,我也不愿意再去向他做過多的解釋,畢竟一段感情走到這個地步,沒有人再需要一個說法了。
一直到送我上飛機之前,徐度還不忘揶揄道:“小沙包,你就先別談戀愛了,等我幾個月。這里的事情處理完我就回江寧去。”
“也沒有人當沙包當上癮的。”
對于徐度拋出來的話題,我只是裝傻地不置可否,只朝他做個鬼臉,然后頭也不回地走進登機口,亞麻色的短發在徐度視線里晃啊晃,晃成一片氤氳的灰。
本來我的原計劃就是結束學業之后就離開澳洲,我不喜歡老外的那一套相處方式,也有可能因為性格就如此。但總而言之,我知道自己的理想和未來并不在這里。現在和顧西南分開,終于不再有任何顧忌,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情,不再需要為任何人犧牲,想想就令人身心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