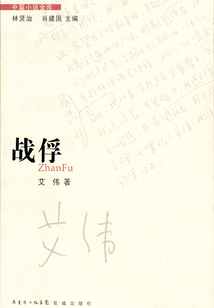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總序
在中國,“小說”一詞使用已久,最早見于《莊子》,《漢書·藝文志》說是“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之所造也”。小說的雛形是神話傳說中的簡略記錄,后來發(fā)展到《搜神記》一類志怪小說和《世說新語》一類志人小說,結構都很簡單。及至出現(xiàn)唐人傳奇,宋元話本,小說乃由粗具梗概變得枝繁葉茂起來。魯迅指出:“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就是說,小說創(chuàng)作的自覺意識到這時方始建立,結果是:小說有了中篇的規(guī)模,題材有所擴展,最突出的是情節(jié)性大大加強,而語言也趨于通俗,更富表現(xiàn)力。明初《三國演義》、《水滸傳》的制作,標志著古典小說趨向成熟;隨著清代《紅樓夢》的出現(xiàn),達至巔峰狀態(tài)。盛極而衰,緊接著,變革時代也就適時而至了。
宋元“說話”中有一類名為“小說”,指的是話本中的短篇故事,與我們現(xiàn)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遠。我們說的“小說”,實際上是晚近的舶來品,可以說,是由歐洲的小說觀念再命名的。
在歐洲,小說發(fā)展的道路與我國大體相似,即由神話而傳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長篇。至十九世紀,長篇小說十分鼎盛,致使黑格爾斷言極限來臨。及世紀末,現(xiàn)代主義小說很快出現(xiàn),傳統(tǒng)的主體和寫法被打破了。其實,十八世紀末以前,歐洲小說的體式已經(jīng)相當完備,只是小說之名(novel)遲至此時才正式流行起來罷了。
幾乎與此同時,有了中篇小說(novelette或n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說是中型的敘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長短劃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當?shù)膹椥裕枰阉鶖⒌氖录囊?guī)模、時間長度、結構的復雜與完整的程度同時作為參照。綏拉菲莫維奇的中篇《鐵流》,論結構,可以算作長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長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維亞卻是把它當做注水的短篇來看的。
五四新文學運動把中國文學分為前后兩截。語言由文言改成白話,表面上是語言層面的改革,實質上是一場帶根本意義的文學觀念的革命。胡適寫《白話文學史》,所說的白話,仍是古典的白話,與五四時期語法相當歐化的白話很不相同。五四的小說,一、凸顯文學的主體性,叛逆性,個性解放與人道主義成為小說的主旋律;二、題材和主題有所擴展,社會問題進入小說,“神圣勞工”及知識分子形象組成了新的人物畫廊。三、小說結構基本上是西式的,塊狀的,自由組合的,而非線性的、連環(huán)組接的傳統(tǒng)章回體。除了思想觀念,還有形式技法,都是現(xiàn)代的,面向西方,學習西方,而有了東方式的創(chuàng)造。
現(xiàn)代小說仍以短篇小說先行,幾年后,中長篇相繼產(chǎn)生。1922年,魯迅的《阿Q正傳》正式發(fā)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納了一個革命的時代,統(tǒng)攝了一個民族的靈魂,這確實是一個奇跡,尤其出現(xiàn)在新聞學的發(fā)軔期。當時,郁達夫、廬隱、廢名等都有中篇問世,但多流于粗淺。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掙脫自敘傳性質而面向廣大的社會面開拓,開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長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鋪子》、《春蠶》反反映中國社會的變動。鄉(xiāng)土題材聚焦了眾多作家,蕭紅、沈從文、王魯彥、吳組緗、沙汀,還有廢名,都有相當數(shù)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場》和《邊城》,或凄厲,或幽婉,更富有鮮明的藝術特色。左翼作家蔣光慈、葉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爭的中篇,對于充斥著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著“大團圓”結局的傳統(tǒng)小說來說,本身也不失為一種革命。其中,蔣光慈較早揭示革命與人性的沖突,并因此遭到內部批判,作為文學史上的一個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寫大時代里的邊緣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顧惜,是另一種筆墨。丁玲從《莎菲女士的日記》到《水》,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宿命般的顯示了中國現(xiàn)代作家群體角色的演變過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等,不重現(xiàn)實而重審美、重感覺、重印象、重情調,以中產(chǎn)階級趣味烹制都市文學。在此期間,巴金、老舍、張?zhí)煲矶际怯杏绊懙男≌f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來寫的《憩園》,一種挽歌調子,似乎與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頗異樣。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學是一種新型文學,但實質上,在“為政治服務”和“為工農(nóng)兵所利用”的背后,卻混雜了不少傳統(tǒng)主義、民粹主義的因素,意識形態(tài)代替了個人思想,形式——所謂“民族形式”——比較單一。趙樹理小說《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在當時可以看作是一種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間,丁玲的《在醫(yī)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時候》,對個人理想和女性主義作最后的堅持,可謂彌足珍貴。在“國統(tǒng)區(qū)”,包括抗戰(zhàn)時的“淪陷區(qū)”,張愛玲寫下《金鎖記》、《傾城之戀》,以第三只眼看人世,著意經(jīng)營現(xiàn)代傳奇。還有師陀,他的《落日光》、《果園城記》,在藝術上非常講究,很有特色。青年路翎異軍突起,寫作《饑餓的郭素娥》,從形象、情節(jié)到語言,則明顯帶有一種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小說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識分子一樣,經(jīng)歷了長達三十年的思想改造過程;而創(chuàng)作,隸屬于這一過程而基本上成為被改造的產(chǎn)物,一些著名小說家停止了小說創(chuàng)作,如進入領導階層的茅盾、巴金;而沉默,如沈從文;而改變作風,如老舍。“解放區(qū)”作家一路高歌猛進,柳青的長篇《創(chuàng)業(yè)史》名重一時,還有趙樹理的《三里灣》、《鍛煉鍛煉》等,;然而到了后來,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這樣的語境中產(chǎn)生的小說,主題基本上是“寫中心”的,因此很難具備優(yōu)秀的品質,中篇的數(shù)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現(xiàn)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題有所開拓。其中,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是有代表性的。年輕作者是嚴肅的,敏銳的,小說揭露官僚主義者的丑惡,閃耀著一個“少布”的理想主義的光芒。宗璞的《紅豆》,忠實于對校園知識分子愛情生活的描寫,無意中涉入禁區(qū)。但是,這些頗有“離經(jīng)叛道”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銷聲匿跡。像路翎、丁玲這些出色的小說家,在“肅反”及“反右”的斗爭中,先后遭到整肅,給中國文學帶來很大的傷害。
至七十年代末,一場浩劫過后,社會思想包括文學思想活躍一時,一批作家解除了荊冠,恢復了寫作的權利;另一批青年流放者從農(nóng)村歸來,正式練習筆耕,小說家隊伍于是迅速壯大。這時,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讀物及文學經(jīng)典,包括現(xiàn)代小說被介紹進來,大型文學刊物紛紛創(chuàng)刊,這就給中篇小說的繁榮準備了溫床。
繼“重放的鮮花”之后,一批帶有創(chuàng)傷記憶的作品問世,其中有《天云山傳奇》、《犯人李桐鐘的故事》、《大墻下的紅玉蘭》、《綠化樹》、《一個冬天的童話》、《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敘述知青生活的小說不斷涌現(xiàn),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數(shù)把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當成一場人生劫難來描寫,像張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駿馬》這樣作積極的浪漫主義的回顧,表達對土地和人民的靈魂的皈依者為數(shù)極少。王小波屬于明顯的異類,他的《黃金時代》表現(xiàn)“文革”的禁錮與荒誕,想象大膽、奇特,在形式上具有很大的獨創(chuàng)性。至于阿城的《棋王》,體現(xiàn)一種道教傳統(tǒng)文化的逍遙心態(tài),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說開始向現(xiàn)實生活掘進,一類著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寫技術知識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寫農(nóng)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類傾力表現(xiàn)中國面臨的社會變遷,包括農(nóng)村的責任承包,城市的企業(yè)改制,等等。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和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可以作為代表。此間,一批描寫民俗,表現(xiàn)人性的作品出現(xiàn)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等,另外還有一些無法歸類的小說。
比起三十年前,這個時期中篇小說的數(shù)量陡增,題材變得更加豐富多樣,然而在主題的發(fā)掘方面,多滿足于形象地復制意識形態(tài)結論,整體風格“溫柔敦厚”,缺乏作家個人判斷的獨立性和社會批判的深刻性。關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長期以來形成的“歌頌”與“暴露”二元對立模式,對現(xiàn)實中的黑暗面、矛盾與沖突的復雜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觀意識往往與現(xiàn)存秩序相妥協(xié)。即便如此,喧嘩一時的中篇小說,仍然顯示出為五十年代以來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說界的風氣很快便宜了被稱作“思想解放運動”時期所確立的關于人的歷史命運的悲劇主題,出現(xiàn)了一種形式主義的傾向。在此期間,有兩大創(chuàng)作現(xiàn)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尋根文學”,即從現(xiàn)實生活中尋找人類學、文化學的源頭。從表面上看,“尋根”是現(xiàn)實問題的深化,實際上大多數(shù)作品都脫離了現(xiàn)實政治,否棄了對現(xiàn)實體制的實質性追詢,公式化、符碼化。王安憶的中篇《小鮑莊》,在國民性的探尋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飽滿的汁液,指著一路的文學中少有的佳作。還有一個現(xiàn)象是“先鋒小說”,皆在形式上做實驗,內容相對單薄,有不少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贗品。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個別小說活躍著新的思想元素,如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徐星的《無主題變奏》;但是大體上,這些實驗小說頗類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領異標新,多少豐富了中國小說的敘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說整體乏善可陳。當此艱難時世,有人倡言“新寫實主義”。“躲避崇高”,“分享艱難”。應運而生的這一類小說,可以說是正統(tǒng)文學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確,藝術追摹宏大;個別作家貌似解構正統(tǒng),如王朔,實質上是一種“別裁”,一種補充。由于有著各種權力資源的支持,潛在勢力是雄厚的。但這時,一種相反的文學趨勢也起來了,就是所謂的“個人化敘事”。敘事的個人性,在這里竟成了反社會的一個遁詞;正如有人標榜“女性主義寫作”,卻置換了整個源自西方用語中的自由、平等這樣帶政治學、社會學的內容,而從事個人題材的寫作,瑣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滿色情描寫。此時,又有所謂的“新生代”群體順次登場,批評家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瀾,呈崛起之勢。其實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會生活方面的體驗,也缺乏文學訓練,浮囂有余而堅實不足。
新世紀以來,又有人提出“底層文學的口號”。倘若能夠正視現(xiàn)實,關注底層,對于有著幾千年“瞞和騙”傳統(tǒng)的中國文學來說,應當是一種根本的轉變。但是,以我們的作家目前的素質和狀態(tài),要高張并堅持一種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精神,并非輕而易舉的事。一些被稱為“大腕”的人物繼續(xù)編造冗長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難”作題材,也是隨意編織材料,違背生活邏輯;而且在主體方面,也缺乏起碼的誠愛與同情。作品的“酷”,不僅僅在于技術上的冷處理。具有一定的底層生活經(jīng)驗的作者,作品大多顯得粗糙,因此在總體上比起八十年代,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不見得有長足的進步。較為優(yōu)秀的作品,有尤鳳偉的《小燈》和林白的《回廊之椅》,兩者對土改歷史都有顛覆性的敘述;描寫礦工生活的,有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農(nóng)村題材的,有劉慶邦的《到城里去》,胡學文的《命案高懸》,以及徐則臣寫農(nóng)民工的“北漂”系列小說。另外,像薛藝溈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鐘晶晶的《第三個人》,則以其哲理性和詩性,在眾多以故事性見長的小說中顯出一種罕見的雜色來。
近百年間,中篇小說從題材、主題、體式、技巧等各個方面,不斷地有所開拓,有所發(fā)展。但是,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現(xiàn)象是,最早出現(xiàn)在現(xiàn)代小說上的《阿Q正傳》,至今仍然是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說來,當代小說雖然在敘述故事和刻畫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對顯得嫻熟,但是,藝術個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現(xiàn)在文學語言本身,就缺少個人筆調;在現(xiàn)實生活中,長期的集體主義教育,使個人性受到遏制,或許是根本的原因。同時,語言也缺少優(yōu)雅的氣質,缺少精致,缺少韻味,這同長期推廣“工農(nóng)兵文藝”,以文學為政治宣傳的工具不無關系;擴而言之,同漢語語境遭到破壞,同整個社會語言的粗鄙化有關。在形式上,中國小說滿足于講述故事,講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說的那種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說的繁榮,從根本上說,有賴于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文學的繁榮。道路是漫長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嘗不可能說是開闊的。單就現(xiàn)代小說發(fā)展來說,從五四到現(xiàn)在也不過是一百年的歷史,具有經(jīng)典性價值的作品極少,而真正堪稱優(yōu)秀的作品也不會很多。在此,我們編選了這套《中篇小說金庫》,旨在集中這類具有較高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過來,也可以充作進一步滋養(yǎng)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份泥土和養(yǎng)料。需要說明的是:其中有個別作品,編者并不認為屬于最優(yōu)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認,它們自問世之后在文學界和讀書界中造成的影響,從文學社會學的意義上考慮,這也未嘗不可以算作是一種“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金庫》分輯陸續(xù)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評家、文學史家及廣大讀者的大力推薦,以確保它作為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一個文本系統(tǒng)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