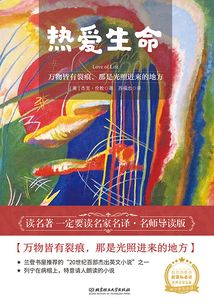
熱愛生命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名家導讀
2016年是杰克·倫敦去世一百周年,就我目力所及,無論紙質媒體還是網絡,沒有看見一點紀念他的跡象,好像這個曾經讓美國出版商哄抬版稅的作家不曾存在過似的。不過,這只是健忘的文人學者們的表現,普通讀者卻不會這樣,至少中國的讀者對這位很會寫故事的作家念念不忘,他的小說一直暢銷,就是最好的紀念。
1896年,加拿大的克朗代克河發現金礦,美國掀起了一股席卷全國的淘金熱。對掙扎在經濟大蕭條底層的杰克·倫敦來說,這是一次發財的機遇。在姐姐伊莉莎的支持下,他懷揣發財夢加入了這支淘金隊伍。漫漫的原始森林、茫茫的雪原、貧瘠的荒原、激流與險灘、高山峻嶺和懸崖峭壁,他一路走來,千辛萬苦,到達了阿拉斯加的道森小鎮。然而,淘金不是人人都能發財的,杰克·倫敦的財路不在淘金隊伍里,他注定要靠寫作實現夢想,因此他在淘金熱中聽到的關于這一活動的故事,是他淘到的遠比金沙還珍貴的創作資源。
關于這些故事的寫作,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家界定為他的“克朗代克故事”,后來統稱為他的“北方故事”。
他的這些短篇小說從所寫人物上來分類,倒是很容易的:印第安人的生活狀況和淘金者的謀生狀況。
在描寫印第安人的短篇中,《趕路的智慧》《北方的奧德賽》《生活的法則》《父輩們的神》《老人的聯盟》和《波波塔克的智慧》等篇,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如《趕路的智慧》寫印第安人希特卡·查利因為弄明白了白人維持社會的法則,把這一法則運用在本族人身上,比白人還在行,他成了白人爭相雇用的印第安人。在一次趕路的途中,他的兩位挨餓的同胞因為偷吃了幾杯面糊,在法則面前只能認栽,由他親自槍殺,因為趕路人都明白一個團隊必須有規矩,法則是為了成就未來,犧牲當下。這里的趕路智慧其實是強權。什么是強權?也許就是誰手里持有一支步槍。希特卡·查利為了能管住為白人服務的本族人,他上路前讓他們把槍都卸掉了,這是他的心機,算不得什么智慧。如果這種心機能算作智慧,那只能說別的印第安人腦子太簡單,簡單到愚蠢。這顯然不是作者要告訴讀者的。印第安人服從法則,敢于擔當,甚至搭上性命,因為對于狩獵民族來說,食物永遠是第一位的。
《生活的法則》肯定了印第安人亙古以來遵循的一種生活法則。這個故事的吸引人之處,在于一個慣例:饑荒來了,印第安人營地周圍沒有了獵物,他們必須追尋獵物的去向而遷徙,成了拖累的老人不得不被拋棄,了卻殘生。這老人曾經是酋長,是強者,引領過一族人,而目前陪同他的只有一個火堆和一小堆木柴。木柴燒完了,餓狼沒有了對火的懼怕,就會圍上來把他吃掉。吃不是問題,保持火旺旺的才是問題。一個人一天只要吃一頓就能不死,但火堆一個小時甚至半個小時不續柴火就會熄滅。老人等死等得讓人不勝唏噓。兒時聽到的這則“知死不知生”的故事已夠精彩,但遠不如這篇短篇小說,它以火為切入點,寫出來讓讀者更為垂死之人擔憂。而“火”在這里又指向人類走向文明的象征物,從而讓人聯想到印第安人的生存尚處在一種原始狀態;他們逐漸地向白人文明靠攏,是他們順從了自己活下來的方向,大勢所趨,如同當今的年輕人紛紛離開農村奔向城市。
《老人的聯盟》從印第安人遭受白人侵擾的角度寫起,老人們結盟反抗,英勇而頑強,但是他們只是孤獨求敗,因為青年男人都不跟他們結盟,他們無以為繼。他們的反抗很悲壯卻無希望,因為決定他們反抗能否前仆后繼的關鍵是物質條件而不是精神信仰。不過,有沒有依靠精神信仰反抗白人的印第安人精英青年呢?
有,《祖先們的神靈》就在回答這個問題。海·斯托卡德是一個混血兒,母親是印第安人,父親是英格蘭人。種種因素迫使他遵循了印第安人的習俗和信仰,娶了印第安女人為妻。他誓死捍衛印第安人的信仰,但擋不住更多的印第安人聽信白人傳教團的說法,他只能孤注一擲。小說涉及了兩個種族的混血問題,既寫人生來對種族所屬都有本能的感覺和認同,又寫世俗和社會對個人的身世并不真正關心,而是只會改造個體。作者相信肉體的力量,也相信精神的力量不可忽視,但兩種力量的和諧相處則要困難得多。一個人可以把這兩種力量集于一身,不屈不撓地去斗爭。
杰克·倫敦的成名作《北方的奧德賽》寫混血兒納斯,在白人引發的印第安人冤冤相報的復仇斗爭中,成了一個部落的唯一男性繼承人;另一族,即敵對勢力,唯一的繼承人是一個姑娘,名叫央加。納斯十七歲時,和央加情投意合,決心娶央加為妻,結束祖祖輩輩的復仇活動。在他結婚的晚上,海上來了一艘觸礁的船,船修好后,船長“黃頭發”阿克塞爾·岡德森看上了央加,用酒把納斯灌醉,把央加劫持到了船上,開船走了。納斯受盡了非人能承受的苦難,終于在北極地區的道森小鎮遇上了阿克塞爾·岡德森和央加。但是央加已經習慣了白人的生活,愛上了阿克塞爾·岡德森,不僅不跟他回到族人身邊,還用刀刺傷他,和阿克塞爾·岡德森抱在一起,凍死在白茫茫的雪野。一場大海撈針的追尋落得這樣可悲的結局,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了。他做了希臘神話英雄奧德修斯所能完成的使命,但結果讓他迷失,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里。有評論說這篇小說寫杰克·倫敦對印第安人的同情,但杰克·倫敦更明白面對人性的復雜,誰能同情得起一個種族呢?
《波波塔克的智慧》似乎就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而寫的。波波塔克是印第安人中的資本家,通過淘金活動積累了很多錢。他慷慨地借錢給印第安人酋長克拉基—納赫,讓他去花天酒地擺一個老貴族的排場。克拉基—納赫坐吃山空,欠了波波塔克一大筆債。他債務還不上,波波塔克說他的千金艾爾—蘇多少債務都能抵得上,如果她做了自己的妻子,所有債務一筆勾銷,但艾爾—蘇發誓不從。為了不讓誓死不從的艾爾—蘇再逃走,波波塔克開槍打爛了她的腳脖子,然后把艾爾—蘇交給了她的戀人阿庫恩。殘忍嗎?很殘忍。對美和青春的摧殘冷酷嗎?很冷酷。但這是印第安人認可的習俗和原則,是一個古代社會和現代文明碰撞后畸形發展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杰克·倫敦讀書龐雜,接受的觀念一定比較紛雜。他底層的出身讓他的寫作多從同情弱者的角度入手,他所接受的紛雜的觀念讓他的寫作難免有概念化的痕跡,他聽來的各種故事讓他必須利用豐富的想象力另辟蹊徑;然而,他復雜的人生經歷卻讓他的寫作每每回歸到人性的復雜和生命的本質上來。印第安人和白人都是人,七情六欲總是第一性的,不論發生多么激烈的沖突,人性都是最終的決定因素。
當杰克·倫敦有力的筆伸向淘金隊伍里的白人時,白人的原始性令人著迷,而原始性中的冷酷無情則令人觸目驚心。極端的環境必然有極端的表現,能在極端環境里自律、守住良心和道德底線的,在杰克·倫敦的筆下,不是鳳毛麟角,便是根本不存在。弱者經不起同情,強者經不住贊歌,杰克·倫敦只能把人的行為交給進化論。進化的核心是為了生存,首先是個體的生命要得到延續,然后是他人的生命的延續,如孩子、妻子和伙伴。
《為趕路的人干杯》寫一個名叫威斯通戴爾的趕路人,他先被別人算計,后不得已進行搶劫。眾人知道了真相,一致同情他,因為趕路人是為了愛妻和孩子,為了溫馨的家。在對家庭的責任面前,依法行使權力的警察反遭無視。淘金人群無法無天,但有行規,這樣的行規必須利于個體生存。
《白茫茫的寂野》里則表現另一種規則:三個人坐著雪橇穿行在茫茫林海里,其中一個突然被一棵倒下的大樹砸成重傷。他們的干糧只能吃到走出林海,多耽擱一天就意味著他們再也走不出林海。受重傷的男子要求伙伴開槍把他打死,趕上雪橇把他妻子帶出林海,因為他妻子的肚子里還有孩子。求生的條件營造得無可挑剔,犧牲一個垂死之人而救下三個,是生存法則允許的:不僅友誼可以因射殺得以加強,而且生命的延續要求必須這樣做!極端環境里只能用極端的解決方式,假若換一種方式,比如偷懶耍奸、茍且偷生又如何呢?
《在那遙遠的地方》可以說寫到了這樣一種生存方式。在茫茫的雪野淘金,白忙活一場,還錯過了回去的最好時機,是勇敢地返回去,還是在北極的黑暗中茍且一冬?勇敢的人都選擇了回去,而兩個“窩囊廢”留了下來。這樣的懶蟲注定只想沾別人的光,因此等到一方不經意間多吃了另一方的食糖時,你死我活的格斗在所難免。一方手持斧頭,一方緊握手槍;持槍者開槍打中對方的臉部時,揮舞斧頭的用斧頭砍中了對方的脊梁骨。中槍的速死,挨斧頭的慢死,生命的結束讓人震驚和思索:生命只有在運動中才有活力,饞吃懶做只是等死。不同的生存態度導致截然不同的生存結果。起碼的生存要求起碼的生存本能。人性在這里必須為生存所用,一旦違背這個規律,就只能是惡劣的獸性爆發。人與人之間如此,人與狗之間也如此。
從內容上看,《巴塔德》的內容好像是寫人與動物的關系,實質上是寫在生命的生存狀態中,無論人性和獸性,善與惡應該占據什么位置。巴塔德是一只雜種狗,碰上了一個狗雜種人,狗與人的關系演變成了以惡制惡的惡性循環。狗受盡百般虐待,人遭到百般抵抗。狗自以為強大時,和人公開較量了一次,以慘敗結束,狗明白了人之所以強大是因為人能利用工具——鞭子和棍子。但是,狗為了基本生存而表現出來的兇惡,是不可征服的,因為這是它的生存底線,它放棄這一底線,就會死掉。它可以受盡主人的各種折磨,但就是不能逃走,因為一旦逃走,它的饑飽就沒有了保障。巴塔德復仇的機會是人性的復雜導致的復雜局面提供的,它抓住了復仇的機會,把惡人主子親自送下地獄,哪怕搭上自己寶貴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熱愛生命》這篇小說,閱讀過杰克·倫敦的作品的人,無人不知。弱肉強食、生命頑強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底線,小說都有涉及,但小說的核心仍會被人忽略:人的生命靠食物維持,食物問題永遠是第一位的。小說的結尾寫“這個人”幾個星期里一直向人乞討餅干,床上和口袋里裝滿了還在討要,看似多余,其實是作者的特別用意:生命離開食物,什么都不是。生命延續之殘忍,是生命必須用另一個生命的蛋白質維持,因此這個人在最后的關頭必須咬開那只餓狼的喉嚨,喝到它的血。看似不可能的情節,其實包含著必然。
純粹的與極端環境抗爭的短篇,在杰克·倫敦的寫作中,數量不是很多,能成為膾炙人口名篇的更少,而《攏火》算名副其實的一篇。當初發表就贏得了廣大讀者的欣賞,后來一直為眾多選本所青睞。故事里的“這個人”帶著一只狗,雖萬般小心卻還是蹚到了雪下水坑,在這樣極端寒冷的天氣里淹泡一次就意味著死亡。從此冷凍開始和他的自救賽跑,看似緩慢的冷凍,步步搶先在他攏火的每一步之前:他冰凍的手指捏不住火柴,他用牙齒咬著劃;劃著一根火柴卻沒法點燃火堆,他改用兩只手的根部夾住火柴一次劃著了一束七十多根,把手掌燒焦了還是沒有把火點著。他企圖把狗整死,把手戳進狗肚子里取暖,卻連殺死狗的力量都被冷凍住了。他幻想著伙伴們來救他的美景,經過一系列的痛苦掙扎,死到臨頭時突然有了愉快感、舒服感。攏起一堆火,在這里不只代表著一個技術,還成了一種象征。人類發明火純屬偶然,但使用火、利用火卻成為走向文明的必需之物。讀者從故事中看到的不只是“這個人”,還有讀者自己。這就是杰克·倫敦的小說長久不衰的生命力。
杰克·倫敦的北方故事發生在北極附近,寒冷是其最顯著的特點。天冷、地冷、生命冷,連他的用詞都冷,因此把生命和人性寫出了硬度和韌性。他講的故事情節冷氣如煙,讓當今的讀者不禁體味到在美國很時髦的一個英文詞cool的俚語含義:極好的,絕妙的,酷的。
蘇福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