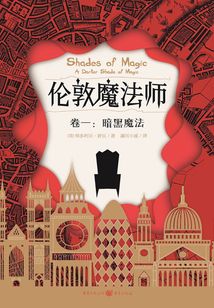
倫敦魔法師(卷一):暗黑魔法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旅者
Ⅰ
凱爾的外套殊為罕見。既不是尋常的單面,也不是出人意料的雙面,而是好幾面——確實,這太不可思議了。
每次他離開一個倫敦,走進另一個倫敦,第一件事就是脫下外套,翻個一兩次(甚至三次),找到他需要的那一面。不是每一面的樣式都稱得上新潮,但它們各有用途。有的使他平凡無奇,有的令他脫穎而出,有一面則沒有什么功能,卻特別討他喜歡。
當凱爾穿過宮墻,來到候見室,他休息了好一會兒——在不同世界之間移動是有代價的——然后抖下身上那件紅色高領外套,從里到外、從右往左地翻過來,使其變成一件純黑上衣。好吧,是一件繡著銀線以及兩排锃亮銀扣的純黑上衣。他每次外出都選用低調的服色(既不愿意冒犯當地貴族,也不想引人注目),但并不意味著連品味也要舍棄。噢,國王們,凱爾一邊扣上扣子,一邊想著。他和萊的想法越來越像了。他穿墻的痕跡朦朦朧朧,依稀可見。如同沙地上的足印,正在慢慢消退。
他從來不在這邊的門上作記號,因為他不會原路返回。溫莎與倫敦相距甚遠,著實不方便,而凱爾只能在不同世界的同一個地點穿梭。所以問題來了,紅倫敦的一天路程之內壓根就沒有溫莎城堡。實際上,凱爾剛剛是從一位富紳的院子里穿過來的,那兒是一座名叫迪杉的鎮子。話說回來,迪杉是個舒適宜人的地方。
溫莎則不是。金碧輝煌是事實。但并不舒適。靠墻有一方大理石臺子,盛著一盆水供他使用,一如既往。他洗凈了手上的血,以及過路所用的銀幣,然后把繩子掛在脖子上,又把銀幣塞進領子里。他聽見前面的廳堂傳來雜亂的腳步聲,還有仆人和侍衛的低語。他選擇候見室就是為了避開他們。他非常清楚攝政王很不喜歡他來這里,凱爾也不希望被人看見,讓一大堆耳目把他來訪的細節匯報上去。
臺盆的上方掛著一面金框鏡子,凱爾迅速檢查了一番自己的儀表——紅棕色的頭發搭下來,遮住一只眼睛,但他并未費心打理,而是仔細地整平了肩部的衣褶——然后推開房門,去見這里的主人。
房間異常悶熱,盡管這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十月天,門窗依然緊閉,壁爐里的火燒得正旺。喬治三世坐在爐火邊,長袍裹著枯瘦的身子,茶盤擱在他膝前,卻不曾動過。凱爾進來時,國王抓緊了扶手。“誰在那里?”他頭也不回地喊,“強盜還是鬼魂?”“鬼魂怕是不會回答您的,陛下。”凱爾應道。
病懨懨的國王森然一笑。“凱爾大師,”他說,“你害我等得好苦。”“還不到一個月。”他說著,走上前去。
喬治國王瞇起了失明的雙眼。“不止,我敢肯定。”“我保證沒到。”“也許對你來說沒到,”國王說,“但時間對于既瘋又瞎的人而言是不一樣的。”
凱爾笑了。國王今天的狀態不錯。這種情況并非經常能遇到。對于面見時國王處于哪種狀態,凱爾根本沒譜。也許使他感覺不止一個月的原因是,上次凱爾來訪時,國王的狂躁情緒著實難以平復,導致凱爾沒能完成帶信的任務。
“也許年份變了,”國王接著說,“月份沒變。”
“啊,但年份是一樣的。”
“是哪一年啊?”
凱爾皺起眉頭。“一八一九年,”他說。喬治王臉色一沉,搖了搖頭說了聲“時間”,仿佛這個詞是萬惡之首。“坐,坐吧,”他揮揮手,又說,“應該還有一把椅子吧。”其實沒有。房間里空空蕩蕩,而且凱爾相信房門只能從外面開關,里面是做不到的。國王伸出一只粗糙的手。戒指已摘下,避免他傷到自己,指甲剪得極短。“我的信,”他說。一瞬間,凱爾仿佛看到了曾經的喬治,那個威嚴的君王。
凱爾拍了拍外套口袋,這才發現在翻面之前忘了掏出信來。他脫下上衣,又換回紅色,在里頭摸索了一番。他把信遞到對方手里,國王愛不釋手地摩挲著封蠟——那是紅王室的紋章,圣杯和旭日——然后將信舉在鼻子前嗅了嗅。
“玫瑰。”他戀戀不舍地嘆道。
他說的是魔法。凱爾從未注意過衣服上沾有紅倫敦的淡淡芳香,但每一次穿梭都有人告訴他,他聞起來就像剛摘下來的鮮花。有人說是郁金香,有的說是葵百合。菊花。牡丹。在英格蘭國王的鼻子里,永遠是玫瑰味。盡管凱爾自己聞不到,但他很高興這是令人愉悅的氣味。他可以聞到灰倫敦(煙味)和白倫敦(血味),但紅倫敦對他來說就是家的味道。
“替我打開,”國王命令道,“不要弄壞封蠟。”
凱爾照做了,把信紙抽了出來。這一次他深感慶幸,國王看不見,也就不知道信有多么簡短。僅僅三行。只是寫給一位名存實亡、病入膏肓的統治者的幾句客套話。
“是王后寫的,”凱爾說。國王點點頭。“繼續,”他強撐著病軀,擺出一副威儀堂堂的派頭,聲音卻顫顫巍巍。“繼續。”凱爾吞了吞口水。“鄰近的王室,”他讀道,“向喬治三世國王陛下致意。”
王后沒有提及紅王室,也不說是來自紅倫敦的問候(其實那座城市真的很紅,因為河流的光璀璨奪目,無處不在),因為她從來不會那樣思考。對于她,以及任何一個只在某個倫敦居住的人來說,區分它們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當其中一個世界的統治者談起別的世界時,他們就說別的,或者鄰居,偶爾(尤其是涉及白倫敦)采用不那么討喜的叫法。
唯有那些為數不多的、能在幾個倫敦之間穿梭的人,需要想辦法區分它們。于是凱爾——眾所周知那個消失的城市被稱為黑倫敦,他受到了啟發——為每一個尚存于世的首府賦予顏色。灰色是沒有魔法的城市。紅色,健康的帝國。白色,饑餓的世界。實際上,城市之間差異巨大(周圍乃至更遠的地方就更無相似之處了)。名字都叫倫敦是一個未解之謎,傳說其中一座城市很久之前就使用了這個名字,那時候門尚未關閉,國王和王后們通信還不是唯一被允準的交流方式。至于哪座城市最先起名倫敦,眾說紛紜。
“我們希望獲悉您一切安好,”王后在信中寫道,“希望貴城的季節與敝城的一樣美妙。”凱爾停了下來。沒有更多內容了,只剩一個簽名。喬治國王的雙手擰在一起。
“只有這些嗎?”他問。凱爾略一猶豫。“不,”他折起信紙,說道。“這只是開頭。”他清了清嗓子,一邊踱步,一邊遣詞造句,以王后的語氣念出來。“感謝您問候我們的家人,她說。國王和我都很好。不過,萊王子還是老樣子,讓人既憐愛又惱火,好在過去的一個月里,他沒有弄斷自己的脖子,或是娶一個門不當戶不對的新娘。要不是凱爾,他起碼會惹一個亂子,甚至兩個一起來。”
凱爾很想讓王后繼續夸耀自己的功績,但墻上的鐘報了五點,凱爾暗自咒罵。他遲到了。“下一封信再敘,”他倉促收尾,“祝笑顏常在,身體康健。敬上。阿恩的艾邁娜王后。”凱爾等著國王說點什么,但見他睜著盲眼,怔怔地遙望遠方,凱爾擔心他失了神。他將折好的信紙擱在茶盤上,朝墻邊走去,剛走了一半,國王說話了。“我還沒有寫回信。”他喃喃道。“沒關系。”凱爾柔聲說。國王好些年都不能寫信了。他嘗試過幾個月,攥著鵝毛筆在羊皮紙上胡亂涂畫,也曾堅持讓凱爾代筆,但通常就是請凱爾傳達口信,凱爾答應逐字逐句地記牢。“你知道,我沒有時間。”國王又說,試圖挽回一點所剩無幾的尊嚴。凱爾也予以配合。“我明白,”他說,“我會轉達您對王室的問候。”凱爾正要走開,老國王又叫住了他。“等等,等等,”他說,“回來。”
凱爾站住了。他抬頭看鐘。已經晚了,越來越晚。他想象著圣詹姆斯宮里的攝政王坐在桌邊,抓著椅子扶手,一聲不吭地生著悶氣。凱爾情不自禁地笑了,于是他轉身面對國王,看見對方顫顫巍巍地從長袍里摸出一樣東西。
是一枚硬幣。“沒了,”國王皺巴巴的雙手捧著硬幣,仿佛那是什么易碎的寶貝,“我感覺不到魔法了。聞不到了。”“硬幣就是硬幣,陛下。”“并非如此,你也知道,”老國王咕噥著,“翻開你的口袋。”
凱爾嘆息一聲。“您會害我惹上麻煩。”
“來吧,來吧,”國王說,“我們的小秘密。”
凱爾把手伸進口袋。他第一次見到英格蘭國王時,交上了一枚硬幣,以證明自己的身份和來頭。君王保守著其他倫敦的秘密,由繼承人一代一代地傳下去,但旅者已有多年不來。喬治王一看到少年手里的玩意兒,就瞇起眼睛,攤開肉乎乎的手掌,于是凱爾把硬幣放在他掌心。只是一枚普通的令幣,與灰倫敦的先令極為相似,不過上面刻的不是君王的肖像,而是一顆紅星。國王握住令幣,放到鼻子底下嗅了嗅。他笑了,把令幣塞進口袋里,然后請凱爾進去。
從那天起,凱爾每次面見國王,他都說令幣上的魔法消失了,要求換一枚新的、帶著體溫的。凱爾每次都會說這是禁忌(確實如此,白紙黑字的規定),但國王永遠說是他們之間的小秘密,凱爾只能嘆息著掏出一枚新的來。
此時,他從國王的掌中取回舊的令幣,換上一枚新的,然后溫柔地合上喬治的枯瘦手指。
“好,好。”病懨懨的國王對著掌中的令幣輕聲念叨。
“保重。”凱爾說完,轉身離開。
“好,好。”國王的注意力逐漸渙散,不再留心周遭的世界和他的客人。
窗簾攏在房間的一處角落,凱爾把沉重的布料拉到一邊,露出墻紙上的一個記號。就是一個簡單的圓圈,當中的直線將其一分為二,那還是一個月前,他蘸著血畫下的。在另一座宮殿的另一個房間的另一面墻上,也有著同樣的記號。它們猶如同一扇門的把手。
凱爾的血與信物匹配,即可使他在不同世界之間穿行。他無需指定地點,因為他當時的所在即是他將來的所在。但在同一個世界里打開一扇門,兩邊就需要完全一樣的記號。大致相同也不行。凱爾吃過沉痛的教訓。
他上次來訪時墻上的記號依然清晰,只是邊緣稍有模糊,但無關緊要,反正要重畫。
他挽起袖子,取下綁在前臂內側的小刀。小刀相當漂亮,堪稱藝術品,從刀尖到刀柄均為白銀打造,刻著花體字母K和L。那是他入宮之前唯一的紀念物。他對那段日子一無所知。應該說是毫無記憶。凱爾把刀刃抵在前臂外側。今天他已經割過一次,為了打開過來的門。現在他又割下第二刀。濃稠的、紅寶石色的鮮血涌了出來,他收刀回鞘,用指頭摸了摸傷口,然后抬手在墻上重新畫圓,以及橫貫其中的直線。凱爾放下袖子,遮住傷口——等他回家再處理身上的傷——回頭看了一眼胡言亂語的國王,然后將手掌按在墻壁的記號上。
墻上的記號在魔法的作用下發出嗡鳴聲。“As Tascen。”他說。轉移。墻紙的圖案開始波動、軟化,在他的觸碰下退讓,凱爾走上前,穿了過去。
Ⅱ
他剛跨出第一步,還沒等第二步落地,乏味的溫莎城堡就變成了優雅的圣詹姆斯宮。悶熱的牢房消失在身后,滿眼都是鮮艷的掛毯和锃亮的銀器,瘋國王的喃喃自語也淹沒在凝重的寂靜氛圍里,有個人坐在奢華的書桌前,手里握著一杯酒,表情相當難看。
“你遲到了。”攝政王說。
“抱歉,”凱爾略鞠一躬,應道,“我有差事在身。”攝政王放下酒杯。“我以為你的差事就是見我,凱爾大師。”凱爾挺起胸膛。“我的順序,殿下,是先見國王。”
“我希望你沒太過縱容他,”攝政王的名字也是喬治(凱爾發現灰倫敦有這種習慣,兒子承襲父親的名字,導致重復太多,也容易混淆),他說著,輕蔑地一擺手,“否則他會精神亢奮。”
“這樣不好嗎?”凱爾問。“對他而言,不好。他很快就會發癲,爬上桌子跳舞,講些魔法和別的倫敦的瘋話。這次你對他耍了什么把戲?讓他相信自己能飛?”
凱爾只犯過一次錯。他在隨后的拜訪中得知,英格蘭國王差點走到窗外。那是三樓。“我向您保證我沒有做過這種示范。”喬治親王捏了捏鼻梁。“他沒法像過去那樣守口如瓶了。因此他不能離開房間。”
“那就是監禁了?”喬治親王撫弄著桌子的金邊。“溫莎城堡是非常體面的地方。”體面的監獄說到底還是監獄,凱爾心里想著,從外套口袋里掏出第二封信。“您的信。”
凱爾被迫站在原地干等,親王讀完了來信(他從未說過信件帶有花香),又從外衣的內口袋里抽出一張未完成的回信,接著寫了起來,而且不慌不忙,顯然是有意刁難凱爾。但凱爾并不介意,他的手指輕叩書桌的金邊,從小指至食指,每一個來回都會讓房間里的無數蠟燭熄滅一根。
“肯定有風。”看見攝政王攥緊了手中的鵝毛筆,他隨口解釋。等攝政王寫完信,兩支鵝毛筆都被捏斷了,情緒也糟糕到了極點,凱爾卻心情大好。
他伸手要信,但攝政王沒有給他,反而起身離開桌子。“坐得我腰酸背疼。陪我走走。”凱爾不喜歡這樣,可也不能空手回去,所以只好勉強順從。他從桌上撿起親王剛剛用完、尚未折斷的一支鵝毛筆,裝進口袋里。“你打算直接回去嗎?”喬治親王問。他領著凱爾穿過走廊,盡頭是一扇不起眼的門,被簾布遮了一半。
“還有一會兒。”凱爾應道,落在半步之后。守在走廊里的兩名皇家衛兵也跟了上來,如影隨形。凱爾感到了他們的目光,猜度著他們對于這位客人的情況了解多少。王室成員應該是知道的,至于侍奉他們的人知道多少,就全憑王室成員的慎重程度了。
“我以為你只是來找我的。”親王說。
“我喜歡您的城市,”凱爾輕聲回答,“而且我的任務特別消耗精力。我要走一走,換換氣,然后再回家。”
親王抿著嘴唇,神色漠然。“恐怕城里的空氣不如鄉下那么新鮮。你怎么稱呼我們來著……灰倫敦?就最近來說真是再貼切不過了。留下來吃晚飯。”親王說的每句話幾乎都是陳述的語氣。就連提問也不例外。萊也是這樣,凱爾認為可能是他們從未被拒絕過,所以養成了習慣。
“你在這兒會很有口福,”親王咄咄逼人,“我陪你喝點酒,好讓你恢復精神。”
聽起來是好心邀請,但攝政王的所作所為向來可不安好心。
“我不能久留。”凱爾說。
“我堅持,”親王說,“飯菜已經備好。”
有人要來嗎?凱爾心想。親王到底想干什么?把他展示給外人?凱爾時常懷疑親王有這種想法,不知道有沒有別的原因,至少年輕的喬治不喜歡保守秘密,鐘情于熱鬧的場面。但不管親王有多少缺點,他并不傻,而只有傻瓜才會將凱爾這樣的人公之于眾。灰倫敦早就遺忘了魔法。輪不到凱爾來提醒他們。
“您太慷慨了,殿下,但我最好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而不是拋頭露面。”凱爾一歪腦袋,甩開一綹紅銅色的頭發,除了湛藍的左眼,又露出深黑的右眼。整個眼睛都是黑色的,包括眼白和虹膜。這種眼睛可不屬于普通人類。那是純粹的魔法。是血魔法師的記號。安塔芮的標志。
攝政王注視著凱爾的眼睛,凱爾對他的反應頗為享受。謹慎,不安……還有恐懼。
“您知道我們的世界為何相互隔離嗎,殿下?”他不等親王回答,接著說道,“是為了保護你們。您也知道,很久很久以前,世界曾經是相通的。您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以及其他世界之間,有門可以出入,任何擁有一絲力量的人都能夠通行。包括魔法本身。但魔法那個東西,”凱爾又說,“捕食心靈強健者和意志薄弱者,其中一個世界無法阻止它。人吃魔法,魔法吃人,吞噬他們的肉體、精神,然后是他們的靈魂。”
“黑倫敦。”攝政王低聲說。
凱爾點點頭。那座城市的顏色并不是他賦予的。每一個人——至少是紅白倫敦的每一個人,還有灰倫敦的少數知情人——都知道黑倫敦的傳說。那是睡前故事。童話。也是警告。關于消失的城市,以及世界。
“您知道黑倫敦和您的倫敦有何共同之處嗎,殿下?”攝政王瞇起眼睛,但并未插嘴。“缺乏克制,”凱爾說,“渴望力量。您的倫敦之所以得以幸存,唯一的原因是它遺世獨立。學會了遺忘。您一定不會希望它恢復記憶。”凱爾沒有說出來的是,黑倫敦的血脈里充滿了魔法,而灰倫敦幾乎沒有,他希望強調自己的論點。看情形,他確實做到了。這一次他伸手要信,親王沒有拒絕,甚至毫不猶豫。凱爾把羊皮紙塞進口袋,與偷來的鵝毛筆放在一起。
“一如既往,感謝您的款待。”他說著,夸張地鞠了一躬。攝政王打了個響指,召來一名皇家衛兵。“護送凱爾大師到他要去的地方。”他不再多說,轉身走開。皇家衛兵把凱爾送到公園邊上就離開了。圣詹姆斯宮佇立在身后。眼前就是灰倫敦。他深吸一口氣,嘗到了空氣中的煙味。他很想回家,但還有事要辦,而且跟患病的國王和攝政王打了一番交道,凱爾需要喝上一杯。他挽起袖子,豎起領子,走向城中央。
他邁步穿過圣詹姆斯公園,走上一條沿河的泥土步道。太陽將要落山,空氣雖不清新,但算得上涼爽,秋風輕輕拂動黑色外套的下擺。他踏上一座跨河而架的人行木橋,靴子踩出了輕柔的聲響。凱爾在拱橋上駐足,身后是燈火輝煌的白金漢宮,前面是泰晤士河。河水在木板底下嘩嘩流淌,他撐在欄桿上,低頭俯視。他心不在焉地彎曲手指,流動立刻停止,腳下的河水平靜無波,猶如一面光滑的鏡子。
他端詳著自己的倒影。
“你又不帥。”每次萊看到凱爾照鏡子,就會這么說。
“我百看不厭。”凱爾如是回答,雖然他從未看過自己——完整的自己——只是觀察眼睛。他的右眼。即便在紅倫敦,魔法盛行之地,這只眼睛也令他與眾不同。永遠格格不入。
凱爾的右側傳來清脆的歡笑,接著是嗯哼聲,然后就聽不大明白了。凱爾松開手指,河水又在他腳下奔流如初。他繼續前行,離開公園,來到倫敦的街道,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依稀可見。凱爾對教堂頗有好感,于是沖著它點點頭,好似老友相遇。盡管這座城市到處都臟兮兮、灰撲撲的,且雜亂無章,貧困潦倒,但也有紅倫敦所缺乏的東西:拒絕改變。不為所動的心態,持之以恒的努力。
修建大教堂花了多少年?它將要佇立多少年?在紅倫敦,品味的變化如同季節交替,因此,建筑每每起而又拆,再以不同的模樣重現。魔法讓事情變得簡單。甚至可以說,凱爾心想,讓事情太過簡單。
有時候在家過夜,他覺得睡前和醒來時身處兩個不同的地方。
但在這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永遠靜靜地等候他的到來。
他經過高大的石頭建筑,穿過車水馬龍的喧囂街道,走上一條環繞著教長庭院的小路,院墻上爬滿了青苔。小路越來越窄,延伸到一家酒館門前為止。
凱爾也止住腳步,脫下外套。他從左往右翻了一面,把帶有銀紐扣的黑衣換成更加低調和陳舊的街頭常服:一件棕色高領上衣,邊緣和肘部磨損得厲害。他拍拍口袋,胸有成竹地走了進去。
Ⅲ
“比鄰”是一家古怪的小酒館。店里墻壁骯臟,地板污穢,凱爾也知道老板巴倫在酒里兌水,盡管如此,他還是每每登門。
雖然環境低劣,客人也邋遢,但這個地方卻始終吸引著他,因為不知是巧合還是人為安排的緣故,比鄰酒館的地點不曾改變。當然了,店名不一樣,提供的酒水也有差異,但就在這個位置,無論灰、紅還是白倫敦,都坐落著一家酒館。實際上,這里不是源頭,不像泰晤士河,或巨石陣,或數十個鮮為人知的魔法標地,但又確確實實地存在著。一種現象。一個定點。
因為凱爾在酒館里做生意(不管招牌上寫的是“比鄰”、“落日”,還是“焦骨”),他自己也成了定點的一部分。
少有人能領會到這種浪漫。霍蘭德也許能。如果霍蘭德有這份心思的話。
撇開浪漫不說,酒館是做買賣的好地方。在灰倫敦,極少數信仰魔法的人——他們滿腦子都是對魔法的幻想,常常聽風就是雨——受到怪力亂神的吸引,趨之若鶩地來到這里。凱爾也受到了吸引。唯一的區別就在于,他知道是什么在召喚他們。
當然,吸引那些對魔法如癡如醉的酒館客人的,不僅是那種透徹骨髓的神秘力量,或怪力亂神的流言,還在于他。或者說,有關他的傳聞。小道消息自有其魔力,在比鄰酒館這里,魔法師的事跡口耳相傳,如同稀釋的麥酒一樣在人們嘴里流動。
他端詳著酒杯里的琥珀色液體。
“晚上好,凱爾。”巴倫說著,加滿了他的酒杯。
“晚上好,巴倫。”凱爾應道。
他倆幾乎每次都這樣相互問候。店老板的身子骨結實得像一堵墻——長了胡子的墻——高大魁梧,穩如泰山。巴倫絕對見識過他怪異的一面,但似乎從不為此困擾。或者即便是心里有什么想法,他也掩飾得很好。吧臺后墻上的掛鐘敲響了七點,凱爾從破舊的棕色上衣里摸出一件小東西。那是一只木頭盒子,手掌大小,有個鐵搭扣將其鎖住。他掰開搭扣,用拇指推開蓋子,盒子展開成一方游戲盤,上面有五個凹槽,各裝著一種元素。
第一個凹槽里是一塊土。第二個,是一勺水。第三個,即空氣所在之處,是一堆散沙。第四個,一滴油,容易著火。第五個,也就是最后一個凹槽里,是一小塊骨頭。在凱爾的世界,這只盒子及其內容不僅是玩物,而且是一種測試工具,用來發現孩子們受哪些元素吸引,以及能夠吸引哪些元素。大多數人很快就用不著玩這個游戲了,他們轉而研習咒語,或者投向更大更復雜的版本,以磨煉技藝。在紅倫敦,這套既靈驗又有局限的元素游戲,幾乎每家每戶都有,周邊的村子可能也有(但是凱爾并不確定)。而在這里,這座沒有魔法的城市,它實屬罕見,凱爾相信他的客戶也同意這一點。畢竟,對方是收藏家。
在灰倫敦,來找凱爾的只有兩種人。
收藏家和魔法迷。
收藏家富有且無趣,通常對魔法本身不感興趣——他們不知道治療符文和束縛咒語之間的區別——凱爾特別喜歡他們的光顧。
魔法迷就麻煩得多。他們幻想自己是真正的魔法師,希望購買一些小玩意兒,為的不是單純的擁有它們,或者展示和炫耀,而是使用。凱爾不喜歡魔法迷——一方面,他覺得他們是白費心思,另一方面,為他們服務有點叛徒的意味——所以,當一個年輕人走過來坐到凱爾身邊,而當他抬起頭來,本以為對方是收藏家,結果卻發現是一個陌生的魔法迷時,凱爾情緒一落千丈。
“這兒有人嗎?”魔法迷不等回答就坐了下來。
“走開。”凱爾淡淡地說。
但魔法迷不為所動。
卡爾知道對方是魔法迷——他瘦高個兒,舉止拘謹,對他的身材而言上衣略短,當那雙長長的胳膊擱在吧臺上時,袖子縮了一英寸,凱爾得以瞥見部分文身。一個畫得很爛的力量符文,意思是將魔法加持在某人身上。
“是真的嗎?”魔法迷又問,“他們說的是真的?”
“要看是誰說的,”凱爾關上盒子,把蓋子扣回原位,“以及說了什么。”這套把戲他耍了上百次。他用藍眼睛的余光觀察對方的嘴唇,為接下來的應對做安排。如果是收藏家,凱爾就通融一下,但如果落水的人自稱會游泳,就不用提供救生筏了。“說你帶東西過來,”魔法迷掃視著酒館,說道,“其他地方的東西。”凱爾抿了一口酒,魔法迷視其為默認。
“我想我需要自我介紹一下,”對方接著說,“愛德華·阿奇博爾德·塔特爾,三世。不過別人都叫我內德。”凱爾揚起眉毛。年輕的魔法迷顯然在等他自我介紹,不過既然此人已經清楚他的身份,凱爾就免去了禮節。“你想要什么?”
愛德華·阿奇博爾德——也就是內德——在凳子上扭了扭身子,湊過來悄聲說:“我在找一點土。”
凱爾斜過玻璃杯,杯口沖著店門。“去公園看看。”
年輕人沉聲一笑,令人不快。凱爾喝完了杯里的酒。一點土。聽上去是很簡單的要求。實則不然。大多數魔法迷都知道,在他們自己的世界里,力量極其有限,而有不少人相信,擁有異世界的一部分實物,他們就能夠使用魔法。
曾經,他們這種想法是對的。那時候源頭的大門敞開著,力量在不同世界之間流動,只要血脈里存在一點魔法,或者擁有一件來自異世界的信物,任何人不僅可以使用力量,還能利用其從一個倫敦穿梭到另一個倫敦。
但那段時光已經一去不返。
大門消失了。是數百年前毀掉的,就在黑倫敦淪落之后,它所屬的世界也隨之泯滅,除了傳說,什么也沒留下。如今只剩安塔芮擁有足夠的力量創造新門,也唯有他們可以通過。但安塔芮的人數向來不多,直到大門封閉時,他們的稀少數量才為人所知,而且仍在日益減少。安塔芮力量的源頭一直都是個謎(不靠血脈延續),但有一點很明確:世界分離得越久,安塔芮也就越少。如今,凱爾和霍蘭德似乎是這支瀕危族群的最后幸存者。“怎么樣?”內德催促道,“你愿不愿意帶土來?”凱爾瞟向魔法迷手腕上的文身。灰世界的居民從來都不明白,咒語的威力大小,取決于施展的人強大與否。此人強大嗎?凱爾扯動嘴角,微微一笑,把游戲盒子推到他面前。“知道這是什么嗎?”
內德小心翼翼地拈起兒童玩具,似乎擔心它隨時可能著火(凱爾的腦子里閃過了點燃它的念頭,但還是打消了)。擺弄一番后,他的指頭終于摸到搭扣,游戲盤在吧臺上攤開了。幾種元素在搖曳的燈火中閃著微光。
“聽著,”凱爾說,“挑一種元素,讓它離開凹槽——當然你不能用手觸碰——如果做到了,我就給你帶土。”內德皺起眉頭。他思考片刻,抬手指著水。“這個。”他至少不蠢,沒有選骨頭,凱爾心想。空氣、土和水是最容易操縱的——即便是萊那種與任何元素都不存在吸引力的人,也可以做到。火需要一點技巧,不過,最難操縱的是那一小塊骨頭。原因不難理解。誰能移動骨頭,就能移動尸體。這是強大的魔法,在紅倫敦也是。
凱爾看著內德把手懸在游戲盤上。他對著水低聲念叨,可能是拉丁語,也可能是胡言亂語,總之不是正宗的英語。凱爾揚起嘴角。元素沒有語言,換句話說,使用任何語言都可以。語言本身并不重要,開口說話是為了集中心智、建立聯系、獲取力量。簡而言之,語言不是關鍵,意圖才是。魔法迷直接用英語對著水說話也行(對他來說最好不過了),但他咕噥著自己創造的語言,手還在游戲盤上空順時針打轉。
凱爾嘆了口氣,將胳膊肘立在吧臺上,用手撐著腦袋。與此同時,內德仍在滿臉通紅地堅持。
過了好一陣子,水微微抖動(可能是因為凱爾打哈欠,又或是因那人抓著吧臺導致的),然后靜止無波。
內德低頭瞪著游戲盤,額頭青筋隆起。他握手成拳,凱爾甚至擔心他會砸碎游戲盤,好在他的拳頭落在了旁邊,很重。
“行了。”凱爾說。
“肯定有詐。”內德咆哮道。
凱爾抬起腦袋。“是嗎?”他問。他的手指微微彎曲,那一小塊土從凹槽里飄了起來,正巧落進他的掌心。“你確定嗎?”他再次反問,一小股風卷著沙子在空中盤旋,繞著他的手腕轉動。“也許是的……”水珠凌空飛起,滴在他的手掌上,凝成一塊冰。“……也許不是……”他又說,油在凹槽里燃起了火焰。
“也許……”凱爾說話時,那塊骨頭也浮在空中,“……只是因為你連一點力量的皮毛也不曾擁有。”
內德目瞪口呆地看著五種元素在凱爾的指間各自舞動。他的耳畔響起了萊的責罵。賣弄。然后,與先前一樣,他又漫不經心地讓它們落下。土和冰砸在凹槽里,發出一聲悶響,沙子悄然落在碗中,油上跳躍的火焰熄滅了。只有骨頭尚未歸位,懸在他倆之間。凱爾一邊思考,一邊感受著魔法迷渴求的目光。
“這個多少錢?”他問。
“不賣,”凱爾回答,繼而糾正道,“不賣給你。”內德立即起身,抬腳就走,但凱爾還沒打算放對方走。
“如果我給你帶土來,”他說,“你能給我什么呢?”
魔法迷站住了。“你報個價。”
“報價?”凱爾從不為金錢而走私。金錢變化無常。他拿著先令在紅倫敦有什么用?還有英鎊?與其帶到白巷買東西,還不如將其燒掉為好。他或許能在這里花錢,但到底花在什么事情上呢?不,凱爾玩的是另一種游戲。“我不要你的錢,”他說,“我要真正貴重的東西。你不愿失去的東西。”
內德匆匆點頭。“好的。你別走,我——”
“不是今晚。”凱爾說。
“那什么時候?”
凱爾聳聳肩。“這個月內。”“你指望我坐在這里干等?”“我沒指望你做任何事。”凱爾又一聳肩。這樣說很殘忍,他知道,但他想看看魔法迷的愿望有多么強烈。如果此人真有決心,能等到下個月,凱爾決定帶一袋土送給對方。“你走吧。”內德的嘴巴張開又合上,然后恨恨地吐了一口氣,拖著腳步走了,半路上差點撞到一個戴眼鏡的小個子。凱爾摘下懸在空中的那塊骨頭,放回盒子里,眼鏡男走到空著的凳子邊。“剛才怎么回事?”他坐下來問道。“不用理會。”凱爾說。“那個是給我的嗎?”對方沖著游戲盒子點點頭。
凱爾頷首,將其遞給收藏家,對方輕輕地接了過去。他任憑這位先生擺弄了一陣子,然后展示了它的用法。收藏家瞪大了眼睛。“棒極了,棒極了。”
他把手伸進口袋,掏出一個被方巾裹住的東西,放在吧臺上發出沉悶聲響。凱爾打開方巾,發現里面是一只銀光閃閃的盒子,側面有一根細細的曲柄。
是音樂盒。凱爾暗自一笑。
紅倫敦有音樂,也有音樂盒,但絕大多數使用魔法演奏,而非齒輪,凱爾對于這種裝置的結構甚是著迷。灰世界在很多方面笨拙遲鈍,但正因為缺失魔法,使得他們偶有精巧的發明。比如他們的音樂盒。復雜而雅致的設計,無數零件以令人眼花繚亂的方式運轉,只為播放一小段曲調。
“需要我解釋嗎?”收藏家問。
凱爾搖頭。“不用,”他輕聲說,“我有好幾個。”
對方的眉頭擰成一團。“那還成嗎?”
凱爾點點頭,又用方巾將其包得嚴嚴實實。
“你不想聽聽嗎?”凱爾想聽,但不想在這家骯臟的小酒館里聽,音樂會失去風味。再者,該回家了。
凱爾離開了仍在吧臺前擺弄兒童玩具的收藏家——他發現不管怎么搖晃盒子,已經融化的冰水和沙子都不會流出凹槽,正為此驚嘆不已——走進酒館外的夜幕中。凱爾朝泰晤士河的方向行去,一路聽著周遭的城市之聲,附近的車輪轆轆作響,遠處有人在叫喊,有的愉悅,有的痛苦(但無法與響徹白倫敦的哭號聲相比)。泰晤士河很快映入眼簾,在夜色中像一條黑色的帶子,這時教堂的鐘聲遠遠傳來,一共八聲。
該走了。他來到一家臨河的店鋪,立在磚墻的陰影之中,卷起袖子。因為之前的兩道傷口,他的胳膊已經很疼了,但他還是抽出小刀,割了第三次,指頭沾著血漿,在墻上涂抹。
掛在頸上的其中一根繩子吊著一枚紅色令幣,與下午喬治國王還給他的那枚一樣,他拿著硬幣,按在涂了血的磚墻上。
“好了,”他說,“我們回家。”他經常下意識地與魔法對話。不是命令,只是交談。魔法是活物——大家都知道——但對于凱爾來說,它不僅是活物,甚至像朋友和家人。畢竟,魔法是他的一部分(遠遠不止一小部分),他有一種感覺,它知道自己說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不僅僅在他召喚的時候,而是一種持續不斷地感知,在每一次心跳、每一口呼吸之間。
因為他是安塔芮。
安塔芮可以與血對話。與生命、與魔法本身對話。第一元素,終極元素,無處不在,無形無影。
他感覺到魔法在掌心悸動,磚墻既熱又冷,凱爾猶豫著,想看看如果不作要求,魔法是否回答。但它毫無反應,只等他發聲下令。元素魔法或許可以使用任何語言,但安塔芮魔法——真正的魔法,血魔法——只有一種語言,絕無僅有。凱爾按在墻上的手指微微彎曲。
“As Travars。”他說。旅行。這一次,魔法聽見了,服從了。世界泛起漣漪,凱爾抬腳進門,沒入黑暗,灰倫敦猶如一件外衣被甩在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