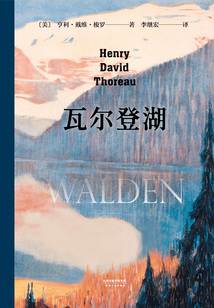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09評論第1章 導讀(1)
當亨利·戴維·梭羅在1845年7月4日搬到瓦爾登湖畔獨自生活時,即將年屆二十八歲的他也許并沒有料到,這次貌似尋常的舉動將會成為世界文學史上極為著名的事件。他平靜的心態可以從翌日所寫的筆記中略見一斑:
7月5日,星期六。瓦爾登湖。昨天我搬到這里來生活。這座木屋讓我想起幾座以前見過的山間住宅,它們似乎散發著飄渺的氤氳,令人聯想到奧林匹斯山的神殿。去年夏天,我曾在某位開辦鋸木廠的人家里住過,就在卡特斯基爾山,松樹果園再往上那片生長著藍莓和樹莓的地方,那里非常清凈和涼爽,別有一番仙境的意味。……墻壁是木條拼接而成的,并沒有涂抹灰泥,里面的房間也沒有安門板。那座房子顯得高尚脫俗,兼且氣味芬芳,很適合招待嬉游人間的神仙……
撰寫筆記是他在八年前,亦即1837年養成的習慣。那年秋天他結束了在哈佛學院四年的學習生涯,遇到比他早十六年畢業的校友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因為在前一年出版散文集《自然》而聲名大噪的愛默生已經組織起超驗主義俱樂部,并且剛剛在8月31日發表了題為“美國學者”的演講,呼吁該國作家擺脫歐洲的影響,開創能夠在風格上獨樹一幟的美國文學,隱隱有成為文壇領袖之勢。愛默生對這個和他一樣居住在馬薩諸塞州康科德鎮的學弟青眼有加,交談間問起梭羅是否有寫筆記的習慣。梭羅受到很大啟發,隨即開始實踐這種將會給他今后的創作帶來極大幫助的做法:
10月22日。“你在忙什么呢?”他問,“你做筆記嗎?”所以我在今天做了第一次筆記。
他堅持了整整二十四年。1906年,波士頓的哈夫頓·米弗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出版了《梭羅筆記》,收錄的條目從1837年10月22日到1861年11月3日,總共有十四卷之多。然而,他在瓦爾登湖獨居了兩年兩個月又兩天,所做的筆記卻非常少,只占據了第1卷的后三章。但這并不意味著梭羅其間很少讀書或者寫作;恰恰相反,他生前出版僅有兩部作品,《在康科德河與梅里麥克河上的一周》與《瓦爾登湖》,都是那段離群索居的歲月孕育出來的。其實梭羅之所以搬到瓦爾登湖畔居住,最直接的原因正是他需要安靜的環境,以便完成一部構思已久的、悼念其亡兄約翰的作品。
約翰出生于1815年,和梭羅相差只有兩歲,彼此間的感情非常深厚。他們從小睡一張床,結伴到康科德鎮學校念書,1828年又一起轉到康科德學院。五年之后,梭羅考取了哈佛學院,已經在鄰郡唐頓鎮當上教師的約翰節衣縮食,幫忙支付了部分學費和生活費。梭羅在1837年畢業,先是在康科德鎮中心學校任教,但由于不愿體罰學生,只工作了幾個星期就辭職。翌年,約翰從唐頓鎮返回故鄉,接手關閉數年的康科德學院,親自擔任院長,并由梭羅出任古典學教師;兄弟倆自此同事了三年多。除了擁有共同的事業,他們甚至還共同愛上一個叫做伊倫·西瓦爾的女孩,不過兄弟倆先后求婚都遭到拒絕。
到了1841年,約翰罹患了肺結核,身體越來越差,梭羅獨木難支,只好關掉康科德學院,隨即住進愛默生家,幫忙做些家務雜活的同時,也向他學習寫作。在愛默生的提拔之下,梭羅開始在超驗主義的大本營《日晷》(TheDial)雜志發表文章,成為嶄露頭角的文壇新人。
1842年1月,梭羅和愛默生都遭遇了慘痛的事情:前者的兄長約翰因為破傷風英年早逝,后者的長子沃爾多由于猩紅熱夭壽而終。約翰的去世給梭羅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創傷,始終不能忘卻兄弟情誼的他想到要通過文字來表達他的悼念,但由于各種紛繁的雜務,這個心愿遲遲無法實現。第二年他接受愛默生的安排,遠赴紐約史泰登島,充當后者侄兒侄女的家庭教師;十個月后,他回到康科德鎮,卻又不得不在他父親的鉛筆廠幫忙。
與此同時,康科德鎮也變得日益喧囂起來。蒸汽機的發明和推廣引發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業已接近尾聲,作為最先進交通工具的鐵路開始在新英格蘭地區出現。1843年5月,費奇堡鐵路公司興建的波士頓-費奇堡鐵路正式動工;隔年6月17日,波士頓至康科德路段開通運營,每天有四班固定的列車往返兩地,使原本僻靜的康科德變得非常熱鬧。而梭羅父母的家又正好在火車站附近,離鐵路只有數百英尺,自然不是適合潛心創作的理想環境。實際上,從約翰去世以后,梭羅的筆記中斷了三年有余,直到1845年7月5日才又接上,這足以證明悲傷的心情、繁雜的事務和吵鬧的環境影響到他的閱讀及創作,盡管其間他在《日晷》上也發表過若干散文和詩歌。
1844年4月30日,梭羅和他的朋友愛德華·霍爾在康科德鎮的費爾黑文湖附近游玩,不慎引發山火,燒毀了三百英畝林木,造成超過兩千美元的損失;這件事成為5月3日《康科德自由人報》上的新聞。梭羅并沒有因此受到任何懲罰,然而鎮上的同胞卻不肯原諒他的無心之失,經常在背后指責他是“燒毀森林的人”。由于紛紜的人言物議,再加上內心的負疚,梭羅在康科德鎮生活得并不舒心,遂漸漸萌發了搬離他父母家的想法。他最初選中了弗林特湖——當地最大的湖泊——旁邊的荒地,準備到那里蓋一座木屋供自己居住,可是沒能獲得其主人的同意。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當年年底,愛默生以每英畝八美元八美分的價格,買下了瓦爾登湖邊十一英畝林地。作為梭羅的朋友兼導師,他自然沒有理由拒絕前者的請求。于是梭羅在1845年3月底來到了瓦爾登湖,動手搭建一座十英尺寬、十五英尺長的小木屋;等到7月4日,也就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終于如愿以償地開始了那段將會在后世成為傳奇的獨居生活。
瓦爾登湖位于康科德鎮區南邊大約一英里處,雖然費奇堡鐵路緊貼著湖邊經過,但由于人跡罕至,依然是個非常安靜的地方;梭羅在這里度過了也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年。1847年8月,愛默生決定接受英國友人的邀請,到大西洋彼岸去講學和訪問,卻又擔心妻小無人照顧,便邀請梭羅再次住到他家里。梭羅當然很樂意替愛默生分憂,況且他和后者家人的相處向來非常融洽,所以在9月6日,他帶著兩部在湖邊生活時完成的書稿,永遠地離開了那座親手所建的小木屋。
那兩部書稿,就是《在康科德河與梅里麥克河上的一周》和《瓦爾登湖》的初稿。前者便是梭羅此前數年間念茲在茲的悼亡之作,記錄了他和約翰從1839年8月31日起在這兩條河上一周的游歷。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部書稿雖然有些瑣碎,但梭羅很成功地將個人感情、自然環境、風俗歷史結合起來,可以算是上乘之作。然而當時默默無聞的他卻找不到愿意將其付梓的出版商;1847年11月14日,他寫信向正在英國訪問的愛默生抱怨好幾個出版商都拒絕這部書稿。此后他沒有放棄努力,但始終沒有得到滿意的答復,只好聽從愛默生的建議,把修改過的書稿交給詹姆斯·曼羅公司,在1849年自費印刷了1000冊。就像其他許多名載史冊的大作家一樣,他的處女作也遭遇了無人問津的慘景。在1853年10月28日的筆記里,梭羅寫道:
過去一兩年來,那位徒有其名的出版商不斷地寫信來,問我應該如何處理庫存的《在康科德河與梅里麥克河上的一周》,最后旁敲側擊地說,他想把原本被那些書占用的地窖派上其他用場。于是我讓他把書寄過來,今天送到了,裝了滿滿一車,總共706冊。四年前我向曼羅買了1000冊,那筆錢到現在還沒付清呢。……另外290余冊里面,有75冊是贈書,其他的都已賣掉。現在我擁有一座藏書近900冊的圖書館啦,而且其中有700多冊是我自己寫的哦。
雖然在筆記里故作幽默,但梭羅為了將這本書付印,不惜背上多達290美元的債務(當時普通工人的日薪只有1美元),整整四年過去,卻只賣掉可憐的219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沉重的打擊。
正是因為《在康科德河與梅里麥克河上的一周》的反響如此之糟糕,同時完稿的《瓦爾登湖》遲遲不能與讀者見面。不過梭羅似乎很少有懷才不遇的負面情緒,他樂此不疲、精益求精地對《瓦爾登湖》進行修改和完善,七年間七易其稿,直到1854年8月9日才由波士頓的提克諾和費爾德茲聯合公司出版。
半個月后,也就是8月24日,愛默生寫信給他和梭羅共同的朋友喬治·帕特里奇·布拉德福德(當時正在倫敦訪問),談到剛剛面世的《瓦爾登湖》:
舉凡吾國人氏,均應以《瓦爾登湖》為喜。是湖雖小,邇來聲名大振。未知閣下已得閱否?其行文欣快,流光溢彩,殊堪玩味,兼且諸妙咸備,部分文字已臻極高境界。吾輩皆視亨利為美利堅群獅之王。但觀其人近日于康科德鎮行走之貌,雖似淡定,然顧盼自雄之情,溢于言表矣。
時年五十二歲的愛默生早已是享譽大西洋兩岸的詩人、散文家和思想家,在美國和英國出版有許多影響深遠的作品,比如《自然》(Nature)、《愛默生詩集》(Poems)和《群英列傳》(Representative Men)等;在歐洲,他深得薩繆爾·泰勒·柯勒律治、威廉·華茲華斯、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托馬斯·卡萊爾等文化巨人的贊賞,在美國,他備受納撒尼爾·霍桑、沃爾特·惠特曼、亨利·華茲華斯·朗費羅、赫爾曼·梅爾維爾等作家同行的敬仰。身為當之無愧的文壇領袖,他為什么會在看了《瓦爾登湖》之后,便謙遜地恭維已經追隨他十二年之久的梭羅是“美利堅群獅之王”呢?這要從他們所處的歷史進程和社會環境說起。
當時美國正處于重要的成長期,社會上出現了若干種新的趨勢和現象,首先是其疆域的不斷擴張。當喬治·華盛頓在1789年4月30日宣誓就任總統的時候,美國總共只有11個州;但在隨后數十年里,通過巧取豪奪,其領土面積以極為驚人的速度膨脹:先是在1803年以每英畝不足三分錢的代價從法國購得總面積達214萬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領地,后來又在1846年向墨西哥宣戰,攫取了原本屬于后者的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和得克薩斯地區,總面積有310萬平方公里。等到1850年9月加利福尼亞共和國加入美利堅聯合國時,美國已經擁有了31個州,其實際控制的領土和現在美國全境差不多,是立國之初的數十倍。
然而更重要的是該國在政治和文化上對大英帝國的疏離。眾所周知,十三個英屬北美殖民地在1776年7月4日宣布獨立,組成全新的美利堅合眾國;喬治三世治下的大英帝國不甘失去這片廣袤的領地,雙方苦戰七年,直到1783年的《巴黎條約》生效之后才握手言和。但隨后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在政治上固然獲得了可以和大英帝國等量齊觀的地位,在文化和身份認同上,卻依然和這個原來的宗主國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依附關系,國內也一直存在強大的親英勢力,尤其是在新英格蘭地區。
這種現象最直接的表征是,當1812年美國總統詹姆斯·麥迪遜試圖向英國宣戰時,眾議院竟然閉門激辯了整整四天,才以79票贊成、49票反對的表決結果勉強予以通過;參議院的表決結果則是19票贊成、13票反對,也是堪堪過線而已。當時代表親英勢力的聯邦黨在美國國會共有39個席位,他們沒有一個人投贊成票。
從雙方的傷亡人數和所獲直接利益來看,這場持續32個月的戰爭既沒有贏家,也沒有輸家:英國和美國于1814年圣誕前夕在比利時簽署了《根特條約》,英屬加拿大和美國維持戰前的邊界,誰也沒有多占哪怕一寸的河山。然而美國在幾次戰役中取得的勝利,尤其奇跡般的新奧爾良大捷,極大地激發了美國人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熱情,促成了他們在心理上的獨立,乃至許多歷史學家將這場戰爭稱為“第二次獨立戰爭”。
從1815年開始,普通美國人親英的情緒大大減弱,政治上的親英勢力自此一蹶不振,聯邦黨在隨后的總統大選中屢戰屢敗,接連輸給民主共和黨,最終于1829年永久地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反觀那些在1812年戰爭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將領,則先后有三位代表民主共和黨成為總統或副總統:安德魯·杰克遜在1828年和1832年兩次當選總統,理查德·門特·約翰遜在1836年當選副總統,威廉·亨利·哈里森則在1840年當選總統。
威廉·亨利·哈里森在1841年3月4日入主白宮,但履新甫及滿月,這位68歲的總統便因肺炎與世長辭。哈里森是美國最后一位出生于獨立革命以前的總統,他的去世極具象征意義,標志著大英帝國殖民統治的最后一批遺民終于煙消云散。自彼時起,絕大多數美國公民都是在1776年之后誕生的,和生于殖民地時期的父輩不同,大英帝國從來不曾是他們身份認同的構成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