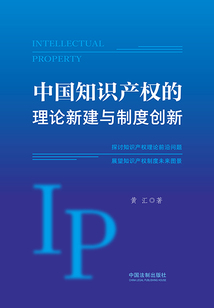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 第16章 我國地理標志保護模式質評
- 第15章 民間文學藝術保護的模式與價值選擇[1]
- 第14章 論知識產權公益訴訟制度的建構[1]
- 第13章 解釋與轉型:知識產權去智力化的闡明[1]
- 第12章 《理論研討與制度展望》:“山寨”治理與中國知識產權建設的未來[1]
- 第11章 人工智能生成物被視為作品保護的合理性[1]
第1章 《商標權基礎理論探討》:全球化背景下商標使用地域性原理的公共政策意蘊及體系化理解[1]
在法律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性原則仍然是各國商標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則,商標使用地域性的理解和適用問題則是其中的難點。區(qū)分商標注冊維持使用、侵權使用和在先使用制度的不同價值取向,對其進行語境化和類型化的解讀,剖析不同制度的公共政策目標之差異,同時借鑒發(fā)達國家商標理論和制度經驗探索其適用的科學路徑與方法,這不但有助于進一步完善我國商標立法,而且有助于豐富相關司法理論,使我國有關商標使用地域性原理的闡釋向著科學化、體系化和邏輯化的方向演進,為我國類似糾紛的科學解決提供統(tǒng)一的方法論基礎和解釋論基礎。
一、商標使用地域性原理的立法原點及價值構造
對商標使用地域性的理解還得從商標權的地域性原理入手。商標權的地域性是指除非有國際條約、多邊或雙邊協(xié)定之規(guī)定,否則商標權的效力僅及于本國境內。商標權作為一種法定權利,系主權國家公共選擇和公共政策的產物,其內容和范圍都要受到各國國內法的強制性規(guī)定。商標權的地域性原理可追溯至《保護工業(yè)產權巴黎公約》第6條有關商標權“獨立性”原則的內容。根據(jù)該原則,一國為何和如何保護商標權,商標權的取得、維持、變更與喪失之條件以及權利保護的范圍、強度和程度等內容,都應由該國的國內法在不違反國際法原則的前提下自主確定。以地域性為基礎建立國際知識產權制度被認為是“19世紀后期世界政治秩序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即便在當今,每個國家政府在其地域范圍內享有主權仍然被認為是構建國際法律和政治秩序的首要原則”[2]。
商標權具有地域性從根本上是由商標法的地域性決定的。商標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國家性,其適用必須以主權國家的地理疆界為范圍。以我國注冊商標權維持制度為例,能夠產生我國《商標法》第49條第2款意義上維持注冊商標專用權效力的使用必須是在我國境內的使用行為,至于在我國境內怎么使用,是在正規(guī)的市場上銷售,還是在夜市或不定地點叫賣,都不會影響使用的效力。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注冊商標權系依我國商標法產生,因此和權利保留有關的商標使用行為,都應當以我國境內為紐帶和連結點。通過商標在我國境內的使用,促成我國產業(yè)經濟的發(fā)展并最終促進我國勞動力就業(yè)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這樣的商標使用行為才能獲得我國商標法的肯定性評價。反之,在我國境外的使用并不能產生維持我國境內注冊商標專用權之效果。誠如有學者所言,“如果商標的使用與特定的地域范圍之間無法建立起聯(lián)系,那么雖然在事實層面該使用事實確實存在,在法律層面也無法得到法律的承認,產生其應有的影響和意義”[3]。我國國家商標局在認定具有維持注冊效力的使用行為時給出的權威解釋也認為“我國《商標法》第49條第2款所稱商標的使用地點應當在中國境內,包括在中國境內從事商品的生產、加工、銷售或提供的相關服務”。[4]即通過注冊后在我國境內使用商標來補正商標注冊時未使用之事實,從而使注冊商標權重新奠定在使用這一“權利自然正當”[5]的理論基點上,最終實現(xiàn)國家保護商標權的對價目標。
商標權只能根據(jù)各個主權國家的國內法而存在。在知識產權世界里,其發(fā)展演繹的規(guī)律化進程表現(xiàn)為知識產權化、產權財產化、財產法律化、法律全球化。知識產權發(fā)展至今,知識產權法律全球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并引導著各個國家國內立法進程。其原因可歸結為四個方面:知識創(chuàng)新的全球價值認同、知識價值的全球溢出效應、知識資本的全球利益需求、知識保護的國別法治落差。但是知識產權法律全球化絕不等于法律的一體化、統(tǒng)一化和去主權化。雖然隨著TRIPs等一大批國際公約的誕生,各國的知識產權立法與實施越來越趨于一致,但知識產權的確立與保護仍然是各國主權范圍內的事。[6]各國的國內法仍是包括商標權在內的各種知識產權權利劃定、權利分配和權利邊界確認的重要依據(jù)。誠如有國際法學者所言:“盡管知識產權國際公約創(chuàng)造了一體化的規(guī)范,但它并非統(tǒng)一立法,締約國仍然保留了相當大的靈活性以決定是否將這些規(guī)定納入其本國法律體系。”[7]因此,在法律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性原則仍堅如磐石。以各個國家的地理疆界和司法主權為限保護商標權,仍然是各國商標立法和司法的基本立足點和出發(fā)點。這既源于現(xiàn)代商標法國家競爭工具的稟賦和主權國家屬地管轄優(yōu)越性的特征,也是商標法作為一種制度文明之社會歷史根源的必然要求。正是在這三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商標權的地域性特征至今仍牢不可破。
二、地域性原理在注冊維持使用制度中的理論突破與制度反思
雖然商標權地域性原理并不復雜,但結合商標使用的具體形態(tài),因不同使用制度的政策目標存有巨大差異,故對其適用方法和理解立場亦存在很大不同。選擇何種解釋方法以符合每項制度之本意,不但涉及對每種商標使用制度的正確理解邏輯還涉及法解釋技術問題,關系到不同知識產權公共政策在每種商標使用制度中的正確貫徹與落實。因此,殊值學理認真探討。
(一)對地域性的合理突破:視出口為合法使用
我國《商標法》第49條明確規(guī)定了注冊維持使用制度,即通常所說的3年不使用即撤銷制度,但《商標法》并未從地域性的角度明確何種地域范圍的使用才是有效的,這在實踐中引起了巨大的爭議。爭議焦點之一即我國商標行政管理部門能否以企業(yè)在國內注冊了商標但因其商標產品3年未在我國境內使用而是出口到境外銷售為理由,撤銷其境內的商標注冊。直至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再審“定牌加工‘USAPRO’商標爭議案”,[8]學界仍有爭議。筆者認為,對此類案件不可教條化地適用商標使用地域性原理。理由在于:首先,在國家鼓勵企業(yè)走出國門,尤其是在當前我國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很多出口型企業(yè)的目標就是境外市場,如果因商標商品3年未在我國境內銷售即撤銷其注冊商標專用權,對該類企業(yè)非常不公平。而且如果商標因3年未使用被撤銷,該商標在國內被其他主體注冊的話,其產品就可能因商標侵權在國內被海關提前扣留,這顯然不利于越來越多外向型企業(yè)走出國門、開拓全球市場。[9]而“眾所周知,出口、投資、消費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因商標撤銷導致出口經濟受損既不符合我國企業(yè)‘走出去’戰(zhàn)略的實施,也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10]。其次,《商標注冊馬德里協(xié)定》第6條規(guī)定了國際注冊的“中心打擊”原則,即“在5年期間內,如國際注冊的申請人在原國內的申請遭到質疑并在此后失去效力,不管是整體還是部分而言,其根據(jù)馬德里協(xié)定獲得的保護在所有的其他國家也就失去效力”[11]。這對我國出口型企業(yè)極為不利,因而,教條化地適用商標使用地域性原理將導致其國際注冊被質疑,甚而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并最終影響其出口貿易。
為鼓勵出口型企業(yè)輸出商標產品以占領國際市場,一些國家的商標法靈活突破了使用的地域性要求,將商標產品出口境外的行為也包括在了有效的使用范圍之內。典型者如《法國知識產權法典》第L.714-5條第2款第(c)項、《英國商標法》第46條之(2)和《意大利商標法》第42條之(2)的規(guī)定。而早在2011年,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xié)會(AIPPI)于印度海德拉巴德召開的“為維持注冊保護的商標真實的使用要求”國際大會上,與會者也達成一致意見,認為“僅為出口目的的商品制造行為,也被認為是對所貼附商標的真實商業(yè)使用行為”[12]。近年來,我國這方面的代表性案例除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審的“貼牌加工‘mine’商標案”[13]外,當屬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SCALEXTRIC’案”,該案判決明確指出,“雖然來料加工的成品并未實際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流通領域,但如果不認定來料加工行為構成商標使用,相關商標權將會因未使用而被撤銷,這既不公平也與國家的貿易政策嚴重相違背,這并不利于我國外向型企業(yè)的發(fā)展”[14]。筆者認為,無論是從公平正當、保護企業(yè)出口、促進我國外向型經濟發(fā)展的角度看,還是從與范式國家商標法全面接軌的角度看,該判決都值得肯定。
當然,從法解釋學的立場來看,之所以應當將出口型企業(yè)商標產品“出口”到境外市場銷售的行為也“視為”有效的商標使用行為,是因為真實的“意圖使用”也屬于商標法上的使用,可以產生維持注冊商標權的效力。對出口型企業(yè)而言,其在國內加工貼附商標的下一步即是將商標產品出口到境外市場銷售,因此國內的貼牌加工行為已足以表明其具有真實使用商標的意圖,從而與一般的以維護注冊壟斷特權為目的的“象征性使用”完全有別,將其納入得以維持注冊商標專用權效力的范圍并不扭曲該制度之本意。對此,正如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在審理“定牌加工‘SODA’商標行政復議案”時所作的裁決:“雖然商標產品直接出口至國外未進入中國市場流通領域,但因其生產行為仍發(fā)生在中國。這種行為實質上是在積極使用商標而非閑置商標,符合我國商法的相關規(guī)定。”[15]也就是說,注冊維持使用制度遵循的是“我用故我在”而非“我注故我在”的原理,其目的是激活已有的商標資源,而非使越來越多的注冊商標落入被撤銷之境地。與其他制度不同,注冊維持之使用考察的重心在于使用人是否有真實使用商標的意圖。“任何能夠體現(xiàn)商標注冊人使用意圖的行為,均可構成該條規(guī)定的使用,而不必拘泥于具體的使用形式。”[16]
實際上,從比較法視角看,在商標注冊維持使用問題上,歐盟的判例法法律實踐經驗較為豐富。比如在“Ansul BV v.Ajax Brandbeveiliging BV案”中,歐盟法院就認為:“某些情況下,如果已注冊的商品曾經被銷售但不再流通時也可以視為實際使用,只要商標權人持續(xù)以注冊商標使用在其銷售的原始商品整體之部分或部件上也構成商標在原始商品上的實際使用。起同樣效果的是,原始商品的保養(yǎng)或維修服務甚至也可視為在相關原始商品上商標的實際使用。”[17]因此,結合到使用地域性原理,視“出口”行為為有效的商標使用行為并產生維持我國境內注冊商標權之效力,完全是法律的一種擬制,并非商標法的常態(tài)。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基于我國世界工廠地位對出口型企業(yè)的一種保護性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否則,中國制造將難以走出國門,也與我國當下正在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難以吻合。
(二)對突破地域性的反思:“相關公眾”的擴大解釋
針對注冊維持使用,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是:法院能否突破地域性原理,通過擴大解釋“相關公眾”的范圍,將境外的消費者也視為“相關公眾”,進而認為在境外的商標使用行為亦構成在我國境內的使用,使之得以產生維持我國境內注冊商標權之效果?我國曾有過類似案例,典型者如2016年的“‘Roadage’商標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時就以原被告雙方的商標產品將出口到墨西哥市場銷售、將在墨西哥市場導致消費者的混淆可能性為由,作為判定國內侵權的依據(jù)。[18]該案系商標侵權案件,但其對注冊維持制度是否具有借鑒意義?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在于,根據(jù)商標使用的地域性原理,能產生維持注冊商標權效力的使用原則上必須是發(fā)生在注冊國境內的使用行為,即可增進注冊保護國境內消費者的福利,并促進其產業(yè)經濟的發(fā)展的使用行為。外向型企業(yè)將商標產品出口到境外的行為也被“視為”商標使用行為完全是基于一國國家利益和公共政策所作的制度安排,并非商標使用效力的常態(tài)。
與我國不同,德國采取“注冊取得”和“使用取得”二元并存的制度模式。《德國商標法》第26條第(1)項是有關商標使用的原則性規(guī)定:“因注冊商標或注冊的維持提出的請求取決于該商標的使用,所有人必須在本國范圍內將商標真正使用于注冊的商品或服務上,除非有不使用的正當理由。”也就是說,按照《德國商標法》第26條第(1)項的規(guī)定,不管是申請注冊時的使用還是注冊維持之使用,原則上都必須在德國境內完成,該條后面各項才是“視為使用”的情況,包括第26條第(4)項規(guī)定的將為出口目的在德國境內貼附商標的行為“視為”合法使用的情形。筆者認為,德國的做法實際上非常合理。因為,不管是注冊時的使用還是注冊維持之使用都具有賦權性質(注冊維持之使用不過是注冊賦權的反面表達而已),所以都必須以商標在本國的實際使用為前提。
我國《商標法》第1條規(guī)定:“為了加強商標管理,保護商標專用權,促使生產、經營者保證商品和服務的質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特制定本法。”依筆者之見,“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的表述就明確表達了我國商標使用的屬地性,強調了商標應在中國境內使用的地域范圍要求。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國家為保護注冊商標權花費了巨大的制度成本(包括國家成立市場監(jiān)督管理部門對注冊商標進行授權審查以及國家的公安、海關、檢察院、法院、邊境、檢驗檢疫等部門對注冊商標的行政和司法保護成本),其意圖換取的“對價”利益就是通過商標在境內使用,增進本國消費者的福利,促進本國產業(yè)文化的進步。[19]相反,針對境外消費者的使用不足以形成我國境內的商標權,也不足以產生維持我國境內注冊商標專用權的效力。就像有學者所說,“商標的本國使用是對商標使用的地域范圍要求”[20],商標的使用必須與特定的空間,即特定的國家和地區(qū)相關聯(lián),才能夠進行相應的法律評價。否則,商標使用如果離開了基本的屬地依歸和屬地原則,主權國家的商標法將難以實現(xiàn)其立法旨趣和目標。
實際上,“‘Roadage’商標案”中,法院的裁判之所以受到學術界詬病,還在于從比較法視角看,即使是針對侵權使用,也必須以商標使用導致本國境內相關公眾的“混淆誤認”為考察對象,而不能突破地域性原理以進口國(或者說目的國)相關公眾為考察對象。比如,就涉案商品和商標分別出口、在歐盟境外貼附商標的“Beautimatic International Ltdv.Mitchel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s Ltd案”[21],針對該境外貼牌加工行為究竟是否構成對歐盟境內商標權人的侵權,歐洲有學者就明確指出:“這種案件的混淆可能性究竟如何評估,我們所能確定的是,由于這種附加行為依據(jù)的是《歐共體商標法》,因此是否導致消費者的混淆要考慮的應是歐盟境內的公眾。”[22]反之,如果以目的國相關公眾混淆與否作為評估依據(jù),則不免與商標法的地域性原則相沖突。
由此可見,因注冊維持之使用具有保留注冊賦權的功能,所以注冊人對商標的使用就必須與注冊保護國領土之間產生積極正面、客觀穩(wěn)定和合法有效的聯(lián)系,通過使用,在注冊國境內產生聲譽影響并成就商譽價值,最終促進該國產業(yè)經濟的進步和商業(yè)文明的發(fā)達。因為,當代國際社會由國家構成,只要有國家的存在,作為維護以領土和主權為特征的國家利益就有其合法性,即便“當前的全球一體化和國際化亦不能抹殺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交往和競爭格局”[23]。因此,在注冊維持使用上強調商標使用的本土性無疑是國家之間經濟競爭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國維護其商標權主權和商標法立法目標的必然要求和具體體現(xiàn)。
三、地域性原理在“在先使用”制度中的適用立場與解釋邏輯
不僅在注冊維持使用制度中,在“在先使用”制度中,地域性原理的理解與適用也十分復雜,需要學理加以探討。我國對在先使用商標的保護主要限于“在先使用有一定影響”者,立法上體現(xiàn)在我國《商標法》第32條和第59條第3款的規(guī)定。但這兩個條款實際上存有本質區(qū)別:前者系注冊禁止條款,主要體現(xiàn)為對在先使用有一定影響商標的所有人禁止他人注冊的保護,是一種消極保護;后者則屬于具有一定程度賦權性質的先用權條款,賦予了在先使用有一定影響商標的所有人在他人注冊商標后在原有范圍繼續(xù)使用商標的權利,是一種積極保護。雖然二者都以保護在先有一定影響的商標為旨趣,但二者的立法目標并不完全一致:前者以遏制非誠信的“搶注”為目的,后者則以平衡注冊人與在先使用人的利益為旨趣。[24]結合到使用地域性原理,這里最值得探討的是“境外使用產生一定影響的商標”能否超越地域性原理而被納入它們各自的調整范圍。這同樣存在法解釋技術問題——如何選擇正確的解釋原則和解釋方法方能符合二者的本意,同樣需要進行法理上的剖析。
(一)地域性原理在消極“在先使用”制度中的適用立場
如前所述,我國《商標法》第32條屬于注冊禁止條款,意在禁止第三人以不正當手段將他人在先有一定影響的商標惡意搶注。[25]但對于“境外使用在我國相關公眾產生一定影響的商標”,其所有人能否啟用我國《商標法》第32條規(guī)定禁止他人注冊,學界仍存有爭議。有學者就明確認為,依據(jù)我國《商標法》第32條規(guī)定,排除他人搶注的在先商標指的是“在中國境內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響者;反之,境外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響但如果未在中國境內使用,不宜依據(jù)該條款加以保護,甚至也不能依據(jù)我國《商標法》第44條第1款‘禁止以其他不正當競爭手段’的規(guī)定給予保護”[26]。筆者認為,此見解仍有商榷余地。
第一,我國《商標法》第32條之規(guī)定系對《商標法》第7條商標申請注冊和使用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的邏輯貫徹。所謂誠實信用者,指的是“同一時空下人類社會多數(shù)眾人超乎條文規(guī)范之秩序,所共同認同、期相遵循之社會生活規(guī)范”[27]。對于在先使用有一定影響商標消極的、具有禁止權能的保護顯然不應有地域性要求。不管是境內使用者還是境外使用者,只要其商標在我國境內的相關公眾中產生了一定影響,就應當有權禁止他人的惡意搶注。否則,在誠實信用這一價值的維護上,我國將違反TRIPs所要求的“國民待遇”原則,容易受到國際社會的詬病。
第二,從比較立法例看,將在先使用有一定影響的商標擴及境外使用者的做法,國際上不乏其例。比如《比、荷、盧經濟統(tǒng)一聯(lián)盟商標法》第4條第(6)項之2、《韓國商標法》第7條第(1)項之12、《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之19都采取該做法。根據(jù)日本著名學者富田徹男先生之解釋,《日本商標法》之所以采行該規(guī)定,“概因日本每年都有數(shù)百萬人出國,這些人在國外看到過多種有影響的商標,如果把被廣泛認識的范圍僅局限在日本國內,那些在外國有名但在日本尚未被注冊的商標將會被全部在日本注冊。歷史上,就曾發(fā)生過尚未在日本注冊的外國商標被日本人模仿使用,因而遭到了外國駐日本大使館抗議的事情”。因此,“為防止外國著名商標在日本境內被大量注冊,才有了不管世界上任何地區(qū)的商標,只要它被廣泛認識,就不允許其在日本國內注冊的規(guī)定”[28]。《韓國商標法》第7條第1款第12項采取了同樣的立場。因為,若不對本國或本地區(qū)之外的在先使用有一定影響商標加以保護的話,除會導致民事主體基于不正當競爭目的“搶注”外,還可能導致相關公眾對商品的來源產生混淆誤認,使其誤以為所購之商品來源于本國或本地區(qū)之外的商標所有人,實際上卻為本國或本地區(qū)內的注冊人提供。總之,對在先有一定影響商標的保護系基于“民法上誠實信用原則、防止消費者混淆和反對不公平競爭行為”這三重目的之考量,賦予在先商標所有人遭他人不法“搶注”時以權利救濟之機會。
如果認為“境外在先使用有一定影響商標”值得保護,其保護范圍究竟多大才合適?是如《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之19那樣,只要是“在相同或近似商品上且以不正當目的使用商標就應當禁止注冊,至于該商標是為日本境內相關公眾還是為外國消費者間所廣泛認知均在所不問”;還是無論境內或境外使用,在先商標都必須在我國境內相關公眾當中產生影響,否則不能獲得保護?筆者認為,宜采后者之立場。理由在于,我國《商標法》第32條對“在先使用有一定影響商標”的保護應以禁止不正當競爭目的的搶注為限。反之,如果在先使用商標僅在境外相關公眾當中產生了影響而境內消費者根本無從知悉,第三人的注冊就難謂“惡意”了。我國《商標法》第32條顯然不能適用規(guī)制善意的注冊者。該觀點亦已得到了我國2016年新頒布的《商標審理及審查標準》的支持,考慮到對境外有一定影響商標的保護之不足,該標準第3.2部分在對我國《商標法》第32條進行解釋時,特別增加了一款規(guī)定,即“當事人提交的域外證據(jù)材料能夠證明該商標為中國相關公眾所知曉的,應當予以采信”。其中,“中國相關公眾所知曉”的要求就明確表明了,在境外使用產生一定影響的商標,只有其影響力輻射到中國境內的相關公眾時才能獲得保護,從而體現(xiàn)出商標保護中國屬地的基本要求。
此外,從解釋學的進路來看,我們需要特別區(qū)分我國《商標法》第32條和第13條的規(guī)定。雖然這兩條都系對未注冊商標之保護,但前者系對“在先有一定影響商標”的保護,后者系對“在先未注冊馳名商標”的保護;前者屬于各國國內商標法自由創(chuàng)設的結果,后者則源于《保護工業(yè)產權巴黎公約》第6條之(2)的強制規(guī)定。根據(jù)奧地利學者博登浩森先生對《保護工業(yè)產權巴黎公約》第6條之(2)的解讀,對境外馳名商標的保護不必以商標在有關國家的商業(yè)中人盡皆知為前提,也不必以申請或獲得與馳名商標利益相沖突的注冊人或使用人實際知曉該未注冊馳名商標的存在為前提。[29]也就是說,對境外在先馳名商標的保護是絕對的。不管境內注冊者是否知悉該馳名商標的存在,其所有人都有權禁止第三人在成員國注冊。但我國《商標法》第32條對在先有一定影響商標的保護是相對的,其意在禁止的是第三人以不正當手段的惡意搶注,在對在先有一定影響商標進行保護時,“商標的一定影響不僅應及于特定地域內的相關公眾,還應及于被異議人”[30]。因此,根據(jù)舉重以明輕的法理,即使認為境外在先使用有一定影響商標的所有人可以動用我國《商標法》第32條來保護,但如《日本商標法》第4條第(1)項之19那樣將保護范圍擴大至“僅為外國消費者廣泛認知者”也顯然并不合理。因為,即使是對境外在先馳名商標之保護也并非說無須本國相關公眾對商標的認知,而只是無須“人盡皆知”而已。我國《商標法》第32條中對境外在先有一定影響商標的保護顯然不能比對在先馳名商標的保護水平更高。
不過,究竟如何認定“通過境外使用在我國境內相關公眾當中產生了一定影響的商標”才更為合理?是否包括境外所有人的商品或服務雖未在我國境內銷售和推廣使用,但通過跨境“廣告宣傳”之方式使其商標在我國消費者當中產生了一定影響的情形?筆者認為應當包括。因為,即便是對境外未注冊馳名商標之保護,TRIPs第16條第2款區(qū)別于《保護工業(yè)產權巴黎公約》第6條之2的地方就在于,它將境外未注冊馳名商標所有人雖未在成員國銷售商品但通過“廣告宣傳”在成員國馳名的情況也包括在內了。[31]筆者認為,隨著全球跨境電子商務的迅猛發(fā)展,境外商標通過跨境宣傳在我國境內消費者當中產生一定影響者將越來越普遍,將它們排除在外顯然不合時宜。只不過在跨境“廣告宣傳”的認定方面,我們宜借鑒英國之做法,“要求這種宣傳必須以本國(中國)的消費者為目標才構成有效的商標使用行為”[32]。反之,境外商標所有人如果只是泛泛地針對全球目標客戶所進行的廣告宣傳,則不能被認為是有效的商標使用行為,難以獲得我國《商標法》第32條的保護。[33]
至于“境外在先有一定影響商標所有人可得禁止他人注冊的商品范圍”究竟多大才合理?是僅適用于相同或類似商品還是可不受商品類別的限制?我國《商標法》第32條對此并未明確規(guī)定。筆者認為,其范圍應和我國《商標法》第59條第3款的規(guī)定保持一致,即應以相同商品或類似商品為限。否則易造成與我國《商標法》第13條之間的價值沖突。我國《商標法》第13條對于未注冊馳名商標之保護也僅限于“在相同或類似商品上”,對境內外在先有一定影響商標的保護自然不得擴大到所有商品上。
(二)地域性原理在積極“在先使用”制度中的適用立場
對在先使用的積極保護主要體現(xiàn)為我國《商標法》第59條第3款之規(guī)定,它賦予在先商標所有人以繼續(xù)使用商標的權利。不過,學界對《商標法》第59條第3款的性質究竟如何仍有爭議。有認為屬于先用權者,也有認為屬于侵權抗辯者。[34]筆者傾向于先用權說。因為權利有實證權利和道德權利之分,前者依據(jù)法律條文的經驗事實產生,后者則訴諸倫理的正當。但不管權利生成的程序如何,都不影響它們在等級次序上存在差異。[35]對在先有一定影響的商標通過“先用權”進行保護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即它將使在先使用人“因對在先商標的持續(xù)使用而贏得的商譽不至于因注冊商標的出現(xiàn)歸于無效”[36]。我國《商標法》第59條第3款亦從實證法的角度表明了該立場。雖然該條款未使用“先用權”之表達,而是規(guī)定“注冊商標專用權人無權禁止他人在原使用范圍內繼續(xù)使用商標”,但筆者認為,“無權禁止”的反面表達即為有權使用。此外,從法理上看,所謂權利者包含四個本質的要素,即“主體的行為意志自由要素,主體的肯定性利益能力要素,社會評價的正當性要素以及社會規(guī)范的認同和保障要素”[37],對在先有一定影響商標所有人而言,這四項要素皆具備。因此,將我國《商標法》“在先商標所有人繼續(xù)使用商標的權益”定位為一種權利并無法理上之障礙。這大概是《日本商標法》第32條明確將在先商標所有人繼續(xù)使用商標的法益定位為“權利”的重要原因。
既然我國《商標法》第59條第3款具有一定的賦權性質,賦予了在先商標所有人“先用權”,那么對其使用的要求顯然應該更高,即同樣必須在我國境內完成,且須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步做出貢獻。從比較法上看,美國強調本土優(yōu)先、實行嚴格的“先使用取得”制度,其立法明確要求所有的在先使用行為都必須在美國境內完成。例如,依據(jù)美國聯(lián)邦憲法貿易條款制定的《蘭哈姆法》第1051條(a)就明確要求:“在美國,聯(lián)邦商標的權利取決于某一標識在洲際貿易中的采納和使用。”[38]“商標之使用須在美國境內進行,從而促進美國洲際貿易的發(fā)展。”[39]反之,當事人在境外使用商標與其在美國境內創(chuàng)設商標權利的愿望無涉,因而不適用“先使用取得”。英國的普通法也采取同樣之立場,比如在“Bernardin(Alain) et Cie v.Pavilion Properties Ltd案”中,法院就認為,商標之商譽若想在英國得到保護,就必須和英國本土的消費者產生實際聯(lián)系,當國外知名公司并未對本土消費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時,盡管因國際物流、跨境旅游或互聯(lián)網等使其商標在英國享有了聲譽,但只要商標權人并未在英國本土經營,該種聲譽也難以轉化為商譽,從而獲得普通法上的先用權保護。[40]除美國、英國外,韓國商標法同樣如此規(guī)定。《韓國商標法》第7條第1款第12項與我國《商標法》第32條類似,屬于注冊禁止條款,即并不要求商標在韓國境內使用。但該法第57條之3在規(guī)定“善意的在先使用商標”時(類似于我國《商標法》第59條第3款)則要求這種使用須在韓國境內完成。筆者認為,這種區(qū)分非常必要且極為合理。它不但使境外的先用權人可以對境內的不當注冊提出異議和宣告無效,還使本國的注冊商標權人始終背負一個境外的“先用權”負擔,這顯然不合理。
若一國如徹底放棄了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將意味著其完全放棄了知識產權保護的自主權,這將導致眾多外國的知識產權主導本國市場,[41]卻使本國人的知識產權處于不受保護的公共領域境地,顯然不利于激勵國民的創(chuàng)新。因此,從解釋學的立場來看,即使認可境外在先使用在我國境內產生了一定影響的商標可以獲得我國《商標法》第32條禁止他人注冊的消極保護,亦不能認為其同時獲得了我國《商標法》第59條第3款意義上的“先用權”保護。國內有學者認為,我國《商標法》第32條和第59條第3款之間可以轉換適用,即依據(jù)第32條享有禁止搶注消極權能的在先商標所有人如果未來得及撤銷在后注冊的話,仍然可根據(jù)我國《商標法》第59條第3款的規(guī)定享有繼續(xù)使用的權利(先用權)。[42]該觀點如果僅做狹隘理解,即認為《商標法》第32條僅保護境內在先有一定影響商標的話,尚可成立;反之,如果認為不限于此而應包括對境外在先有一定影響商標之保護,就非常值得斟酌了。因為,無論從范式國家的商標法還是從激勵本國人民創(chuàng)新的角度看,先用權顯然都不能賦予外國商標所有人,否則,既不利于一國商標權管轄主權的實現(xiàn),也不利于國家競爭能力的提升和創(chuàng)新收益的最大化。
四、地域性原理在侵權使用制度中的辯證理解與解讀立場
對侵權使用地域性原理的理解,當前最具爭議的問題莫過于標準定牌加工(OEM)案件,即境內外就定牌加工產品分別有不同的商標權人,境內的加工方只負責貼牌生產,貼牌產品將全部出口到境外委托人所在的市場銷售的情形。當前的爭議在于:我國法院適用我國商標法,認定貼牌加工行為構成對境內商標權人的侵權并禁止有關產品的“出口”是否合理?筆者認為,鑒于國內的定牌加工方只負責加工生產,貼牌產品將全部出口到境外市場銷售,因此不宜適用我國商標法對定牌加工產品的“出口”行為加以禁止的規(guī)定。結合到商標使用地域性原理,仍有許多理論問題需在此加以澄清。
(一)地域性原理與商標使用侵權混淆可能性之阻卻
有觀點提到,對商標侵權的認定只要有我國境內消費者發(fā)生“混淆可能性”就可以,不必有消費者實際混淆的發(fā)生。[43]因為“實際混淆影響的只是商標侵權損害賠償?shù)闹鲝垼瑢で蠼罹葷恍枳C明消費者有混淆可能性為已足”[44]。否則如何解釋市場監(jiān)管部門在侵權商品尚未出廠銷售前,就可以對其進行查處。對商標侵權而言,“如果要求實際混淆,對于在產生嚴重損害前即需要采取保護行動的商標權人而言,無疑是一種懲罰”[45]。既然商標侵權判定采取的是“混淆可能性”標準,針對貼牌加工行為,我國境內商標權人自不必等到商標產品實際投放市場后才能主張侵權,而是在出口銷售前就可以要求法院下禁令以阻止海關放行,否則難免與“混淆可能性”之標準相抵牾。
該觀點固然沒錯,但混淆可能性標準只是針對在我國境內銷售的產品才有意義。在侵權產品于我國境內銷售,消費者有混淆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因實際混淆而實質性地影響我國境內商標權人的市場壟斷利益以及我國商標法激勵境內商標權人培育商譽功能的實現(xiàn)時,為預防侵權行為的發(fā)生,將侵權的遏制提前到消費者混淆可能性之階段非常必要。但在一般定牌加工情形下,由于貼牌產品直接銷往境外,其必定不會帶來我國境內消費者的實際混淆。此時,將侵權的遏制提前到混淆可能性階段既不合理也沒必要。因為地域性因素的介入,實際上已阻斷了我國境內消費者實際混淆的發(fā)生,此時僵化地理解混淆可能性標準則可能引致我國境內消費者被推定有混淆的可能性,但終因定牌加工產品全部銷往境外,國內消費者根本不會混淆、更不會因此而產生誤認誤購的悖論。筆者認為,在定牌加工案件中機械地推定我國境內消費者有“混淆可能性”不過是一種簡單的臆測,終將被產品銷往境外、我國消費者根本不會發(fā)生混淆的事實所證否。因此,在此類案件中適用混淆可能性標準無異于緣木求魚,難謂合理。
(二)地域性原理與使用侵權商標法域外效力的反思
20世紀,隨著知識產權跨境貿易的不斷加劇,為了防止本國知識產權制度被實質性架空,一些國家采取了確認知識產權域外效力的做法,以對境外的知識產權活動加以規(guī)范,具體包括兩種情形:一種是基于行為主義的域外效力,另一種是基于效果主義的域外效力。前者對于跨境知識產權法律的適用不但包括行為效果地法還包括不發(fā)生效果的行為地法,這使得一國的法律可以規(guī)制“從內到外”的行為;而后者僅針對“從外到內”的行為。[46]但自其誕生之日起,基于行為主義的域外效力就飽受國際社會的質疑。因為它導致了非效果產生的行為地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規(guī)范管轄權擴張,在相當程度上違反了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原則。[47]
針對定牌加工案件,我國理論界和法院有以《商標法》第57條第1款(2001年《商標法》第52條第1項)所謂的“雙同規(guī)則”(商標和商品均相同)為依據(jù),認為只要定牌加工者在相同的商品上使用了與我國境內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就構成侵權,而無需考慮我國消費者是否發(fā)生實際混淆的情況,從而對定牌加工產品進行從內到外的管轄,并禁止相關貼牌產品的出口。對此,筆者認為:
首先,該做法對我國《商標法》第57條第1款存在嚴重誤讀,因為該條款并非放棄了商標侵權混淆可能性標準而不過是采取“推定混淆”之做法,[48]而雙同規(guī)則下的“推定混淆”早已被TRIPs第16條所認可。[49]從商標侵權判定的總體邏輯來看,誠如鄭成思教授所言:“對商品來源造成誤認和引起混淆,是認定商標侵權的總原則。”[50]也就是說,是否構成商標侵權最核心的要件仍然為是否導致消費者的混淆誤認。反之,如果在商標侵權判定中脫離市場,僅對原被告雙方的商品和商標進行物理比對,則無異于是對“商標的生命來自使用”的漠視。因此,那種在定牌加工不會導致我國境內消費者混淆誤認的情況下,試圖以我國《商標法》第57條第1項的規(guī)定來直接判定定牌加工行為構成侵權之做法,顯然犯了以“行為論”取代“結果論”的錯誤。
其次,即便是某些對本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較高的國家,在知識產權的域外適用方面也持較為審慎的態(tài)度,更多采取的是“從外到內”管轄的做法,針對域外的商標使用侵權行為,往往以被告是本國公民,境外的商標使用行為將對境內的貿易構成實質性損害,以及本國商標法的域外適用與外國商標法所確立的原則不沖突為前提。[51]采用“從內到外”管轄的做法與國際上基于“效果主義”原則才會啟動本國商標法對域外的侵權使用行為加以規(guī)制的趨勢難以吻合。
最后,最為關鍵的是,定牌加工產品完全輸出到境外銷售根本不會導致我國境內商標權人的利益遭受實質性侵害,也不會導致我國境內的市場競爭秩序遭受實質性影響,適用我國《商標法》第57條第1項提前對定牌加工企業(yè)的“出口”行為進行“從內到外”的規(guī)制只會傷害民族產業(yè)的發(fā)展。而當前,我國仍處于世界工廠之地位,“中國制造”向“中國創(chuàng)造”轉型尚未最終完成,定牌加工在相當時期內仍將在我國產業(yè)經濟中占據(jù)一席之地。在此情況下,對定牌加工行為進行從內到外管轄的做法既不利于中國制造全球環(huán)境的營造,更不利于中國制造走出國門。誠如有學者所言的那樣,“知識產權法律生成在中國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國所具備的歷史情境、社會環(huán)境和國際場景”[52],“在全球化的今天,就我國的法制實踐而言,我們應該堅持為自己立法,以我們的真正需求以及與我們共享時空他者的需求為根據(jù)采取法的行動”[53]。所以,結合當下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實階段,在定牌加工問題上,我們顯然不宜抬高本國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否則,突破商標地域性原則,不顧條件地對定牌加工行為進行從內到外的規(guī)制,將不利于我國企業(yè)與外國企業(yè)的競爭,不利于我國民族產業(yè)和民族工業(yè)的發(fā)展。[54]
(三)地域性原理與域外國家將出口界定為侵權使用的正確解讀
針對定牌加工行為,還有論者從比較法的視角出發(fā)認為,歐洲范式國家的立法,如德國、英國和意大利的商標法,都規(guī)定了“出口帶有本國注冊商標標記商品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55]因此我國法院對定牌加工產品“出口”至境外的行為進行規(guī)制理所當然。
對此,筆者認為,首先,上述規(guī)定都源于《歐共體商標條例》第9條第(2)款之規(guī)定,[56]上述各國之所以將貼附了本國注冊商標標記商品的“出口”行為定性為侵權行為是因為它們都系歐盟的成員國。而歐盟成立之時的一個重大目標就是推動歐洲統(tǒng)一市場的建立、促進歐洲貿易自由化的實現(xiàn)。在此背景下,商標產品在歐盟各成員國境內銷售與出口至歐盟他國市場銷售并無實質性區(qū)別。這大概是上述國家將“出口”定性為侵權行為的重要原因。其次,這里所謂的“出口”應當指第三人未經許可直接將境內商標權人的商標產品出口轉售到其他國家的行為,即這里的“出口”實際上是出口銷售的含義,其最本質的特征是跨境販售。它與本文所探討的定牌加工行為的情況完全不同:定牌加工在進口國有不同的商標權人,境內的加工方只負責貼牌加工,具體的銷售行為由境外委托人來完成。這也是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提審的“‘PRETUL’牌掛鎖案”[57]和2016年再審的“‘東風’商標案”[58]中否定貼牌加工方行為構成“商標性使用”而認定其僅是一種物理貼附行為的重要原因。最后,從商標使用的地域性原則出發(fā),當委托人在進口國有商標權的情況下,其進口后的銷售行為也完全是基于其在另一地域市場上合法商標權的正當行為,已不受我國境內商標權人的控制。因為地域性作為主權國家意志的體現(xiàn),“意味著任何一國法律賦予民事主體的權利,只能在本國有效”[59]。總之,筆者認為,以歐盟的德國、英國、意大利等國家商標立法為理由來當作我國法院應將定牌加工產品出口境外銷售的行為作為商標侵權來對待的做法,顯然屬于對這些國家商標法誤讀之結果,同樣不合理。
(四)地域性原理與使用侵權判定國際禮讓原則的正確適用
針對定牌加工行為,近年來我國法院以境外委托人在進口國的注冊商標系對境內商標的“搶注”為由,判決國內的定牌加工行為構成侵權。[60]筆者認為,從效果主義的原則立場出發(fā),對這類案件,我國法院毫無疑問應積極行使管轄權。因為,如果境外委托人的注冊確系“搶注”,將對我國境內商標權人的利益構成實質性損害,出于對境內商標權人利益之維護,我國法院主動作為完全有必要,尤其是在境外委托人又系中國公民的情況下。
與此同時,筆者認為,依據(jù)商標權的地域性原理,因每一個國家的商標法只能在本國有效,境外委托人的注冊是不是合法、屬不屬于“搶注”,顯然不能依據(jù)我國商標法進行評判。因為,根據(jù)知識產權法律適用的“國際禮讓”原則,不得對域外知識產權的效力作出判定是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一項基本規(guī)則,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同。比如《美國法律協(xié)會有關知識產權跨國爭端、司法管轄和判決原則》就明確規(guī)定:“對于已經注冊的知識產權,諸如商標權利的產生、效力、期限、屬性、侵權及其救濟等,都應當適用注冊國的法律。”[61]歐盟也采用同樣的立場,比如在一起專利侵權案件中,歐洲法院就認為:“當案件需要確認一項法國專利的有效性時,德國法院是無權就涉嫌在法國發(fā)生專利侵權行為案件的因果關系加以判定的。”[62]因各國實行不同的商標權取得制度,關于是不是搶注以及如何認定搶注,各國商標法的理念和具體的程序并不完全相同。從“國際禮讓”原則出發(fā),以我國商標法為依據(jù)來衡量外國委托人的注冊行為是否構成對我國境內商標權的“搶注”顯然衡諸失當。若不同國家超越地域性原理對在他國發(fā)生的商標使用行為進行效力評價,將不利于跨境貿易的自由發(fā)展,也不利于我國定牌加工產品走出國門。正因如此,我國有學者甚至認為:“即便存在我國知名商標在境外被搶注的問題,正確的方法也應是由當事人依被搶注國的商標或相關國際公約的規(guī)定由商標被搶注國處理,而不能因商標的搶注,就推定商標權人在我國受到了實質性損害,并進而認定定牌加工構成了對我國注冊商標權的侵害。”[63]該觀點具有相當?shù)暮侠硇浴?
當然,若境外委托方的注冊確系對我國境內商標之搶注的話,從維護境內商標權人的利益出發(fā),我國法院積極行使管轄權非常必要。只是在“搶注”的認定方面,不宜適用我國商標法,而應通過法律查明的方式適用注冊國的法律。誠如有學者所說的那樣:“此時不能因為外國法的查明非常復雜,就放棄對涉外定牌加工行為的規(guī)制,否則沖突法就失去了意義。”[64]總之,針對此類案件,從商標權的地域性原則出發(fā),對域外商標注冊之效力進行域內法之評判同樣難謂妥當,值得從學理上進行反思。
(五)地域性原理與商標使用侵權中注意義務審查的檢討
針對貼牌加工案件,實踐中有做法將“被告在相同或近似商品上對外國委托方商標權的真實性未盡到合理的審查義務”或者“明知國內相同領域有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卻未盡到合理的避讓義務”作為認定其構成侵權的重要依據(jù)。筆者認為,該做法同樣值得從學理上進行再探討。因為,如果說早期的“商標侵權規(guī)范源于普通法,其是惡意侵權之分支”,那么晚近以來的商標法則轉向“使消費者免予混淆誤認而非著眼于考察侵權者的主觀動機”[65]。因此,侵權人對注意義務之違反更多的只對損害賠償有價值。從比較立法例看,無論是國際公約還是美國的商標法都采行該做法。如《保護工業(yè)產權巴黎公約》第10條之2第3款第1項在規(guī)制反競爭的“混淆”行為時,就“并未將作為或不作為的故意或過失作為禁止混淆的前提條件,然而在處罰侵權行為的時候可以考慮惡意”[66]。美國《蘭哈姆法》本身不要求以實際侵奪意圖的確證作為侵權判決的前提,但依該法第1117條的規(guī)定,因侵權判決獲得賠償,意圖是必要的。[67]也就是說,行為人是否違反相關的注意義務而在主觀上存有過錯,并非侵權行為成立的要件而恰是責任的承擔要件,具體而言是損害賠償責任的承擔要件,行為人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返還財產的侵權責任,則不需要主觀上有過錯”[68]。針對定牌加工案件,因貼牌產品最終全部銷往境外,鑒于地域性之阻隔,國內消費者根本不可能發(fā)生實際的混淆。在不會有國內注冊商標權人利益受損害的情況下,根據(jù)“無損害即無責任”的基本法理,國內的定牌加工方顯然缺乏承擔侵權責任的根本性前提。此時,苛責境內的加工方盡到對委托方商標權合法與否的審查義務,系在對侵權行為成立與否未做根本判斷的情況下提前對侵權責任(損害賠償責任)的要件進行了判斷,該做法顯然誤置了侵權責任法的邏輯,實在難謂科學。因此,法院以被告在相同或近似商品上接受境外委托加工時未盡到授權審查或合理避讓的注意義務來認定國內受委托方的加工行為構成侵權,顯然不符合民事侵權責任法的一般法理。
五、結語
“法律的權威有賴于法律適用的準確”[69],針對商標使用的地域性問題,亟待區(qū)分注冊維持之使用、侵權使用和在先使用的不同形態(tài),應對其進行區(qū)別立法。否則,作為一種社會化的組織工具,“如果(商標)法律不能充分解決由社會和經濟的迅速變化所帶來的新型爭端,人們就不會再把法律當作社會組織的一個工具加以依賴”[70]。
在立法未作修改的情況下,法官的解釋變得極為重要。因為,“法官對于法律不應只是盲目的服從,而應是一種有思考的服從。不能要求法官單純邏輯地適用概念,而是要對其進行利益評價,從而形成考慮到法律之精神與意義的判決”[71]。在商標使用的地域性問題上,應充分區(qū)分注冊維持之使用、在先使用和侵權使用的不同形態(tài),對其進行語境化的解讀,進而找尋到不同案件的規(guī)范起點,并確立起一套科學的解釋路徑和解釋方法。
具言之,針對商標使用的地域性問題,在適用時應把握以下原則:對注冊維持之使用,因其系商標注冊賦權的反面表達,具有保留注冊賦權之功能,所以原則上其必須在注冊保護國的境內完成,以為其產業(yè)經濟的進步和商業(yè)文明的發(fā)達做出貢獻,反之,則不能獲得保護。而視“出口”行為為有效的商標使用行為更多是一國公共政策和公共選擇的產物,有利于保護出口型企業(yè)的發(fā)展,且并不會扭曲一國商標權保護“利益對價”機制的實現(xiàn)。對在先使用而言,則應區(qū)分積極的在先使用和消極的在先使用,前者因同樣具有一定的賦權性質,所以基于一國知識產權收益最大化的考量,這種使用也必須在本國境內完成,通過使用,與本國境內的相關公眾建立起識別性聯(lián)系,以促進本國產業(yè)經濟的進步和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后者更多體現(xiàn)的是對商標誠信使用秩序的維護,因此這種保護不應內外有別,而是應平等地開放給境內外所有符合條件的在先使用者。侵權使用更多強調的是對境內相關公眾混淆誤認行為的遏制,從而為境內的商標權人創(chuàng)造商譽的勞動努力提供激勵性動機。因此,在標準的定牌加工情形下,當貼牌加工產品最終全部銷往境外時,因其不會導致我國境內消費者的混淆誤認,不會引致我國商標法激勵功能制度性失靈,所以,不將其作為侵權來對待不至影響我國商標法功能的實現(xiàn)。
現(xiàn)今,盡管包括商標法在內的知識產權法出現(xiàn)全球化趨勢,但地域性仍然是知識產權保護一個重要的特征和基本立足點。其原因主要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家政治目標不同、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別政策選擇存在區(qū)別、知識產權國際競爭工具的價值稟賦以及主權國家屬地管轄優(yōu)越性之特征。知識產權地域性具體表現(xiàn)在不同國家基于公共政策目標的差異在知識產權權利取得、保護客體、權利范圍、保護強度、權利限制和侵權判斷等方面存在強度、力度和程度的區(qū)別。對此,就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選擇而言,既要注重知識產權全球化的發(fā)展進程,注重知識產權國際保護中國方案的輸出;也要遵循知識產權保護的地域性原理,注重知識產權保護“國別場景化—社會語境化—本土條件化”的價值立場,并且在國際層面和國內層面上應當強調不同的知識產權保護原則,分別是國際層面上強調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家利益最大化,促進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合作并切實維護國家知識產權安全;國內層面上則應強調知識產權保護主體之間的利益平衡以促進國家創(chuàng)新收益的最大化。關于國內層面,應特別強調保護創(chuàng)新和公共利益兼顧的理念,這有利于促進我國創(chuàng)新生態(tài)鏈的形成,有利于國家走可持續(xù)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道路。
注釋
[1]原載《中國法學》2019年第5期,本次選入對標題和部分內容進行了修改。另,本書對所收錄文章均有不同程度的修改,以下不再提示。
[2][美]弗雷德里克·M.阿伯特、[瑞士]托馬斯·科蒂爾、[澳]弗朗西斯·高銳:《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國際知識產權法(上冊)》,王清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00頁。
[3]趙建蕊:《商標使用在TRIPs中的體現(xiàn)及在網絡環(huán)境下的新發(fā)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4]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編著:《商標法理解與適用》,中國工商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頁。
[5]黃匯:《商標權正當性自然法維度的解讀——兼對中國〈商標法〉傳統(tǒng)理論的澄清與反思》,載《政法論壇》2014年第5期。
[6]參見高光偉:《走進商標,走進商標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頁。
[7]何雋:《全球化時代知識產權制度的走向:趨同、存異與變通》,載《比較法研究》2013年第6期。
[8]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第8135號行政裁定書。本書所選取的案例皆出自中國裁判文書網等公開來源,以下不再另作提示。
[9]參見黃匯:《公共政策衡量視角下商標權地域性原則的突破》,載《人民法院報》2015年7月29日第7版。
[10]張凌博:《地域性原則在商標授權確權行政訴訟中的適用與突破》,載《中華商標》2018年第8期。
[11][英]杰里米·菲利普斯:《商標法:實證性分析》,馬強主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86頁。
[12]胡剛:《僅為出口的貼牌加工中商標使用的法律問題——近期相關司法判例解讀》,載《中國專利與商標》2013年第2期。
[13]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4)行提字第30號行政判決書。
[14]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0)高行終字第265號行政判決書。
[15]北京市知識產權法院(2015)京知行初字第5119號民事判決書。
[16]曹佳音:《我國商標法中“商標使用”概念辨析——以貼牌加工為線索》,載《北方法學》2016年第2期。
[17]Ansul BV v.Ajax Brandbeveiliging BV,Case C-40/01,[2003]ERCI-2439.
[18]參見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浙民再字第121號民事判決書。
[19]參見[日]田村善之:《日本知識產權法》(第4版),周超、李雨峰、李希同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
[20]趙建蕊:《商標使用在TRIPs中的體現(xiàn)及在網絡環(huán)境下的新發(fā)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頁。
[21]See Beautimatic International Ltd v.Mitchel Internationl Pharmaceuticals Ltd and another,[1999]ET-MR912.
[22][英]查爾斯·吉倫:《簡明歐洲商標與外觀設計法》,李琛、趙湘樂、汪澤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86頁。
[23]徐迅:《民族主義》(第2版),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63頁。
[24]參見程德理:《在先使用商標的“有一定影響”認定研究》,載《知識產權》2018年第11期。
[25]參見郎勝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6—67頁。
[26]孔祥俊:《商標法適用的基本問題》(增訂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頁。
[27]曾世雄:《民法總則之現(xiàn)在與未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頁。
[28][日]富田徹男:《市場競爭中的知識產權》,廖正衡、張明國、徐書紳、金路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29頁以下。
[29]參見[奧地利]博登浩森:《保護工業(yè)產權巴黎公約指南》,湯宗舜、段瑞林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頁以下。
[30]馮曉青、羅曉霞:《在先使用有一定影響的未注冊商標的保護研究》,載《學海》2012年第5期。
[31]參見[美]弗雷德里克·M.阿伯特、[瑞士]托馬斯·科蒂爾、[澳]弗朗西斯·高銳:《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國際知識產權法(上冊)》,王清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523頁。
[32]L'Oreal Sa&Ors v.Ebay Internatinonal Ag&Ors,[2009]EWHC 1094(ch),a402.
[33]比如,不以中文方式而是使用其他語言所進行的廣告宣傳,就不能認為是針對我國境內相關公眾所進行的廣告宣傳,其商標也難以被認定為我國《商標法》第32條規(guī)定的在先有一定影響的商標。
[34]參見杜穎:《商標先使用權解讀——〈商標法〉第59條第3款的理解與適用》,載《中外法學》2014年第5期。
[35]參見謝曉堯:《競爭秩序的道德解讀:反不正當競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
[36]王蓮峰:《論對善意在先使用商標的保護——以“杜家雞”商標侵權案為視角》,載《法學》2011年第12期。
[37]菅從進:《權利四要素論》,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38][美]謝爾登·W.哈爾彭、克雷格·艾倫·納德、肯尼思·L.波特:《美國知識產權法原理》,宋慧獻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355頁。
[39]J.Thomas Mc Carthy,Mc Carthy on the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17:9(Eagan:Thomson/West,2008).
[40]參見董美根:《英國商譽保護對我國商標專用權保護之借鑒》,載《知識產權》2017年第5期。
[41]參見馮術杰、于延曉:《知識產權地域性的成因及其發(fā)展》,載《長白學刊》2004年第6期。
[42]參見程德理:《在先使用商標的“有一定影響”認定研究》,載《知識產權》2018年第11期。
[43]參見彭學龍:《論“混淆可能性”——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修改草稿〉(征求意見稿)》,載《法律科學》2008年第1期。
[44]Resource Developers,Inc v.Statue or Libety-Ellis is land Foundation,Inc.,926 F2d 134,17U.S.P.Q.2d 1942,7th Cir.1991.
[45]Lois Sportswear,U.S.A.Inc.v.Levi Strauss&Co.,799F.2d 867,230U.S.P.Q.831,2d Cir.1986.
[46]參見阮開欣:《論跨境侵犯知識產權的法律適用——以涉外定牌加工問題為出發(fā)點》,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47]參見阮開欣:《論跨境侵犯知識產權的法律適用——以涉外定牌加工問題為出發(fā)點》,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48]參見李明德:《美國知識產權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72頁。
[49]TRIPs第16條第3項規(guī)定:“在對相同貨物或服務使用相同標記的情況下,應推定存在混淆的可能性。”
[50]鄭成思:《WTO知識產權協(xié)議逐條講解》,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頁。
[51]See Vanity Fair Mills,Inc.v.T.Eaton Co.,234F.2d 633(2d Cir.1956).
[52]吳漢東:《中國知識產權法律變遷的基本面向》,載《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8期。
[53]王莉君:《全球化趨勢下我國法律發(fā)展的自主性》,載《比較法研究》2013年第4期。
[54]參見馮曉青:《知識產權法利益平衡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頁以下。
[55]在《德國商標法》第26條、《英國商標法》第46條、《意大利商標法》第42條規(guī)定“出口”行為得以維持本國注冊商標權效力之同時,《德國商標法》第14條之(3)、《英國商標法》第10條之(4)、《意大利商標法》第1條之(2)進一步規(guī)定了“出口帶有本國注冊商標標記商品的行為”構成對本國商標權的侵權。
[56]《歐共體商標條例》第9條第(2)款規(guī)定,只有商標所有人才有出口帶有注冊商標標識商品的權利。
[57]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38號民事判決書。
[58]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39號民事判決書。
[59]劉春田:《知識產權解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
[60]這方面典型的判例當屬“‘東風’商標爭議案”,具體參見劉莉:《對涉外定牌加工商標侵權認定的再思考》,載《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11期。
[61]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Intellectual Property:Principles Governing Jurisdiction,Choice of Law,and Judgments inTransnational Disputes,Proposed Final Draft(March 30,2007).
[62]Gesellschaft fur Antriebstechnik mb H&Co.KG v.Lamellen und Kupplungsbau Beteiligungs,KG Case C-4/03.
[63]李楊:《商標法基本原理》,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48頁。
[64]阮開欣:《涉外定牌加工商標侵權行為新探——以商標法域外適用為視角》,載《中華商標》2015年第12期。
[65]J.Thomas Mc Carthy,supra note 41,§ 23:104.
[66][美]弗雷德里克·M.阿伯特、[瑞士]托馬斯·科蒂爾、[澳]弗朗西斯·高銳:《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國際知識產權法(上冊)》,王清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911頁。
[67]參見[美]謝爾登·W.哈爾彭、克雷格·艾倫·納德、肯尼思·L.波特:《美國知識產權法原理》,宋慧獻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420頁以下。
[68]張新寶:《民法分則侵權責任編立法研究》,載《中國法學》2017年第3期。
[69]馬一德:《商標注冊“不良影響”條款的適用》,載《中國法學》2016年第2期。
[70][美]羅納德·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信春鷹、吳玉章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序言第2頁。
[71]吳從周:《概念法學、利益法學與價值法學:探索一部民法方法論的演變史》,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