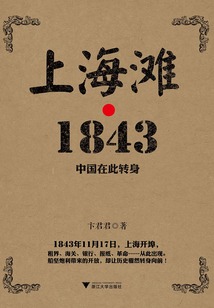
上海灘·1843
最新章節
- 第18章 后記
- 第17章 革命星火——花園里的革命吶喊
- 第16章 說“洋涇浜”——小河的滄海桑田
- 第15章 海派濫觴——東方的西方切口
- 第14章 《融合,燎原的星火》:報業繁茂——“申報紙”的大變局
- 第13章 黑幫大哥——革命“有功”的江湖
第1章 《城市的源起》:海上來“客”——注定結局的開始
上海,一座被大炮轟開的城市,為了貿易,為了這個四億人口的市場。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天未亮,黃浦江通往東海的入海口處,一個漁家孩子背著竹簍,穿過一片蘆葦坡,去茅草叢生的灘涂上挖牡蠣。顯然,這個孩子不會預知到兩百年后,他腳下這片海灘將成為一座繁華的城市,城市的名字叫——上海。
他也不知道,就在他挖牡蠣的時候,遠在千里之外的北方盛京(今沈陽)皇城內,一個和他年齡相仿的、只有五歲半的孩子被擁立為嗣皇帝。半個多月前,他的父親皇太極突然猝死,由此清王朝出現了第一位娃娃皇帝。這位小娃娃就是愛新覺羅·福臨,第二年于大政殿舉行即位大典,改元順治。
1644年,中國出現了三個皇帝,除了還是“部落首領”的愛新覺羅氏以及秉承家業的明朝崇禎皇帝之外,另外一個加入“皇榜”成員的是個農民,他叫李自成。他們三個人在當時中國的歷史舞臺上形成了三支政治力量:沒落的明、關外虎視中原的清和號令農民“造反”的大順。
從朱元璋開始,明朝歷代皇帝都有濫殺功臣、多疑吝嗇的壞毛病,崇禎的這個家族之癥已經讓整個王朝病入膏肓。抗擊清兵時,如果一個城市淪陷,就把失城的將領殺掉;一個地方淪陷,就把丟地的官員殺掉。就連戰功赫赫的袁崇煥、孫傳庭這樣的大帥也是說殺就殺,而且抄滅全家。皇帝如此苛求擅殺,怎能不讓與清兵殊死搏斗的官兵們心寒呢?吳三桂、洪承疇、耿精忠、尚可喜等,都是能征善戰的將領,前車之鑒讓他們有了事后做“漢奸”的充分理由。
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乘著晦暗天色,開始攻入北京城。19日破曉,紫禁城內的太監們在聽到攻城炮聲后早已作鳥獸散了,滿朝文武無一人來護主。親眼看著幾個老婆或跳井或上吊自殺后,絕望的崇禎皇帝踉踉蹌蹌地爬上了紫禁城后門的煤山。此時天色大亮,京城已完全陷落了。在山頂的壽皇亭,他放眼一看,只見京城內外火光沖天,四周喊殺聲陣陣傳來,炮聲隆隆作響。見此,崇禎不禁仰天長嘆,淚如雨下,想不到當年祖宗出于象征江山永固而堆筑的萬壽山,今成自己的葬身之地。隨后,崇禎在半山腰找了一棵歪脖子槐樹,解下衣帶上吊了。
據說,崇禎皇帝的死狀非常狼狽,身上只穿著白色內衣,披散著頭發,右腳穿著一只紅鞋,左腳光著。他用34歲的年齡給277年的大明王朝畫上了一個黑色句號。臨死,可憐的崇禎還哀嘆:“朕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皇帝殉國,何等悲烈!
崇禎死了,李自成的屁股也沒能捂熱紫禁城的龍椅,“一怒為紅顏”的吳山桂打開山海關迎清兵入關。清軍打出替漢族地主“報君父之仇”的旗號,滅了李自成的大順而一統中原。應該說,明朝的統治是李自成推翻的,但順治卻揀了個天大的漏,成了清朝第一位入關的皇帝。
清軍入關被很多海外學者認為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農民們用菜刀、鋤頭革了一個舊王朝的命,而滿族的鐵騎又踏下了一個新王朝。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朝換舊朝。盡管農民起義波及黃河南北,滿漢戰爭傷亡千百萬人,但中國還是封建社會,同兩千多年前的秦王朝別無二致。
與中國的農民革命、清兵入關大致相同的時間,歐洲的英國也發生了一場“革命”。從1640年英國國王查理一世召開新議會事件開始,被稱為“世界近代史開端”的資產階級革命爆發了。1649年1月30日,在英國王宮前的廣場上,查理一世的頭顱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斧頭砍落。英國資產階級的勝利,是一個歷史的新紀元。這場革命,為歐洲和世界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敲響了喪鐘,隨之一種迥別于封建社會制度的新政治制度在歐洲宣告誕生。
幾乎是同時發生的東西方兩場革命,同樣是兩個以悲劇結局的皇帝,但兩個國家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發展之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為工業革命提供了新的政治大廈,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里釋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它波及世界,震撼全球。工業革命產生的堅船利炮讓英國在大洋大海中橫沖直撞,成為18世紀世界最強大的殖民國家,號稱“日不落帝國”。我們不難設想,在皇宮廣場上處死查理一世時民眾的歡呼聲,不就是兩百年后西方叩擊中國國門的隆隆炮聲嗎?
“暴力革命”總是需要代價的,在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中,貴族與平民都把守了一個傳統底線,即尊重和維護私有財產。于是,“暴力革命”變成了一場沒有流血和犧牲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使得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制完全在英國確立下來。一百多年后,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翻版在法國上演。令人嘆息的是,中國從來沒有在法理或者制度上確立財產不容侵犯,在強勢而毫無契約觀念的政府面前,皇帝要抄你家,甚至要你死,大家都還要“謝主隆恩”。
資產階級革命改變了英國也改變了世界,但中國還在舊有的軌道上運行,盡管莊家換了,卻還是原來那副牌局。東面是大海、北面是凍土區、西面是高原、南面是島嶼,中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孤島”,在持續千年的時間內,這個“孤島”內部一直發生著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的商品交換,發達的市場、繁榮的商貿、成熟的農業……以至于被認為“14世紀時,離工業化只有一根頭發絲的距離”。然而,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專制制度,讓這個微小的距離直至鴉片戰爭爆發時的19世紀,在這長達五百年的時間都沒能跨過去。
今天的故事重復著昨天的歷史,改朝換代的船票沒有搭上駛向蔚藍色大海的資本主義客船。從此至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末代皇帝溥儀退位,愛新覺羅氏統治了華夏整整268年。以入關的數十萬人馬領導上億人口的帝國,這個看上去很像“小概率事件”的事實,讓滿人部族政權時刻保持著防止被顛覆的警覺。
1653年,已經坐穩紫禁城龍椅的順治接到一份來自廣州的“內參”報告,稱一艘荷蘭國的海船停靠在虎門港,提出要上岸通商貿易。順治從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口中得知,荷蘭是一個新崛起的西方強國,1624年擊敗西班牙獨占了臺灣島。群臣對是否與荷蘭做生意,分歧很大。于是,荷蘭人對清朝官員大肆行賄,同時游說被順治尊稱為“瑪法”(滿語中“爺爺”之意)的湯若望,希望他能在皇帝面前多說好話。
后世,有人找到了一份當時參與此事的荷蘭人信函,上面記錄:“政府官員對我們的禮品出奇地滿意,并同意向我們提供各種便利。”信中記載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湯若望見到我們把大量的禮物,特別是武器、毛毯、紅珊瑚、鏡子等眾多奇珍異品一件件擺出來的時候,他發出了一聲長長的嘆息。”1653年,順治接見了荷蘭使團,特許荷蘭國每八年到中國“朝貢”一次,每次來的人不超過100人,并只允許20個人能到京城。
對于一個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他們對海外貿易是不怎么感興趣的,在征服漢族后就視自己為天朝,不承認平等“貿易”,視他國為藩屬,連“朝貢”也只能八年一次。尤其是1661年鄭成功集團收復了臺灣島,為了切斷沿海百姓與鄭成功集團的聯系,以“騎射”得天下而水軍薄弱的清王朝只能下令海禁,規定“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甚至將沿海居民內遷30里,使靠近臺灣島的沿海邊界變成無人區。
清朝的海禁政策執行了二十多年,直到順治的兒子康熙平定“三藩”、統一臺灣之后,海商貿易才逐漸寬松。1685年,強勢、開明的康熙皇帝正式宣布開海貿易,設立粵、閩、浙、江四大海關。海關制度的建立,是中國自唐代開辟“絲綢之路”,創設“朝貢貿易”的市舶制度以來,政府首次將對外貿易的管理與經營活動分開的新貿易模式,伴隨催生的是一個迥異以往的、從事洋貨生意的商人階層。
設立海關后,外商被允許在四大海關自建商館內,自主買賣。荷蘭、美國、丹麥、英國、瑞典等國先后在廣州珠江邊自建商館,每個商館占地21英畝,年租金為600兩白銀。這批在中國土地上最早的西洋建筑群,與中國人的房屋相映,猶如一道突兀而怪異的風景。清政府對這些外商的行動進行了嚴格管制,頒布了許多限制法令,例如外商未經批準不能進廣州城、禁止外商雇用中國人做仆奴、禁止外商向中國商人放貸資金,甚至有禁止外商在廣州過冬、外商不得乘轎子等奇怪規定。外商到中國幾乎是被“圈養”起來了。
中國商人同樣需要獲得政府發放的牌照,方能與外商交易。第一批被特許從事洋貨貿易的商行共有13家,他們是政府與外商之間聯系的唯一中間人。一項廣受外商詬病的規定是:洋人有事要申訴,自己不能直接向廣州當局上告,必須通過行商向政府呈文。這顯然是極不利于維護外商利益的。為了控制價格,廣州的商人還成立公行,締結同盟,分享利益,一致對外。這個組織顯然是受到官方支持的,這種“對外統一行動、對內壟斷利益”的商業特色極像揚州“鹽商”的做法,“十三行”商人因此漸成一個組織嚴密的壟斷型商幫,與兩淮鹽商、晉陜商人一起,被后人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
廣州“十三行”牌坊明清時代崛起的粵商,與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轉型相始終,承前啟后,脈絡至今不絕。而廣州十三行行商則是清代中前期興起的粵商中獨樹一幟的勁旅,當時的英國人稱他們是“國王的商人”。明末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在《廣州竹枝詞》中描寫道:“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這反映了當時十三行地區洋船云集,外貿繁盛的情況。
1689年,一艘懸掛著英國國旗的商船駛進廣州港,與粵海關監督達成協議后,獲得登岸貿易的許可。這艘商船并沒有獨特之處,但它的到來卻是個歷史性事件,原因在于它屬于大名鼎鼎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世界企業史上,英國東印度公司是最早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之一,它在英國殖民地印度的貿易壟斷特權是經伊麗莎白一世女王特許的,是英國政府和商業利益集團的“全權代表”,最鼎盛之時,英國東印度公司控制著全球40%的貿易。
初進中國市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買賣清淡,船艙里裝滿了毛紡織品,這在天氣炎熱的廣州并不受歡迎。由于毛紡織品的滯銷、茶葉瓷器的剛性需求以及清政府的強硬,造成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相當長時間里處于貿易逆差的被動局面。除了官定稅額以外,英國人還遭到中國官員大量勒索,這在中國當然是司空見慣了,但這方面,英國人似乎不怎么習慣享受這種“國民待遇”。于是,他們試圖將貿易轉往廈門、寧波等其他港口,但發現那里的“刮地皮”勒索更厲害,只好又回到廣州。
為了打開市場,英國東印度公司一直試圖解決兩個困擾外商的難題:一是擴大對華貿易的市場港口;二是找到更能賺錢的對華商品。1715年,東印度公司在廣州城外設立了固定的商館。在隨后的近兩百年間,這家“國有參股”的巨型公司,主導了西方世界的對華貿易,并直接打破了東西方的貿易均衡,它是鴉片貿易的始作俑者,對中國和亞洲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轉眼時間到了1736年,清朝皇帝的龍袍披到了25歲的乾隆身上,經過他爺爺康熙和爸爸雍正的嘔心經營,年輕的乾隆擁有了一份殷實的家底。中國似乎有一個興旺慣例,只要社會有七十年以上的平穩期,經濟必會重獲繁榮,因此清朝也迎來了“康乾盛世”的社會繁榮期。
1743年,又一個英國“游客”從海上“漂”來。“百夫長”號船長喬治·安森帶著他疲憊不堪的船員駛入虎門港,這是史上第一艘英國籍戰艦進入中國水域。他們已經幾個星期沒有看見陸地了,船上的給養幾乎消耗殆盡,更為嚴峻的是,三分之二的船員因患敗血癥相繼死亡,如果不立即上岸補充淡水和食物,他們只有死路一條。
喬治·安森向廣州地方官員提出的申請遭到了拒絕。于是,海盜出身的喬治·安森推出震天響的火炮,威脅要擊毀駐扎在港內的中國船只,這種虛張聲勢的恐嚇竟然奏效了。百年后的1838年,約翰·巴羅在其撰寫的《安森傳記》中寫道:“由于英國戰船的新奇,由于其船長的堅定,由于明智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偶然夾雜著一些可能更有必要使用的威脅,此外還由于早就洞察了這個民族的真正特性,安森成功了。”
在炮口下,廣州的官員屈服了。他們并不知道,這種屈從或許暫時拯救了這座城市,卻玷污了中國人的聲譽,使得中國陷入了一種易被威嚇的膽小印象,最終大清王朝高高在上的地位,在歐洲人心目中喪失殆盡。
喬治·安森被允許登岸,他將海上劫得的財寶賣掉,獲得了40萬英鎊。他用這些錢采購了大量中國貨物,據說裝滿了32輛馬車之多。1744年6月15日,凱旋回到英國的喬治·安森,將戰利品放到倫敦的大街展示,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被英國皇室封為爵士,并出任海軍大臣,成為英國近代海軍改革者。
長時期“不許舢板下海”的國策,幾乎讓中國人喪失了挑戰海洋的能力和勇氣。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遠在中國北方的俄國,比康熙小12歲的年輕沙皇彼得一世,力排眾議將首都從莫斯科遷到波羅的海邊的一塊沼澤地上。日后證明這是一個偉大的決定,這座被命名為圣彼得堡的新城市,讓俄國由一個內陸國家變成了面向大海的新帝國,而彼得也以“大帝”名垂歷史。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9月,中俄在尼布楚舉行邊界談判,盡管當時清朝占理占勢,卻“戰略性”地放棄了對西伯利亞的控制權,雙方簽訂《尼布楚議界條約》,這是清政府和西方國家簽訂的近代的第一個“平等條約”。為表示慶賀,雙方還互贈禮品,舉行了盛大的宴會。清朝的這次露怯,對后世的影響深遠,并且結局相近的故事被一再重演,這是最讓后人倍感沮喪的地方。
從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再到英國人、俄國人,他們對華的姿態和貿易情況,竟成為了西方列國驗證實力的晴雨表。在許多困難之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仍然在不斷發展。這其中的原因是,雖然它向中國販賣毛紡織品一直虧本,但在茶葉貿易上賺到了不少錢,它每年進口茶葉的利潤近50%,在抵消了毛紡織品虧損之后還有26%以上的盈余率。
壟斷好辦事,這句話一點兒都沒錯。1773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又游說英國政府,使其成為英國在北美地區的利益總代理。它壟斷了北美地區的茶葉運銷,其輸入的茶葉價格低廉,使其他販賣“私茶”的商人無法生存。這件事引發了北美地區民眾的憤怒,因此爆發的“波士頓傾茶事件”成為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索。1789年4月30日,美國宣布成立聯邦政府,產自中國的茶葉竟然促發了美國的獨立。隨即英國取消了美國在英國所有殖民地范圍內享有的一切貿易優惠。
為了打破英國的經濟封鎖,擴大海外貿易,美國人決定到遠東碰碰運氣。1784年2月,一艘名為“中國皇后”號的商船從紐約港鳴鑼出發。“中國皇后”號,這是一個多么直白的向中國致敬的名字。商船橫渡大西洋,繞道好望角,再經印度洋,遠涉113萬海里歷經半年抵達廣州。船上滿載了40余噸的棉花、皮貨、胡椒等商貨,返程時裝走了數百噸的茶葉、瓷器、絲織品以及漆器等中國物品。
與歐洲人相比,美國人到中國做生意則晚了將近一百年。但他們的收益是豐盛的,返航回到美國后,船上貨物馬上被搶購一空,據稱連開國總統華盛頓也忍不住購買了一只繪有龍紋的茶壺。紐約的報紙也詳盡報道了這次神奇的航行,據估算,此次遠航船主賺了3萬美元,獲利高達15倍。那些日子里,所有美國人都在談與中國貿易的話題,廣州的英文名稱——Canton,幾乎成了財富的代名詞。
在美國并無東印度公司一類的特權機構,貿易是在平等條件下向所有人敞開的。所有人都希望能去廣州撿錢,“只要有能容納5個人的帆船,就在計劃到廣州去”。這并不是說笑,不久之后,一艘名叫“實驗”號的貨船出現在了廣州港。對于一艘噸位只有84噸就敢漂大西洋的貨船來說,美國人追求財富的冒險精神可見一斑。據統計,從“中國皇后”號開始至鴉片戰爭前夕,共計1004艘美國商船來華經商,數量僅次于“海上霸王”英國。
發生在近代歷史的中國東南沿海的商貿故事,生動地呈現出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全球化的新時代即將來襲,而它的桅桿已經在地平線的遠端露出端倪。黎明時刻來臨了,擁有巨大消費者市場;巨量的茶葉、瓷器和絲綢商品;勤懇并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商人集團;至少表面上還獲得尊重的政府……無論哪一點,都預示著東方的中國將成為這次全球化時代的最大受益者。
但悲劇的是,中國人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建造起了一個獨特的、封閉的自治社會,這一社會以農業而不是商業為基礎,由地主和官僚統治,自滿自足的社會拒絕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外貿關系。事實上,他們對外部世界毫無興趣,籠統地將歐美國家稱為“蠻夷”。即使當以千計的帆船載滿白花花的銀子叩擊緊鎖的國門時,“廣有四海”的皇帝仍然無動于衷,拒絕一切的變化。這個國家只剩下了故步自封的高傲。
顯然,美國人的“插足”以及中國政府苛刻的貿易限制,讓英國東印度公司既頭疼又憤怒。為了擴大利潤額,避開“十三行”的價格圍墻,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出一個精通漢語且能說閩南話的英國人洪仁輝(James Flint)到福建泉州和浙江寧波從事茶葉和絲綢生意,這兩個地方一個位于武夷山產茶區范圍,一個地處中國紡織業最繁華的江南且是龍井綠茶的主產地。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之外的貿易日增,影響到了廣東海關的稅收,在兩廣總督的強烈反對下,清政府把浙江海關的關稅提高了一倍,卻依然沒有有效遏制英商北上的沖動。
1757年,乾隆下詔關閉福建、浙江、江南省(轄江蘇、上海、安徽地區)三地海關,距離紫禁城最遙遠的廣州成為唯一的通商口岸。不甘心的洪仁輝給清廷寫了一份請愿書,提出多埠貿易。乾隆皇帝對蠻夷的魯莽行為十分震怒,認為這是對大清“一口通商”政策的蔑視。他下詔將洪仁輝“在澳門囚禁三年,期滿逐回本國,不許逗留生事”。洪仁輝吃牢飯,而替他代寫請愿書的中文老師則更加倒霉,被按了個“為夷商謀唆”罪名而處死了。
這種將貿易限于廣州一地、行商壟斷貿易、中外交往由行商居中轉達等對外貿易管理體制被稱為廣州體制。廣州能成為唯一通商口岸,并不是兩廣總督寫給皇帝的“內參”威力大,而是因為“偏遠”的廣州離京城遠而離南洋近,天高皇帝遠,即使出點亂子也不會影響到政府穩定。另外,皇帝心里也有本小九九賬目,廣東海關隸屬于清朝的內務府,所謂內務府就是管理皇家大小事務的總機構,是皇帝的生活秘書。換而言之,海關收入的銀子全都進了皇室的私家腰包,廣州成了“天子銀庫”。當然,十三行的行商也從廣州“一口通商”及壟斷貿易的“公行制度”中爆賺,一首當年流傳下來的《嶺南樂府·十三行》中描述道:“粵東十三家洋行,家家金珠論斗量。樓闌粉白旗竿長,樓窗懸鏡望重洋。”由此可見行商的富裕。
在廣州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廣利行、怡和行、義成行最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鑒而揚名天下。通過貿易特權,伍秉鑒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都建立了緊密的聯系,不僅在國內擁有房地產和茶園、店鋪、錢莊,還越洋到美國投資鐵路、股票和保險等業務,怡和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跨國財團。此外,伍秉鑒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有時東印度公司資金周轉不靈,經常向伍家借貸。全盛時期,伍秉鑒名下資產多達白銀1872萬兩,儼然已是世界超級富豪。2001年,伍秉鑒與比爾·蓋茨以及成吉思汗、和珅等人一起,被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評為一千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在入選的6名中國人中,伍秉鑒是唯一一個靠經商發財致富的“平民”商人。
面對如此巨大的一塊肥肉,政府官員的“紅眼病”又犯了,各種苛捐雜稅名目繁多,種種中央與地方、洋行與外商之間就海關稅費、官吏腐敗、貿易壟斷之間的紛爭與博弈,幾乎伴隨了整個十三行一百多年的外貿興衰史。
1792年9月,英王喬治三世派他的表兄馬嘎爾尼勛爵組成官方訪華使團,訪華的目的是為了說服清政府放棄或改變廣州貿易體制,“取得以往各國未能獲得的商貿利益與外交權利”。皇親國戚的馬嘎爾尼并非是泛泛之輩,他曾先后任駐俄國公使、加勒比島嶼總督和印度馬德拉斯省督,是個出色的外交官。
為了訪華成功,英國政府用了一年的時間,耗巨資采購600箱他們認為最好的禮物準備送給乾隆皇帝。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駛進廣州港的103年之后,馬嘎爾尼乘坐著英國當時最先進的配備64門巨型火炮的軍艦“獅子”號,炫耀著武力駛向中國。隨行的使團共計800多人,其中包括外交官員、地理學家、天文學家、哲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軍事學家、醫師、工程師、畫師、技師以及一支衛隊的軍官和士兵。
浩浩蕩蕩的使團艦隊繞道好望角,經過10個月的航行終于抵達舟山海域。看到一船的禮品,地方官員就認為西洋鬼子是給皇帝祝壽進貢來了。乾隆聽說人家這么遠趕來為他祝壽,也很高興,就同意馬嘎爾尼去北京見他。
嚴格意義上說,馬嘎爾尼使團的到訪是中英兩國在官方層面的第一次“非親密接觸”。盡管英國已經和中國做了一百多年的生意,可是沒有一個英國人能在這片廣袤的國土上自由行走。他們依然沉浸在《馬可·波羅游記》所描述的“世上最美、人口最多、最昌盛的王國”而讓人產生的遐想之中。然而,馬嘎爾尼使團在赴京路上的所見所聞無情地打破了他們的幻想。
當時馬嘎爾尼的助手、使團副使斯當東在日記里,詳盡記錄了他眼中的乾隆盛世境況。清政府官員強迫大批百姓來拉纖,英國人注意到這些人“都如此消瘦”,他們明顯缺衣少食,瘦弱不堪。“拉一天約有六便士的工資”,稍有怠工就會被官兵隨意鞭打,“仿佛他們就是一隊馬匹”,除了逃跑沒人反抗。在多次目睹到體罰平民的迫害后,英國人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寫道:“中國人的天性在法律和規矩的影響下所受的扭曲幾乎是徹頭徹尾的……雖然他們生性和平、順從和膽小,但社會狀況以及法律的濫用讓他們變得冷漠、麻木甚至殘酷。”清代統治者追求的是國民的順從、軟弱,甚至愚昧,其治國方式依然停留在簡單而粗暴的各種壓制手段上,而對國民的尊嚴與現代國家的開放毫無興趣。
1793年9月,在經歷一整年的旅行后,馬嘎爾尼使團從天津入境抵達承德避暑山莊。在準備拜見乾隆皇帝時,分歧產生了。清朝禮部官員要求馬嘎爾尼見中國皇帝時行三跪九叩大禮。馬嘎爾尼斷然拒絕叩拜,最后和珅出面相勸也沒有解決矛盾。多番交涉后,乾隆“大方”地沒有要求他們雙腿下跪,同意單膝下跪,唱個大諾了事,權當外夷族人沒教養不懂禮儀。
乾隆看到了英國送給他的禮物,其中包括標有世界各國位置的地球儀以及精致的鐘表、望遠鏡、氣壓計、蒸汽機、棉紡機、織布機等各種精密機械和科學儀器……此外,使團還奉送了帶有減震裝置的馬車、用特種鋼制作的刀劍和30多支當時技術領先的毛瑟槍、榴彈炮、裝備110門大炮的軍艦模型。馬嘎爾尼希望這些蘊含著即將引發世界滄桑巨變的科學技術、發現成就能“討好”乾隆皇帝和各級官員。誰知,乾隆對這些禮物幾乎是不屑一顧,更沒有人意識到這些槍炮的潛在威脅,這讓馬嘎爾尼像一個街頭遭冷落的藝人般尷尬。
最后,這些精心挑選的禮物都被當作好看的擺設陳列到圓明園里,有些甚至放了一百多年都沒有拆封,直到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北京城,又原封不動地被搶回歐洲。
除了禮沒送好,雙方在貿易通商方面也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共識。英方提出開放寧波、舟山群島、天津為新的貿易港口;申請在舟山附近擁有一個小島或一小塊空地用于存放商品;允許可長年住在廣州以及活動自由;希望中國有規定的、公開的海關稅則;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一洋行,買賣貨物;讓英國人在華自由傳教;等等。這些要求,最終都被乾隆皇帝以“與天朝體制不合”為由回絕了,連貿易要求也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讓他們卷鋪蓋回家。
京杭大運河在西方被稱為“帝國運河”,1793年秋天馬嘎爾尼使團沿運河南返之時,他們留下了大量關于運河及其沿岸社會情形的文字和圖像記錄。這些記錄一直成為鴉片戰爭前,歐洲特別是英國人了解大清帝國腹地的重要來源。英國希望直接通過與清王朝最高領導人談判,打開中國大門,開拓東方貿易市場的想法破滅了。1793年10月7日,和珅向使團交呈了乾隆的回信和回禮,馬嘎爾尼只得無奈離開北京。使團沒有從天津港上船走海路回去,而是選擇了經京杭大運河南下。他們幾乎游歷了中國沿海東部。過江蘇、渡長江、抵杭州,富庶的杭嘉湖給了馬嘎爾尼深刻印象:“上帝慷慨地將氣候、土壤和產量這些優勢毫不吝惜地賜予這個地方。在我們眼里,這個國家的長江兩岸像一個連綿不斷的大村莊,十分美麗富饒。”
旅途中,在緊靠長江,居蘇州府和杭州府兩個城市之間的位置,他們得知了一個地名:松江府上海縣。一個處于長江入海口的城鎮,那里離海不遠,盛產棉花與布匹,不但供應國內,而且遠銷國外,周邊的揚州、蘇州、杭州等城市,在商業方面都很有規模,尤其在上海縣城,來自福建的船源源不斷地駛入,另一些帆船則從那里出發到日本去做生意。這是英國官方人士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接觸上海。此時的馬嘎爾尼已經敏銳地注意到江浙沿海地區的通商價值,以及上海地區在中國的重要地位。
1793年11月9日,使團來到了《馬可·波羅游記》中譽為“天堂之城”的杭州,在這個“世界最美麗華貴之城”,馬嘎爾尼記錄到:“城市周圍非常美麗,鑲嵌著一個巨大的湖泊,依傍著一條大運河,還有大大小小的河道,并不陡峭的山丘一直耕種到山頂。桑葚園、低矮的果樹點綴其間,橡樹、水榆、樟腦樹華蓋遮天。”
一個月后,馬嘎爾尼使團回到廣州,又在澳門停留了3個月。1794年3月17日,帶著乾隆回贈英王的禮物,馬嘎爾尼心情抑郁地返回倫敦。耗資巨大的外交徹底失敗,讓英國當局非常尷尬,碰了一鼻子灰的馬嘎爾尼,作為使者更是顏面盡失。他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憤憤評論道:“中國自滿洲韃靼占領以來,至少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里沒有進步,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
馬嘎爾尼使團的中國之行成為了中外交往史上的分水嶺,此后批評中國成為歐洲中國觀的主旋律且延續至今。其實英國使團并非毫無收獲,他們在華逗留期間,收集了大量政治、經濟、軍事情報:中國并不富足,窮人很多;國家既沒有嚴格的法律制度,也沒有合理的審判制度;官員貪贓枉法、徇私舞弊;清兵的裝備雖然有火槍和大炮,但海防的炮臺與士兵簡直是擺設,大炮不但射程近而且還不能瞄準、不能升降……這些見聞、筆記和圖畫資料被整理出版廣泛傳播。
在詳細而深入了解中國之后,馬嘎爾尼留下了一番經典的論述:“中國只是一艘破爛不堪的舊船,它之所以在一百五十年間沒有沉沒,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它使周圍領船害怕的地方,不過是那巨大的軀殼,一旦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和安全就都完了……船將不會立即沉沒,它將像一個殘骸那樣到處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它將永遠不能修復。”這種當時看來頗為荒誕的預言,在經歷了百年風云變幻后,才不被視作無稽之談。
這是“兩個文明的沖突”,美國著名國際政治理論家塞繆爾·亨廷頓說過,每一個文明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歷史當做人類歷史主要的戲劇性場面來撰寫。歷史總是充滿了戲劇性,英格蘭人與滿洲人,這兩個地處世界兩端的民族,一個擊敗了西歐強國主宰著海洋,一個統一了東亞廣袤的腹地,自詡為天朝上國主宰大陸。他們在千年大變局時代相遇了,他們都盛氣凌人,都認為自己是世界的霸主,都試圖處于領導地位,將自己的觀念準則強加給對方,于是,這種接觸的失敗是必然的。
又過了二十三年,1816年英國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再次派遣由阿美士德伯爵率領的使團出使中國。這次出使的目的,與當年馬嘎爾尼的要求如出一轍,要求清政府放松對商貿活動的管制。此時,嘉慶皇帝已經接替了乾隆的皇位,喜怒無常的嘉慶比他父親做得更絕,不僅禮物全部退還,甚至連面也不見就把英使團“勸”回老家了。其中,有兩個很小的細節值得一提,一個是盡管訪華失敗,但這位阿美士德后來當上了印度總督,光榮隱退,日后,“阿美士德”這個名字將成為造成上海灘“堤壩決口”的第一只螞蟻;另外一個是訪華團的副使,是當年記錄游記的斯當東的兒子。前后兩輩人的際遇,恍若一個故事的兩個翻版。
又過了二十多年,當英國議會以投票決定是否與中國開戰的時候,兩鬢斑白的小斯當東毫不猶豫投下了贊成票,他認為:中國人聽不懂自由貿易的語言,只聽得懂炮艦的語言。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
上海,這座新矗立而起的海邊城市,被鴉片侵蝕出一個血腥的缺口,那些從海上呼嘯而來的艦船,猶如螞蝗一樣從這個撕開的口子,貪婪地吮吸中國的“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