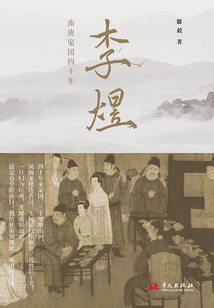
李煜:南唐家國四十年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三十年來夢一場
出生便是帝王家
楊吳天祚三年(937),七夕,金陵,齊王府,一個男嬰呱呱墜地。他就是后來成為南唐國主,被稱為李后主的李煜。按照中國史書的習慣,著名人物往往都自帶光環登場,要么是夜夢天神、紅日入懷、異香滿室等祥瑞之兆,傳說宋太祖趙匡胤出生時紅光滿屋;要么就是長相讓人過目不忘,比如蜀漢先祖劉備不僅耳朵大,兩手下垂的時候還能超過膝蓋。
李煜也不例外,史書記載他是“重瞳”,即有兩個瞳孔。盡管用現代醫學來看,“重瞳”是一種眼科疾病,但在古代,卻被認為是富貴之相。歷史上有記載的“重瞳”只有六個人:倉頡、舜、重耳、項羽、高洋、李煜。每一個都是響當當的人物,倉頡造漢字;舜,三皇五帝之一;重耳即晉文公(春秋五霸之一);項羽乃西楚霸王;高洋是北齊皇帝。至于李煜,中國古代文學有兩大巔峰,唐詩宋詞,他就是宋詞輝煌的先聲。雖然他后來不幸成為亡國之君,但文壇地位難以撼動。
盡管自帶光環,但跟他后來傳奇且悲劇的命運相比,他的出生,并不引人注目。這一年政治舞臺上最耀眼、最傳奇的人,是他的爺爺,南唐開國皇帝——李昪。李昪當時的名字仍叫徐知誥,一身兼任吳國太師、大元帥、齊王,名義上的皇帝楊溥,不過是任他擺布的一個傀儡而已。徐知誥八歲的時候,還不過是一個寄人籬下的孤兒,如今距離皇帝之位僅剩下一步之遙。
當年正月,徐知誥下令建造太廟、社稷壇,改牙城為宮城,任命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并設置文武百官。三月,他立長子徐景通——李璟(即李煜的父親)為王太子。金陵城內,大街小巷到處都聽到兒童們傳唱童謠“東海鯉魚飛上天”,有人私下解釋,“東海”是齊王徐知誥的爵名,即東海郡王,“鯉魚”上天就是要成龍當皇帝,意思就是徐知誥要當皇帝。
不久之后,有天夜里,金陵城內突然響起鐘聲,很多老百姓從睡夢中被驚醒,以為發生了什么大事,紛紛惶恐不安。第二天一大早,就聽說敲鐘的人被抓到了,還是個老和尚。老百姓紛紛去衙門圍觀。徐知誥本人親自組織公審,老和尚在公堂之上一點也不緊張,解釋道:“不是故意吵醒各位,只是因為突然想到一首好詩,激動得睡不著,只好敲鐘抒發一下心中的喜悅。”這下大家的胃口都吊起來了,什么好詩值得如此興奮?
老和尚不慌不忙緩緩吟來:
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
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徐知誥聽完之后笑道,“好詩好詩,恕你無罪”,不僅當場釋放了和尚,還重賞了一大筆錢。大部分圍觀群眾目瞪口呆,表示一頭霧水的時候,腦袋機靈的已經反應過來,“徐徐東海出,漸漸入天衢”,不就是應和“東海鯉魚飛上天”的讖言,暗示徐太師要當皇帝嘛。
輿論都造成這樣,再看不出來就是真傻了。徐知誥的心腹們心領神會,紛紛上書請求他趕快稱帝。吳國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一把年紀,牙齒都掉光了,還拖著病體入宮勸說傀儡皇帝楊溥禪位。孤家寡人的楊溥無計可施,整天嘀咕,“吳國的國祚到頭了”,身邊人只得寬慰他,“國家氣數已盡,這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改變”。
鎮南軍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趕到金陵,率領百官聯署,勸徐知誥不負眾望,上順天意,下體民意,早點接受禪位。由古至今,世界上最不費力的,就是錦上添花,一片勸進聲中,號稱山林隱士的沈彬也不甘寂寞,主動獻上《觀畫山水圖》,并題詩曰:
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
這一年年初,石敬瑭從洛陽遷都到開封。前一年年末,后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依靠契丹軍隊的支持,起兵造反成功,當上了皇帝,建立起五代當中第三個王朝——晉,史稱后晉,并改年號為天福元年。他付出的代價是向比自己小十歲的契丹國主耶律德光稱“父”和割讓“幽云十六州”。前者讓他成為臭名昭著的“兒皇帝”,后者使得中原王朝失去保護河北平原的地理屏障,此后在與北方勢力交手時總是淪為下風,收復“幽云十六州”成為中原王朝念念不忘的心病。
跟隨石敬瑭車駕前往開封的,不僅有朝廷文武百官、后宮嬪妃,還有禁軍將領趙弘殷和他十歲的兒子——趙匡胤。金陵到開封距離差不多六百一十公里,今天坐高鐵最快只要四個多小時,但在南唐升元元年(937),卻分別屬于兩個國家。如果一切按部就班的話,李煜和趙匡胤兩人的人生之路幾乎沒有懸念,也不會有任何交集:李煜出生就是帝王家庭,一生錦衣玉食,詩酒年華;趙匡胤將會子承父業,成為五代亂世中的一名職業軍人,征戰四方刀口舔血。
但他們所生活的十世紀,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確定。
這是一個王冠墜地、等級崩解的時代,也是一個草根逆襲、平步青云的時代。面對權力的誘惑,忠誠變得廉價,親情蕩然無存,王朝國度更迭無常,皇帝成為高危職業。從朱溫弒殺唐朝末代皇帝開始,走馬燈一樣換了多個皇帝,每個朝代頂多只能傳兩代人,最短的皇帝在位半年不到,最長的在位十年,平均下來,每個皇帝在位時間不到五年。
李煜出生這一年,距離唐朝滅亡已有整整三十年,原先的唐朝疆域內,分布著若干個大大小小的國家。這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大分裂的時期,即“五代十國”。《水滸傳》開篇有一首詩,“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說的就是這段時代,“五代”即中原依次出現的五個王朝,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十國”,即先后出現的十個地方性割據小國,即吳、南唐、吳越、楚、前蜀、后蜀、南漢、南平(荊南)、閩、北漢。
江湖不問由頭,英雄不問出處。這些國家的建立者,大都來自社會底層。伴隨著唐朝的崩潰,憑靠世家大族出身或是讀書入仕改變命運的通道,都不得不讓位給武力,讓草莽英雄們找到了出人頭地的機會。不管出身如何,農民還是馬賊,只要手頭有兵,就能稱帝稱王,所謂“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寧有種耶?”
譬如吳王楊行密,早年是山賊;閩王王審知是河南農民;吳越國王錢镠年輕的時候,靠販賣私鹽為生;楚王馬殷,第一份工作是木匠。當然,還有曾經在寺廟寄食的孤兒徐知誥。
這一切,要從一場相遇說起。
別人家的孩子
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斗,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即使已經過去近四十年的時光,當徐知誥坐在龍椅上,看著眼前彎腰肅立的文武百官時,依舊能想起他六歲那年第一次見到楊行密的那個清晨。當時的他,是一個被濠州開元寺僧人收留的孤兒,靠著僧人的施舍,過著饑一頓飽一頓的日子,完全沒有任何未來可言。
灰暗且絕望的人生,在他見到楊行密后戛然而止。一個是六歲的孤兒,一個是手握重兵的大唐淮南節度使,兩個人的生命軌跡在這一刻相遇。過了這個下午,徐知誥的命運將因為眼前這個人而發生神奇的轉變。
徐知誥,原本姓李,徐州彭城人,生于唐僖宗文德元年(889)。那時的大唐王朝日薄西山,各個藩鎮不關心民生,整天忙著打仗兼并。皇帝的政令不出大明宮,“自國門以外,皆分裂于方鎮矣”,朝廷對這些飛揚跋扈的割據勢力束手無策,普通的老百姓如同螻蟻一般生活。
他六歲這年,朱溫率軍進攻徐州,父親李榮在戰亂中不知所終。年幼的小李,跟隨伯父李球、母親劉氏一起逃難到濠州,伯父、母親相繼病故后,只得棲身濠州開元寺,像很多孤兒一樣,在亂世中艱難茍活下去。
唐昭宗乾寧二年(895),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攻取濠州,在當地名剎開元寺拜佛的時候,偶然發現了小李。楊行密注意到這個小男孩不僅相貌奇特,而且質樸聰明,滿心喜歡,決定將他帶回家中收作養子。濠州就是今天的鳳陽,三百多年后,有一個叫朱重八的人也在鳳陽城西南鳳凰山日精峰下的於皇寺出家為僧,后來改名朱元璋,成為明朝的開國皇帝。濠州的兩座寺廟,先后走出兩個皇帝,也算是中國歷史之最。
小李被楊行密帶回揚州后,并沒能進入楊行密的家門,因為楊家人尤其是楊行密的長子楊渥看不起這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不屑與他兄弟相稱。楊行密沒辦法,只好把他托付給了徐溫,說,“這個小孩相貌不同于常人,將來必定大有出息,可惜我的兒子不能容他,只好托付給你。”從事后的發展看,這次小小的意外,應該是命運女神再一次地垂青于他。如果真的成了楊行密的養子,小李或許永遠不可能寫下自己的傳奇。
徐溫當初也是私鹽販子,雖然沒什么武藝,不能沖鋒陷陣,但卻很有謀略,在以草莽好漢為主要構成的楊行密團隊中,顯得頗有遠見。當初楊行密攻克宣州后,所有部下都忙著搶劫金銀財寶,只有他去開倉放糧,賑濟老百姓。徐溫資歷老(楊行密創業團隊“三十六英雄”之一),又不掌握軍隊(“未嘗有戰功”),從古至今這種下屬最讓人放心。楊行密任命他為衙內右直都將、左長劍都虞候,掌握侍衛親軍,保護楊行密及家人安全。
就這樣,小李轉而被徐溫收養,并改姓為徐,名知誥。晚唐五代是中國歷史上收養義子風氣最盛的時期,豪強們有三五個義子可以說是司空見慣,比如晉王李克用手下的“十三太保”,就全部是義子。收養義子最多的是前蜀皇帝王建,相傳有120人,其中有名有姓的有40多人。這種風俗最早起源于胡漢雜居的河朔地區,后來逐漸成為亂世中一種壯大實力和培養心腹的手段。小李變成小徐的同時,楊行密的事業也正處于一個急速上升期。
唐昭宗乾寧二年(895),楊行密被唐朝廷拜為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包括揚州、潤州(鎮江)在內的淮河以南、長江以東各州都成為其勢力范圍。唐代中葉以后,朝廷的生存基本依賴淮南等東南八道的賦稅收入,所謂“國家用度盡仰江淮,若漕運阻絕不通,則上下皆無以供給”。潤州是江河交匯處,大運河在這里穿城而過,匯入長江,來自江南的糧食都在這里集中,再從北岸的揚州伸向華北腹地。掌控大唐經濟命脈的楊行密很快就成為各方勢力覬覦的對象。
兩年后,中原地區最大的軍閥朱溫派遣大將葛從周、龐師古統率大軍分兵兩路南下進攻淮南,結果慘敗,龐師古戰死,出發時七萬人的大軍,最終活著逃回開封的不足一千。戰事結束后,楊行密寫了一封信給朱溫,信中用輕蔑的口氣說,“龐師古、葛從周太差了,你自己帶兵來跟我決戰還差不多。”
擊敗朱溫后,楊行密聲勢大振,不僅守穩了淮南的基本盤,還向東攻占了蘇州、常州,又出兵向西奪取光州、黃州、蘄州、鄂州,此后又多次擊敗朱溫,成為阻擋其南下的定海神針。朱溫及其后繼政權既不能奪取淮南,也就意味著失去了統一天下的財力物力,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也就只能繼續維持下去,直到后來有人能打破這個平衡為止。
在被收養后,已經改名徐知誥的小李,終于不用再擔心餓肚子。但他很快發現,自己又轉而陷入了一種比餓肚子還要緊張的人生。和所有寄人籬下的人一樣,小李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時時察言觀色,生怕討別人不開心,或擔心做錯什么事情。他除了要無微不至地侍奉養父母,還要處理好和他們親生兒子之間的關系。
九歲那年的一天傍晚,徐溫讓他掌燈時,他隨口吟成詠燈詩:
一點分明值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
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
明著講燈,實則希望養父像對燈一樣善待自己,一個九歲的小孩能寫出這樣語帶雙關的詩,著實讓徐溫刮目相看。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徐溫此后果然更加用心栽培這個送上門來的孩子。隨著年歲漸長,徐知誥也確實沒讓徐溫感到一絲失望和不滿。有一次,徐溫得了重病,徐知誥和妻子王氏不眠不休在床邊照理。徐溫不管何時從昏睡中醒來,只有徐知誥夫婦坐在身邊服侍。徐溫讓他管理府中事務,不僅各項事情處理得井井有條,而且任勞任怨,經常加班加點,闔府上下沒有人不說他好話。
史書上說,徐知誥長得高大威猛,寬額高鼻,儀表堂堂,“及長,身七尺,方顙隆準,修上短下,語聲如鐘,精彩鑠人”,不僅喜歡讀書射箭,走起路來龍行虎步。在養父徐溫眼中,他就是傳說中“別人家的孩子”,以至于他教育兒子們時,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們做事能像徐知誥一樣嗎?”
孤兒當上了皇帝
歷史學家柏楊在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王朝更替的時候,提出過“柏楊瓶頸”:即每個朝代的建立都有瓶頸危機,就像瓶子一樣,當一個王朝傳位到第二代或第三代繼承人的時候,就處在瓶頸時期。出現危機的原因很多,大多數是因為王朝剛剛建立,需要時間積累威信,新政施行也需要時間驗證,人事布局還未穩定,再加上皇帝本身的領導才能未臻成熟,出現任何稍大的震動都會使新政權倒塌。
唐昭宗天復二年(902),楊行密被唐昭宗封為吳王,官拜東面諸道行營都統、中書令,因為國主姓楊,為了區別三國時期的孫吳,又被叫作楊吳。唐哀帝天祐二年(905),楊行密病死于揚州,時年五十三歲。今天從合肥出城往北開車六十里路,有一個叫吳山鎮的地方,鎮子的西北郊坐落著一座古色古香的小廟——吳王廟,廟背后就是楊行密的陵墓——興陵所在,當地人將這座小山一樣的陵墓稱之為“吳山”。楊行密當過農民、當過兵,參加過叛亂,有勇有謀,一生當中幾乎從沒打過敗仗。他死的時候,吳國已經成為南方實力最強、面積最大的割據政權,假如老天讓他多活幾年的話,五代十國或許是另外一個走向也未可知。
楊行密死后,楊吳政權很快就遭遇了柏楊所說的“瓶頸危機”。他的兒子楊渥不僅欺凌蔑視父親的一幫老部下,還試圖剝奪他們的權力。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左右牙指揮使張灝、徐溫發動兵變控制楊渥。第二年,張灝、徐溫合謀殺害楊渥。不久之后,徐溫又誅殺張灝,扶持楊行密的次子楊隆演繼位。此后,國中大權逐漸被徐溫所掌控。
楊吳天祐六年(909),徐溫決定物色一個人去治理升州(今江蘇南京)并訓練水師,他自己則繼續留在廣陵(今江蘇揚州)控制朝政。徐溫之所以經營升州,不僅是看中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內心深處還有一個想法,就是在廣陵之外,營建一個屬于自己的根據地。徐溫雖然名列楊行密三十六兄弟,但排名卻是最后一位。楊行密時期的很多老臣宿將仍在,對他獨攬大權心存不滿,盡管已經制服劉威、陶雅、李遇等老兄弟,其他人仍然讓他不得不暗自提防。隨著徐溫的權力越來越大,迫切需要的,就是一個值得信任且有能力的班底。這個時候,“別人家的孩子”徐知誥自然就進入了徐溫的視野。
楊吳天祐六年三月,徐知誥被任命為升州刺史,這一年,他才二十歲。很多人在這個年齡,還沒機會進入官場,而他起步就已經很高了。徐知誥此時還不知道的是,他和他的家族,將和南京這個城市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此時的升州早已沒有六朝時的恢弘,隋開皇九年(589),隋朝大將韓擒虎率軍攻克建康(今江蘇南京)后,隋文帝楊堅為了永絕后患,下詔“平蕩墾耕”城邑宮室,昔日富麗堂皇的六朝宮城、府第名園、亭臺樓閣全部被夷為平地,辟作農田,供百姓耕種,數百年繁華剎那間煙消云散。
對于優秀的人來說,只怕你不給他平臺,一旦有了平臺,就如魚得水。徐知誥到任之后,就專心經營升州,并盡心恢復。當時的地方官大多都是職業軍人,尤其擅長橫征暴斂,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徐知誥經營升州時,一切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僅勤奮好學、敬重文人,自己也很注重勤儉節約,執政非常寬容仁愛,老百姓提到他,都豎起大拇指。作為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經過徐知誥的精心經營,昔日破敗的升州逐漸恢復了六朝時的風采。徐知誥主持的城建工程從楊吳天祐六年開始動工,一直到楊吳武義二年(920)最后完工,前后花了十多年。徐知誥不僅手筆很大,規劃也充滿了先見之明,不僅整體南移城市,改變了六朝建康城只包容宮殿衙署的舊格局,還把石頭城及秦淮河下游兩岸最為繁盛的商業區及人口集中的富庶區全部劃入城內。令人稱嘆的是,徐知誥在規劃道路建設時,不僅路面鋪磚,道路兩側還開排水溝,并雜植槐樹、柳樹作為行道樹,簡直引領時代之先。
修繕后的城墻周長達到十二余公里,基闊三丈五尺,頂寬二丈五尺,高二丈五尺,開城門八座,除東西南北四個城門外,另外開辟上水門、下水門、柵寨門、龍光門。后來北宋的江寧府、南宋的建康府、元朝的集慶路(今江蘇南京)都是以徐知誥規劃的升州城為治所所在。元朝末年,朱元璋攻克集慶路,并改名為應天府,此后在這里稱帝,并再次擴建成為明代都城,其實最初的藍本都來自徐知誥。楊吳天祐十二年(915),徐溫被吳王任命為管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兼侍中,封齊國公,并總領升、潤、常、宣、歙、池六州之地。他起初在潤州建立霸府,來升州巡視時,驚喜地發現徐知誥治理下的升州市面繁華、府庫充實,頓時決定搶為己有。不久,徐溫把長子徐知訓留在廣陵,一則監視吳王楊隆演,二來鍛煉行政能力,自己則移鎮升州遙控朝政,并將其改名為金陵。
楊吳天祐十二年,徐溫任命長子徐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和內外馬步都軍副使,不久,又擢升為吳國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在這期間,徐知誥被從升州調到潤州(今江蘇鎮江)為團練使。一個在朝廷中樞,一個在地方轉圈,這就像是一個家族企業,外人再有能力也只能做到高管,自家兒子水平再差也是作為接班人來培養。徐知誥再吃苦再努力,待遇和親生兒子還是不一樣。可惜虎父犬子,楊行密和徐溫都是一時豪杰,生的兒子卻是競相比爛。
傳說中的“坑爹”往往具備的特征就是:喜歡惹事,也敢惹事,只是惹事后,自己的能力解決不了。這種人,通常都存在智力、能力上的缺陷。按照這個標準來看,徐知訓簡直就是一個“坑爹”的典型。徐知誥在升州廣收人心培養班底,獲得了朝廷內外一致好評。徐溫給了徐知訓最好的平臺,指望他繼承基業,他卻把從上到下的所有人得罪了一遍,最終把自己送上不歸路。
他在廣陵正事不干,整天以凌辱吳王楊隆演為樂。兩人一起演戲,徐知訓自己扮演主角,吳王扮演僮奴,頭發扎兩個丫角,穿個破舊衣服當跟班。還有一次,徐知訓和楊隆演一起到禪智寺賞花,徐知訓酒喝高了,就開始臭罵楊隆演,直到把楊隆演都罵哭了,還是喋喋不休。楊隆演的左右隨從擔心徐知訓情緒失控,想偷偷帶楊隆演離開。沒想到徐知訓更加惱羞成怒,拿起鐵錘當場砸死了楊隆演的一名親信。楊隆演被嚇得呆若木雞,一動不動,徐知訓這才罵罵咧咧地回家睡覺去了。
李德誠是最早跟隨楊行密的老部下,時任撫州刺史,徐知訓聽說他家的女伎才色雙全,就跟他討要。李德誠婉拒了徐知訓,說他家的女伎都是既老又丑,實在不配侍候貴人。徐知訓看信后破口大罵,說李德誠連幾個家伎都不肯給,分明是瞧不起他,發狠要殺了李德誠,連同他的妻室一同奪過來。李德誠趕緊花重金買了幾個美女送往廣陵,才把這件事擺平。
徐溫經常夸徐知誥能干,導致徐知訓更加嫉恨徐知誥。有一次,徐知訓召集幾個兄弟喝酒,徐知誥因故沒參加,徐知訓大發雷霆,揚言道,“討飯的家伙不想喝我的酒,難道是想試試我的劍嗎?”
不過徐知誥是一個善于隱忍的人,歷來欲成大事者,大都懂得隱忍,亦懂得什么時候才是最好的時機,特別是實力不如對手的時候。徐知訓此后幾次三番想暗殺他,他都選擇了息事寧人。惡人自有惡人報,徐知訓很快就碰到了命中的克星。
朱瑾是淮南名將,有萬夫不當之勇,其雄武倜儻,有吞噬四方之志,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威震中原。他成為唐朝冊封的泰寧軍節度使時,徐溫還只是一個私鹽販子而已。楊行密之所以能建立吳國,有一大半的功勞來自朱瑾。徐知訓年幼的時候跟著朱瑾學習兵法,倆人有師生之誼。楊吳天祐十三年(916),宿衛將李球、馬謙挾持吳王楊隆演,以勤王的名義發動兵變,召集庫兵討伐徐知訓,幾乎攻破宮門。朱瑾正好從潤州來到揚州,順手率部擊潰亂兵,不費吹灰之力便擒斬李球、馬謙,救了徐知訓一命。
可就是這樣一個救命恩人加師生之誼的長輩,徐知訓也要往死里得罪。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大概就是徐知訓的人生信條。他聽人說朱瑾有匹名馬,大咧咧地開口就要,朱瑾很不客氣地拒絕了他,心想“我在中原爭奪天下的時候,你還在穿開襠褲呢”。沒想到徐知訓遭到拒絕之后,竟然派刺客去刺殺朱瑾。結果朱瑾三下五除二把刺客都團滅了。事后朱瑾也沒聲張,就當沒有發生。
按理說,這事到此為止也就罷了。然而徐知訓這種坑爹貨永遠不知道“挫折”二字怎么寫,他就是屬于那種根本沒有腦子,能力二流不到,偏偏特能惹事的奇葩。“我打不過你,可是我的官比你大”,他到徐溫那里打小報告,并強迫吳王在泗州設置靜淮軍,然后下詔把朱瑾外放過去擔任節度使。五代十國時期,突然外放很有可能就是死刑命令的前奏。后梁太祖朱溫就是在任命次子朱友珪為萊州刺史之后,被后者反過來弒殺。熟知歷史的朱瑾到此時終于明白,寧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徐知訓是決心要他的命了。
楊隆演是傀儡,徐知誥是養子,李德誠是地方官,都只能讓著徐知訓。朱瑾不是這樣的人,武人的血液依舊在身體里燃燒,既然忍無可忍,無法再忍,不如先下手為強。相比于徐知誥在金陵的表現,徐知訓完全沒有一點點政治手腕可言。他甚至嗅不到空氣中危險的味道,殺心已下的朱瑾為他擺下了有去無回的鴻門宴,他卻依舊欣然赴宴。楊吳天祐十五年(918),朱瑾以臨別贈送寶馬為由,邀請徐知訓來家中赴宴,席間趁其不注意,將其當場擊殺。
人貴在有自知之明,庸人缺乏的,恰恰是自知之明。可以說,正是徐知訓這種四處咬人的瘋狗性格,決定了他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江湖兇險,更不知道進退的行事風格。這種做人風格發展到最后,要么自己丟人失份兒,要么喪失回旋的余地,直接被人一刀反殺出局。
徐知訓帶來的家仆聽說主人被殺,嚇得一哄而散回去報信。朱瑾割下徐知訓的首級,隨即來到吳王府,找到楊隆演說,“我今天為國去賊,為民除害”,希望楊隆演抓住機會振作一把,里應外合鏟除徐溫勢力。所謂“賊”是竊國,“害”是蠹民,朱瑾連口號都代楊隆演設計好了。此時徐溫人在升州,徐知誥在潤州(今江蘇鎮江),吳王只要登高一呼,未必不能趁機鏟除徐溫在廣陵的勢力,利用長江天塹,接管揚州的控制權,營造既成事實。
可惜機遇只適用于勇敢的人,楊隆演看到徐知訓的人頭,嚇得魂不附體,用衣服遮住自己的臉,顫抖地說:“這事是你干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朱瑾氣得暴跳如雷,“婢女生的兒子果然不足共事”,將徐知訓頭顱狠狠地拋在地上。此時徐知訓的親兵接到消息已經追殺到了吳王宮城門外。朱瑾勢單力薄,只好翻墻而逃,結果不小心摔斷了腿。眼看追兵將至,朱瑾長嘆一聲,“我一人做事一人當”,便揮劍自刎了。
徐知訓的死亡,意外導致了吳國中樞的權力真空。關鍵時刻,徐知誥之前暗插的心腹馬仁裕,第一時間把消息傳到潤州。徐知誥迅速以討平叛賊為名率兵渡江,搶在徐溫之前進入廣陵,控制朝局造成了既成事實。當徐溫來到廣陵時,盡管一切已經塵埃落定,但長期栽培的長子意外被殺,還是讓他決定大開殺戒,誅戮所謂的朱瑾同黨。徐知誥趕緊勸阻,并且羅列了徐知訓欺凌吳王、臣僚的種種言行,徐溫這才稍微平息怒氣,所有幸免于難的人內心感激徐知誥。
與此同時,徐知誥還給徐溫設了一個局。徐知訓的府中有一個密室,徐知誥直等到徐溫來后,才帶他去當面開啟,結果發現里面做的是徐溫等人的木偶,而且都被用刑具捆得結結實實,尤其是徐知誥等兄弟還被設計成被斬首的模樣。徐溫看了之后,氣得大罵,“這條狗死晚了”。這個密室之前從沒打開,徐知誥還很有先見之明似的請徐溫先看,恰好里面還是證明徐知訓罪惡的證據,這就很讓人遐想徐知誥在其中的作用,畢竟徐知訓是長子,一切都是靠徐溫的庇蔭,并沒有太多的理由要這么做。
不管如何,徐知訓的死還是深深刺激到了徐溫,此后直到死,他再也沒有邁出篡位這一步。他提拔二兒子徐知詢,同時又不肯采取嚴可求的建議除去已經勢大的徐知誥。道理他不是不懂,但同時代那么多活生生的例子就擺在那里,無論長子,還是次子,能力都不如徐知誥。自古至今,硬把能力不行的人推上重要的位置,不僅害人,也必將害他自己。徐溫的最后十年是在彷徨、苦悶和聽天由命中度過的。
盡管吳國徹底變成了徐家天下,楊家只是象征意義,有人勸他干脆取而代之,徐溫回答說,“當初先王(楊行密)臨終前本想傳位給劉威,是我極力反對,才傳位給烈祖(楊渥),當時先王在病榻上就落淚了,如今我如何忍心做這種事情”。楊吳順義七年(927)十月,吳國大丞相、東海郡王徐溫去世,壽六十六歲。此時,他的頭上已經有七個頭銜,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和曹操、高歡、宇文泰等一樣,他始終以權臣自居,完成了對楊行密的承諾。
徐溫如果篡位,可以把帝位順理成章地傳給親生兒子。但他并沒有,所以權力再大也不過是個權臣,當他死后,新一輪的爭斗就開始了。徐溫死后不過九天,他的親生次子徐知詢就繼為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輔國大將軍,檢校太尉,守中書令,金陵尹,以控制吳國上游。徐溫盡管容忍了徐知誥的存在,但也給徐知詢留下了足以自保的底牌。畢竟徐溫已經經營金陵多年,不僅城市地理位置重要,還有大批忠心的部下。
不過徐知詢同樣是個不學無術的紈绔子弟,當初徐知詢在宣城為官的時候,聚斂苛暴,老百姓被折磨得苦不堪言。據說他有一次進宮侍宴的時候,席間上演優伶戲,有個伶人假扮鬼神,旁邊就有一人問:“你是誰”。答:“我是宣州的土地神,因為父母官進京,把我跟地皮一起刮來了。”“刮地皮”的典故就是由此而來,徐知詢的官聲之差可見一斑。不僅如此,史書中說徐知詢不僅懦弱、缺乏遠見,而且待弟弟們很薄情,因此幾個弟弟都跟他離心離德,向著沒有血緣關系的徐知誥。這樣的人很快就被徐知誥斗敗,被遠遠地打發到洪州(今江西南昌),封東海郡王。楊吳大和六年(934),徐知詢在郁郁寡歡中病死。
多年前,徐溫跟楊行密夸徐知誥,意思就是這孩子英俊杰出,其他人的孩子都比不上他,結果真的是一語成讖。徐氏父子消失后,再也沒人能夠阻擋徐知誥稱帝的步伐。楊吳順義七年十一月,也就是徐溫去世一個月后,在徐知誥的策劃下,吳王楊溥正式稱帝,追尊歷代帝后,大赦,改元。從吳王到吳帝,楊溥依然改變不了“工具人”的身份。他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不停地給徐知誥加官晉爵,為他在權力之路上不停地鋪磚,直到無限靠近皇位那天。楊吳大和六年(934)十月,吳國皇帝楊溥下詔封徐知誥為大丞相、尚父,嗣齊王,賜九錫。楊吳大和七年(935)十月,楊溥下詔封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天下兵馬大元帥、齊王,以升、潤等十個州為齊國。徐知誥裝作誠惶誠恐,推辭不受。
楊吳天祚二年(936)正月,徐知誥在金陵建立大元帥府,設六部,長子李璟為太尉、副元帥。同在南方的閩國、南漢等國都遣使者前來,勸徐知誥稱帝。不久,徐知誥改名徐誥,“知”字去掉了,等于告訴天下:我和徐溫的兒子們,不再是兄弟關系。
南唐升元元年(937),十月初五,李煜快滿百天的時候,徐誥連續推辭三次后,終于“勉為其難”即皇帝位,改年號為升元,同時改金陵為江寧府。因為他的爵位是齊王,所以新王朝的國號為齊。以開國皇帝的封爵作為新王朝的國號,是元朝以前的慣例,如劉邦是漢王、曹丕是魏王,李淵是唐國公等。
徐誥即位后,給禪位的前皇帝楊溥賜了一個尊號:“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感謝吳帝讓出皇位的高風亮節,不過這只是一個安撫人心的花招罷了,被篡位的皇帝能保住性命的都沒幾個,哪能繼續住在皇宮。楊溥是個聰明人,主動請求皇帝讓自己搬家。
南唐升元二年(938)五月,楊吳最后一個皇帝——楊溥,按照徐誥的旨意,從廣陵崇德宮遷居到潤州丹陽宮。揚州到鎮江一江之隔,登船之前,楊溥潸然淚下,吟詩一首:
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
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
云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
此時還不滿周歲的李煜并不知道,這首詩因為太過凄涼,和幾十年后他的境遇又太過相似,以至于之后的很多人都忘記了原先的作者,誤以為是李煜所寫。
不過當時無論是誰,都不可能想到,李煜未來會成為南唐的帝位繼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