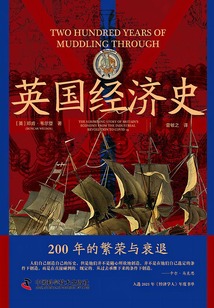
英國經濟史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引言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1]
——卡爾·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有一個非常著名也是非常古老的愛爾蘭笑話,講的是一個人被游客問路,他回答道:“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從這里出發。”這個笑話可能并不會讓人哄堂大笑,但是它用更簡練的方式表達了馬克思的文字。兩者都在說同樣的觀點:人們沒有辦法選擇他們的起點。然而這一簡單的道理,在討論經濟和政治的時候卻常常被遺忘。
這是一本關于英國經濟如何走到今天這步的書。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衰退前夕,英國經濟處于非常奇怪的矛盾狀態:它既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經濟體之一,也拖了歐洲經濟的后腿。
從英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說,它處于世界領先的位置。但是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它的生產率水平(即使在過去十年之前)卻低得可憐。英國有一些地區是整個歐洲最富裕的,但是也有一些地區比起德國或者法國更像是南歐。從經濟角度上來看,英國就像是“葡萄牙,但還有個新加坡在墊底”,這句話用來形容英國并不算很夸張。
經濟史有助于解釋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如果這本書有一個主題,那就是路徑依賴的重要性。
路徑依賴或許會被解讀成這樣一個觀點:某人到達某地的路線是什么和目的地是哪里一樣重要。在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史)領域,這一概念可能至關重要。或者換一種說法,過去和歷史很重要,有時就像那個給游客提供建議的人一樣,對現在沒有什么特別的幫助。
這個想法在科技史上被廣泛應用,而或許許多經濟學家本能般想到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標準QWERTY鍵盤的設計。
按照傳統的說法,這個故事差不多是這樣的。當19世紀60年代位于密爾沃基的印刷商和報刊出版商克里斯托弗·萊瑟姆·肖爾斯(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首次發明打字機時,他自然而然地將鍵位按照字母順序排列,雖然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可能很奇怪,但是從直覺上這樣的排列方式比從Q開始然后接著是W、E、R要更說得通。
但是他的早期型號存在機械故障,當相鄰按鍵被快速連續敲擊時,很容易會出現卡鍵的情況。所以在1878年申請專利的時候,肖爾斯重新安排了鍵位布局來解決這個問題。有可能被經常連續敲擊的按鍵被排在了鍵盤的兩端,雖然這降低了打字速度,但它并非設計缺陷,而是刻意為之,其目的在于放慢打字流程從而防止昂貴的機器不斷卡住。
肖爾斯和槍械制造商雷明頓(Remington)合作,考慮到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的結束,后者可能在尋求新的業務線。到1893年,五個最大的打字機制造商都采用了QWERTY標準,歷史就這樣塵埃落定。
當然現代計算機不會出現和19世紀的打字機一樣的機械故障。實際上,有說法稱,這種機械故障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從打字機上被消除了。
1936年,奧古斯特·德沃夏克(August Dvorak)為另一種布局申請了專利,這種布局在美國海軍于1944年的測試中(當時快速制作報告的能力至關重要)明顯地提高了打字速度。但是盡管有了更好的設計,盡管最早采用QWERTY布局的理由已經不再成立,它仍然是行業基準。
通過率先入局市場,QWERTY鍵盤創立了一個標準。經過QWERTY鍵盤訓練的打字員不愿意切換到新的布局,而生產商們看到用戶對替代品沒有需求,也樂于繼續推出這些產品。效率較低的技術成了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或者說,傳統的故事是這樣說的。它確實很好地演示了路徑依賴這一概念的實際應用。令人遺憾的是,如同許多好故事一樣,它可能并不完全是真的:許多人對德沃夏克鍵盤持懷疑態度。但不管這個大多數經濟學家最喜歡的現象的例子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它仍然很有用,而且路徑依賴的應用范圍遠比在科技史領域更廣泛。
它毫無疑問地會出現在可能被稱作“經濟地理學”的地方。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們早就注意到了商業聚集的趨勢。假如有一個城鎮或者城市發展起了繁榮的印刷業,那么其他印刷企業就有理由選擇在此地開業——當地的勞務市場有著經驗豐富的印刷工人并且存在現成的紙張和油墨等必需品的供應商。該工業從本地區最初發展起來的原因——可能是勞務市場有特定技能的工人、特定原材料的供應或者其他完全不同的原因——可能并沒有它的確發展起來了這個事實重要。
美國出版業一直以來以紐約為中心,只是因為在19世紀,從英國來的快船就停在這里。這意味著查爾斯·狄更斯(在他的時代,他是一位在美國與英國有相同市場潛力的作家)最新的小說將率先登陸紐約,當地對知識產權鮮有尊重的出版商將為美國市場盜版并重印這些小說。(對版權規則跨國執法的擔心確實不是什么新鮮事了。)印刷業早就和跨越大西洋的航運時間表無關了,但一旦它在紐約扎根,它就一直在那里了。
城市中心(Centre for Cities)[2]智囊團在2015年的一項令人沮喪的研究中調查了1911年到2011年英國城市的增長和表現。一個重要的結論是:在2011年,一個城市里的“知識工作者”在勞動力中的所占比例是決定一個城市前景的重要因素。而解釋2011年知識工作者數量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1911年這個城市有多少知識工作者。作者認為,維岡(Wigan)在2011年仍沒有一個蓬勃發展的科技中心的原因在于它在1911年是一個小工廠工業鎮。相比之下,曼徹斯特中部地區在一個世紀以前就已經以高技能服務業工人為核心。歷史很重要。
另一個例子是一些經濟學家所說的“滯后效應”(hyste-resis effects)。滯后效應來源于希臘語中的“后來的(that which comes later)”,指的是在最初的催化劑或起因消失后仍然持續存在的簡單效應。最常見的兩個例子體現在勞務市場和國際貿易中。例如,英鎊升值使得某些英國出口產品在海外市場競爭力下降,該行業的公司會采取削減產量和工作崗位等相應措施來應對。然而如果幾年后,英鎊貶值使得英國出口產品再次具有了國際競爭力,但產量和就業情況可能并沒有辦法恢復到原來的水平。在英鎊價格高漲和失業率上升的時期,英國工人的技能可能已經退化,其他外國公司可能已經搶占了他們的市場份額。因此,英鎊升值可能會增加一個行業的失業率,但是當英鎊價格回落到原來的水平,這種影響并不會消除。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后期就是這種情況,當時強勢的英鎊成為英國制造業工作崗位減少的催化劑。20世紀90年代初英鎊走弱也未能重新刺激就業。
同樣地,一些貿易專家發現,國際貿易模式中持續存在滯后效應。這種觀點認為,公司在第一次進入一個市場時,一般會產生高昂的一次性成本。一旦一個公司已經選擇投入資金,即便有看似更好的機會出現,它可能也不愿意轉向另一個市場。
本書中一個反復出現的主題是,一代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商業領袖所采取的決策(同樣重要的還有他們所回避的決策)通常會塑造出他們的繼任者所面臨的決策。這一切與其說是被視作支持“歷史和過去將永遠決定未來”的論據,倒不如說是對“未來至少會被之前的事情所塑造(shaped)”的認可。
看著英國經濟在21世紀20年代呈現出來的許多特征,提一句“好吧,我不會從這里開始”的建議非常容易,然而這個建議對英國的政策制定者來說,就像前文中愛爾蘭人對游客所說的建議一樣“有用”。
路徑依賴是這本書的中心主題,但不是唯一一個。回顧過去兩個世紀的英國經濟史,我們能看到其他一些一次又一次反復出現的線索。
首先,政治經濟學很重要。如果不去考慮更廣泛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就試圖去理解一個經濟體所走的道路,尤其是長期以來的道路,這是無法做到的。英國在過去兩百多年的發展是由不同的(廣義的)政治利益集團的興衰所決定的。其次,政治重要性的方式常常被誤解。短期來看,政治家們高估了他們的影響力,但是長期來看,他們又低估了這種影響力。一個存在已久的經濟問題很難有一個簡單快速的解決方案,任何預算或政治優先事項在幾個月或幾年內能產生的影響都是有限的。但是經過幾年或幾十年,重大的政治決策會產生重要影響。而這往往發生在這些決策者卸任之后。
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是關于經濟與政治的交互以及兩者之間的反饋循環。當經濟增長疲軟時,政治極化會更加嚴重,同時分配斗爭會更加激烈。簡單來說:當蛋糕快速做大時,對于份額的爭搶會更少。經濟形勢最糟糕的時候就是政治形勢最緊張的時候:19世紀初期和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0年、20世紀70年代和2008年后,英國都處于疲軟的經濟增長和惡性的政治斗爭時期。
國際經濟和金融背景很重要。盡管表面上看,或者至少在經濟上看,英國并不是一個孤島。英國經濟總是被世界經濟的順風和逆風所沖擊,政策抉擇經常被國際因素所制約。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看似糟糕的宏觀經濟表現背后的驅動因素,是維護當時盛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下英鎊價值的需求(被視為是)。穩定和增長的世界經濟(加上低價中國商品的供應)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和21世紀初英國經濟的較好表現。英國國內的政策制定者往往得到了過多(本不屬于他們的)的贊譽和責難。
在政策方面,幾乎沒有免費的午餐。絕大多數現代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都是關于權衡的,這些權衡的內容(例如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或以犧牲長期增長為代價來提高短期收入)在不同時期也有所變化。這種權衡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簡稱“戰間期”)、20世紀70年代以及2008年后尤為尖銳和令人不快。
隨著本書對過去兩百年的回顧,許多議題會頻繁出現:經濟開放與國家主權之間的平衡、銀行是否過于強大或龐大到不會倒閉的問題、英國職業培訓的失敗、精英階層缺乏科學知識的假定、對德國制造業領先的擔憂、對新技術在勞務市場中所產生影響的憂慮、對不平等現象加劇的苦惱以及關于如何幫助那些有可能掉隊的地區和城市的問題。一個令人沮喪的結論是英國的公共辯論中幾乎沒有什么新內容。
另一個也許更令人沮喪的主題是,英國的政策制定者過于頻繁地選擇逃避選擇。面對有長期影響的困難決策,他們經常選擇簡單的方法得過且過,并且期待著最終能有點兒結果。過去幾十年來,修補和將就已經成了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
21世紀20年代的英國是一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然而資本主義并不是某種單一龐大的實體,它有某種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正如北歐模式和美國資本主義有所區別一樣,英國資本主義和其他先進經濟體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有所不同。這些經濟模式安排生產和分配的方式有不同的優勢和劣勢,有些擅長創造就業機會,有些擅長處理經濟衰退。人們很容易想問哪種模式更好,但是這有點像問雨衣和短褲哪種衣服更好的問題,答案當然是取決于天氣。但是,與服裝不同的是,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并不能因心血來潮而“說換就換”。相反,它們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能取得成果,并扎根于路徑依賴。
但是在真正深入到英國經濟是如何走到今天這步的故事之前,人們需要了解現代經濟本身是如何開始的。現代經濟史始于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則始于英國。
注釋
[1]中文譯文摘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譯者注。
[2]城市中心(Centre for Cities)是一個獨立的、無黨派的城市政策研究單位,并且是在英國注冊的一家慈善機構。該中心的主要目標是了解英國城市的經濟增長和變化如何以及為什么發生。——譯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