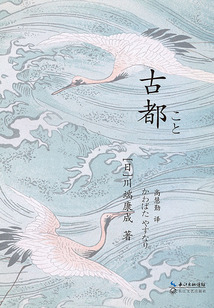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古都》:春之花
千重子發現楓樹的老干上,紫花地丁含苞吐蕊了。
“哦,今年又開花了。”千重子感到了春的溫馨。
在市內這方狹小的庭院里,這棵楓樹顯得特別大,樹干比千重子的身腰還粗。樹皮又老又糙,長滿青苔,當然同千重子那婀娜的腰肢無可比擬……
楓樹的樹干,齊千重子腰際的地方,略向右彎,到她頭頂上面,愈發彎了過去。而后,枝葉扶疏,遮滿庭院。長長的枝梢,沉沉地低垂。
在樹干屈曲處的稍下方,似乎有兩個小洼,紫花地丁就長在兩個洼眼里。而且,逢春必開。自千重子記事時起,樹上便有這兩株紫花地丁了。
上面一株,下面一株,相距一尺來遠。正當妙齡的千重子常常尋思:
“上面的紫花地丁同下面的紫花地丁,能相逢不?這兩枝花彼此是否有知呢?”說紫花地丁“相逢”咧,“有知”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每年春天花開不過三五朵。可是,到了春天,就會在樹上的小洼眼里抽芽開花。千重子在廊下凝望,或從樹根向上看去,時而為這紫花地丁的“生命力”深自感動,時而又泛起一陣“孤寂之感”。
“長在這么個地方,居然還能活下去……”
到店里來的顧客,有贊賞楓樹長得美的,卻幾乎無人留意紫花地丁開花。蒼勁粗實的樹干上,青苔一直長到老高的地方,顯得格外端莊古雅。而寄生其上的紫花地丁,自然不會博得別人的青睞。
然而,蝴蝶有知。千重子發現紫花地丁開花時,雙雙對對的小白蝴蝶,低掠過庭院,徑直飛近楓樹干上的紫花地丁。楓樹枝頭也正在抽芽,帶點兒紅,只有一丁點兒大,把翩翩飛舞的白蝴蝶襯映得光鮮奪目。兩株紫花地丁的枝葉和花朵,在楓樹干新長的青苔上,投下疏淡的影子。
這正是花開微陰,暖風和煦的春日。
直到白蝴蝶一只只飛去,千重子仍坐在廊下凝望楓樹干上的紫花地丁。
“今年又在老地方開花,真不容易呀。”她獨自喃喃,幾乎脫口說出聲來。
紫花地丁的下面,楓樹根旁豎了一盞舊的石燈籠。燈籠柱上雕了一個人像。記得有一次,父親告訴千重子說,那是基督。
“不是圣母瑪利亞么?”千重子當時問道。“有座大的和北野神社里供的天神像極了。”
“據說是基督。”父親肯定地說。“手里沒抱嬰兒么。”
“哦,當真……”千重子點了點頭。接著又問,“咱家祖上有人信教么?”
“沒有。這盞燈大概是設計庭園的師傅,要么是石匠搬來安在這兒的。燈也沒什么稀罕。”
這盞基督雕像燈籠,想必是從前禁教時期造的。石頭的質地很粗糙,易脆,上面的浮雕人像,經過幾百年的風吹雨打,已經毀損殘破,只有頭腳和身子依稀看出個形影來。恐怕當初的雕工也很簡陋。長袖幾乎拖到下擺處。雙手似乎合十,手腕那里略微凸了出來,辨不出是什么形狀。印象之間,與菩薩和地藏王是截然不同的。
這盞基督雕像燈籠,不知從前是為了表示信仰,抑或是用來當作擺飾,標榜異國情調?如今因其古色古香,才搬到千重子家店鋪的院子里,擺在那棵老楓樹腳下。倘使哪個來客發現了,父親便說“那是基督像”。至于店里的顧客,難得有人留心大楓樹下的舊燈籠。抑或有人注意到,院子里豎上一兩盞燈,本是司空見慣的事,誰也不會去看個仔細。
千重子的目光從樹上的紫花地丁向下移,看著基督像。千重子上的不是教會學校,但她喜歡英語,常出入教會,讀新舊約全書。可是,給這盞燈籠供花點燭,卻似乎有點不倫不類。上哪兒都沒雕十字架的燈籠。
基督像上面的紫花地丁,令人聯想起圣母瑪利亞的心。于是,千重子從基督雕像燈籠抬起眼睛,又望著紫花地丁。——驀地,她想起養在舊丹波[1]瓷壺里的金鐘兒來。
千重子養金鐘兒,比她最初發現紫花地丁在老樹上含苞吐蕊要晚得多,也就這四五年的事。在一個高中同學家的客廳里,她聽見金鐘兒叫個不停,便討了幾只回來。
“養在壺里,多可憐呀!”千重子說。可是那位同學卻說,總比養在籠子里白白死掉強。據說有些寺廟養了好多,還專門出售金鐘兒的子。看來有不少同好者呢。
千重子養的金鐘兒如今也多起來了,一共養了兩只舊丹波壺。每年不遲不早,準在七月初一前后孵出幼蟲,八月中開始鳴叫。
只不過它們出生、鳴叫、產卵、死亡,全在又小又暗的壺里。但是壺里可以傳種,也許真比養在籠子里只活短暫的一代強。而壺中討生活,亦別有天地。
千重子也知道,“壺中別有天地”是中國古代的一個故事。說是壺中有瓊樓玉宇,珍饈美酒,完全是脫離塵世的化外仙境。是許多神仙傳奇中的一個。
然而,金鐘兒卻并非因為厭棄紅塵才住進壺里的。雖然置身壺中,卻不知所處何地,就那么茍延殘喘下去。
頂叫千重子驚訝的,是要不時往壺里放入新的雄蟲,否則同是一個壺里的金鐘兒,繁衍的幼蟲又弱又小。因為一再近親相交的緣故。所以,為了避免這情形,一般養金鐘兒的人,彼此經常交換雄蟲。
眼下正是春天,不是金鐘兒引吭的秋天。可是,千重子從紫花地丁今年又在楓樹干的洼眼里開花,聯想到壺里的金鐘兒,倒并不是毫不相干的兩件事。
金鐘兒是千重子給放進壺里的,而紫花地丁又為什么會長在這樣一個局促的地方呢?紫花地丁業已開花,金鐘兒想必年來也會繁殖鳴叫的吧?
“難道是自然賜予的生命么……”
千重子將春風拂亂的鬢發掠到耳后。心里一面同紫花地丁和金鐘兒相比較:“那么我自己呢……”
在這萬物勃興的春光里,瞧著這小小的紫花地丁的,怕也只有千重子了。
聽見店里有動靜,大概正在開午飯。
千重子應邀要去賞櫻花,也該去梳洗打扮一下了。
昨天,水木真一打電話給千重子,邀她上平安神宮去賞櫻花。真一有個同學打工,半個月來,天天在神宮門口查票。真一聽他說,眼下正是花事最盛的時節。
“好像派人專門守望在那兒似的,這消息最確實不過了。”說著,真一低聲笑了起來。真一低低的笑聲,聲音很美。
“恐怕他會瞧見我們的。”千重子說。
“他是把門的呀。誰都得從把門的跟前過嘛。”真一又笑了兩聲。“你若覺得這樣不合適,咱們就分頭進去,到院子里的櫻花下碰頭好了。那兒的花,即便一個人賞,也看不厭的。”
“那你就一個人去賞花,豈不更好?”
“好固然好,萬一今晚下了大雨,花事凋零,我可不敢保。”
“那就看落花的風情罷。”
“雨打泥污的落花,難道還有什么風情可言?這就是你所謂的落花……”
“你真壞!”
“到底誰壞……”
千重子穿了件素凈的和服,走出家門。
平安神宮以“時代祭”[2]而著稱,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為紀念一千多年前桓武天皇奠都京都修建的,所以殿堂不太陳舊。據說大門和前殿是模仿當年平安京[3]的應天門和太極殿。右有橘林,左有櫻花。遷都東京之前的孝明天皇(1846—1866),從一九三八年起,也同歷代天皇一起在這里祭祀。在神前舉行婚禮的人為數不少。
最美的,莫過于一簇簇紅垂櫻,裝點著神苑。如今真可謂“除了此地櫻花,無以代表京洛的春天”。
千重子走進神苑的入口,便見櫻花滿枝,姹紫嫣紅,覺得賞心悅目。“啊,今年又看到京都的春天了。”她佇立著凝視櫻花。
然而,真一在哪兒等她呢?難道還沒來不成?千重子打算找到真一后再看花,便從花叢中走下緩坡。
真一正躺在下面的草地上閉目養神,兩手交叉枕在頭下。
千重子萬沒想到,真一會躺在那兒。真討厭。居然躺著等年輕姑娘。倒不是千重子覺得受了羞辱,或者是真一沒有禮貌,而是他那么躺著就不順眼。在千重子的生活里,難得見到睡著的男人,所以有點看不慣。
在大學校園里,大概真一也常和同學一起在草坪上,或支肘側臥,或仰天而躺,談笑風生。他此刻的樣子,不過是一種習慣姿勢罷了。
真一的身旁,坐著四五個老婆婆,攤開提盒,在談天說地。想必真一感到她們仁厚和藹,就坐在一旁,而后才躺了下去。
這么想著,千重子微微笑了,但是面頰上也跟著飛起一片紅暈。她不去驚動真一,只一味站在那里。終于,抬腳從真一身旁走開了……千重子確實從未見過男人的睡相。
真一的學生服穿得整整齊齊,頭發梳得光光溜溜。長長的睫毛合在一起,看來依然像個少年。可是,千重子正眼也沒瞧他一下。
“千重子!”真一叫住她,站了起來。千重子陡然著惱起來。
“睡在那兒,多不雅觀!過路人都看著你呢。”
“我沒睡呀。我知道你來了。”
“你真壞。”
“我想,要是不喊你,看你怎樣。”
“你看見我,還裝睡,是么?”
“我心里在想,進來的這位小姐多幸福啊!不覺感到有些悲哀。而且,還有些頭痛……”
“我?我幸福?……”
“……”
“你頭痛么?”
“不,已經不痛了。”
“臉色看著不大好。”
“不,沒什么。”
“簡直像把寶刀似的。”
真一不大聽人說,自己的臉“像把寶刀”。千重子這么說,卻還是頭一次聽到。
每逢別人這么說他,正是一股激情漲滿他的胸臆之時。
“放心,寶刀不傷人。而且,這兒又是櫻花樹下。”真一笑著說。
千重子登上緩坡,往回走到回廊的口上。真一也離開草坪,跟了過來。
“這些花真想全看一遍。”千重子說。
站在回廊西口,望著一簇簇紅垂櫻,頓時使人感到春意盎然。這才是名副其實的春天呀!連纖細低垂的枝頭,也開滿了嫣紅的重瓣櫻花。櫻花叢中,與其說是花開樹上,看起來倒像枝丫托著繁花朵朵。
“這兒的櫻花,我最喜歡這棵樹上的。”千重子說著,帶真一走到回廊另外一個拐彎處。那兒有棵櫻花樹,格外顯得花繁葉茂。真一也站在一旁,望著那棵櫻花。
“仔細看上去,頗有些女性的風韻,”真一說,“纖細低垂的枝丫,以及枝丫上的花朵,那么柔媚又那么豐滿……”
重瓣櫻花,朵朵都紅中帶紫。
“我從未想到,櫻花竟這么富有女性風度。無論是色調,姿態,抑或是嬌艷的風韻。”真一又說了一句。
兩人離開這棵花樹,向池邊走去。窄窄的小徑旁,擺著坐榻,上面鋪著大紅氈子。游客坐在那里喝茶品茗。
“千重子!千重子!”有人喊道。
幽陰的樹叢里,有座叫“澄心亭”的茶室。真砂子穿著長袖和服,從里面走出來。
“千重子,來幫個忙吧。我都累死了。我正幫師傅點茶呢。”
“我這一身,只配洗洗茶杯什么的。”千重子說。
“不要緊,洗茶杯也成……反正我端出去。”
“我還有個伴兒呢。”
真砂子這才發現真一,便咬著千重子耳朵問:
“是未婚夫么?”
千重子微微搖了搖頭。
“男朋友?”
又搖了搖頭。
真一轉身走開了。
“那么,你們就一起到茶會上來吧……這會兒正空。”真砂子這么邀請,千重子謝絕了,回頭追上真一說:
“是和我一起學茶道的。人很漂亮吧?”
“平平而已。”
“瞧你,不怕人家聽見。”
真砂子站在那里目送他們。千重子向她點頭致意。
穿出茶室下面的小徑,便是池塘。岸邊那片菖蒲葉子,綠意迎人,競相爭翠。水面上浮著睡蓮的葉子。
池塘的四周,沒有櫻花。
千重子和真一沿著池塘,向一條林蔭小路走去。嫩葉的清香和著濕土的氣息,溢滿空中。這條林蔭路又窄又短。走到盡頭,豁然開朗,呈現一片池水,比方才的池塘還大。池邊的紅垂櫻,映在水中,照人眼明。外國游客對著櫻花紛紛拍照。
池對岸的樹叢里,馬醉木開出樸素淡白的小花。——千重子想起了奈良。有不少松樹,雖然談不上古木參天,卻婆娑多姿。倘若沒有櫻花,蒼翠的松樹也足以使人注目觀賞的吧?想必不錯。眼下,高潔的青松,澄明的池水,把朵朵的紅垂櫻襯映得格外妍媚。
真一走在前面,踩著池中的石步。這叫作“渡水”。一塊塊石步,圓圓的,仿佛是從牌樓柱子上截下來的。有的地方,千重子須略微撩起和服的下擺。真一扭過頭來說:
“真想背你過來呢。”
“你背個試試。算我佩服你。”
這些石步,連老太婆都能渡得過的。
石步旁邊,也漂浮著睡蓮的葉子。快到對岸時,石旁的水面上映著小松樹的倒影。
“這些石步,排列的形狀,很有點像抽象派。”真一說。
“日本的庭園,不是全有點像抽象派么?醍醐寺院的杉形蘚,大家也都說什么抽象抽象的,聽著叫人反感……”
“誠然,那里的杉形蘚,的確很抽象。醍醐寺里的五重塔,已經修繕完畢,就要舉行竣工典禮了。去看看好嗎?”
“那五重塔,也會跟新金閣寺[4]一樣么?”
“想必也會煥然一新,莊嚴堂皇吧。盡管塔沒燒掉……也是拆掉后,照原樣重蓋的。竣工典禮正趕上櫻花盛開的時候,恐怕會人山人海。”
“要講賞花,看了這里的紅垂櫻,別處的就不會再想看了。”
兩人說著,走完了最后幾塊石步。
走完石步,池邊是片松林。再走不多遠,便上了“橋殿”。“橋殿”也者,實則為橋,因造型像座宮殿,故名曰泰平閣。兩側的橋欄,有如帶矮靠背的長凳,游人可以坐在上面休憩,隔池眺望園景,不,應說眺望帶池塘的庭園。
坐在橋邊的人,吃的吃,喝的喝,也有小孩子在橋心跑來跑去。
“真一,真一,這兒……”千重子先坐了下來,右手給真一占了個座位。
“我站著好了,”真一說,“蹲在千重子小姐腳下也行……”
“不理你。”千重子倏地站起,讓真一坐下。“我去買些鯉魚餌來。”
千重子買回魚餌,撒到池里,鯉魚一群群聚攏來,有的跳出水面。漣漪一圈圈漾了開來。松陰櫻影,搖曳流蕩。
剩下的魚餌,千重子問真一:“給你吧?”真一默不作聲。
“頭還痛么?”
“不痛。”
兩人在橋上坐了很久。真一臉色發青,兀自凝睇望著水面。
“想什么呢?”千重子問。
“哦,想什么?有時會什么都不想,卻覺得挺幸福!”
“在這櫻花爛漫的春日……”
“不,在幸福的小姐身旁……或許也沾到點幸福?那么溫婉可人而又富有朝氣。”
“你說我幸福?……”千重子反問了一句,眼里忽然蒙上一層憂郁的陰影。她低垂著頭,池水仿佛映上她的眼簾。
千重子站了起來。
“橋對面有棵櫻花,我最喜歡。”
“這里也看得見,是那棵吧?”
那株紅垂櫻,極其俏麗。盡人皆知,是棵名花。花枝有如弱柳低垂,疏密有致。走在花下,輕風微拂,花瓣飄落在千重子的肩上,腳下。
樹下也有點點落花,間或也散在水面上。不過,算來怕只有七八朵的樣子……
有的垂枝雖撐以竹竿,但樹梢纖纖,仍一味下垂,幾乎拂到地面。
繁花如錦,透過隙縫,隔池猶可望見東岸樹叢之上嫩葉覆蓋的一發青山。
“是東山的余脈吧?”真一問。
“是大文字山。”千重子答。
“哦,是大文字山?怎么看著那么高?”
“恐怕是站在花叢里看的緣故。”然而,千重子自己也是在花樹叢中的。
兩人都有些流連難舍。
那棵櫻花四周的地面上,鋪滿了白色的粗砂。右邊,松林高聳,在這座園子里可謂挺拔優雅,接著便是神苑的出口。
走出應天門,千重子說:
“我想去清水寺看看。”
“清水寺?”真一臉上的表情,仿佛是說,去這么個不足道哉的地方。
“我想從清水寺那兒看看京城的黃昏。還想看看西山上落日的霞空。”聽千重子一再這么說,真一便也點頭同意。
“好,那就去吧。”
“走著去好嗎?”
路相當遠。他們避開電車路,繞道南禪寺,出知恩院后門,穿過圓山公園,踏上一條羊腸古道,便來到清水寺前面。這時已是春日向晚,暮靄沉沉了。
清水寺的舞臺上,游人只剩三四個女學生,她們的面容已經看不甚真切了。
這正是千重子最喜歡的時刻。漆黑的正殿里已點上明燈。千重子停也不停,徑直走過正殿的舞臺,從阿彌陀佛殿前面走進里院。
里院也有座“舞臺”,是筑在懸崖峭壁上的。屋頂葺以檜樹皮,檐角輕飏,舞臺小巧玲瓏。但這舞臺是面西而坐的,朝著京城,對著西山。
市里已經燈火點點,夜色微茫。
千重子靠著舞臺的欄桿,仰望西天,仿佛忘了同來的真一。真一走到她身旁。
“真一,我是個棄兒。”千重子突兀地說。
“棄兒?”
“嗯,棄兒。”
這“棄兒”二字,難道是別有用意?真一頗感迷惑不解。
“棄兒?”真一喃喃地說,“你怎么胡思亂想自己是個棄兒!你算棄兒,那我更是棄兒了,那種精神上的……也許人人都是棄兒。一個人降生到世上,就像是被上帝拋到人間一樣。”
真一望著千重子的側臉,隱隱約約好像染上一層暮色似的。也許是春宵惱人,她才凄然不樂?
“正因為是上帝之子,所以拋棄在前,拯救在后……”
真一的話,千重子似乎沒有聽進去,只管俯瞰燈光璨然的京城,對他看都不看一眼。
看到千重子這種莫名的悲哀,真一不覺抬起手來,往她肩上放去。千重子把身子一閃,說道:
“別碰我這個棄兒。”
“明明是上帝之子,卻說是棄兒……”真一的聲音提高了一點說。
“別說得那么玄……我才不是什么上帝的棄兒,實在是為人間的父母所遺棄的孩子。”
“……”
“是個扔在鋪子外面格子門前的棄兒。”
“你胡說什么呀!”
“是真的。雖說這事告訴你也沒用……”
“……”
“從清水寺這兒,望著暮色中廣漠的京城,我心里想,自己果真是出生在京城的么?”
“看你說的。簡直是發神經……”
“我干嗎要瞎說呢?”
“你難道不是批發商的掌上明珠么?獨生女就愛想入非非。”
“當然,他們疼我。如今棄兒不棄兒也沒什么要緊,可是……”
“你說是棄兒,有什么根據么?”
“根據?鋪子外的格子門就是根據。古老的格子門,知道得最清楚。”千重子的聲音愈發清朗悅耳,“記得上中學時,母親把我叫去,告訴我說:‘千重子,你不是我親生的。我看到一個可愛的嬰兒,就抱了乘上車,一溜煙逃回了家。’不過,在什么地方偷抱的,父親和母親有時不留神,說法互有出入。一個說在祇園[5]的夜櫻下,一個說在鴨川邊上……要是照實說,我是給扔在店門前的棄兒,他們準是覺得我太可憐,才這么說的……”
“哦,那你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誰么?”
“現在的父母很疼我,我也就無意再去打聽了。也許他們早已成為仇野墓場里的孤魂野鬼了。石冢已經陳舊不堪……”
春日的溶溶暮色,宛如一片淡紅的云霞,從西山一路籠罩過去,遮蔽京都的半邊天空。
真一簡直難以置信,千重子會是一個棄兒,更不消說是偷來的孩子。她家在古老的批發商大街上,到附近一打聽就能知道。當然,眼下真一還沒打算要去查個明白。他感到迷惘,并想知道的是,千重子為什么要在此時此地告訴他這些話。
難道說,約他真一到清水寺來,就是為了說這事的?千重子的聲音更加清越明澈了。語調優美,透出剛毅的韻味。看來并非是向真一訴苦。
千重子隱隱約約知道,真一在愛她。莫非千重子的告白,是為了叫所愛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世不成?真一聽著又不像。不如說,正相反,言外之意是她壓根兒就拒絕他的愛。然而,即便“棄兒”一說是千重子編造的也罷……
真一心里尋思,在平安神宮里,他幾次說千重子“幸福”,千重子的話要是用來反駁他的,那就好了。真一想試探一下。
“你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感到失望沒有?傷心了么?”
“不,一點都不失望,也沒傷心。”
“……”
“只是我提出要上大學的時候,父親說,一個要繼承家業的女孩兒,上什么大學!反倒誤事。還不如好好學做生意實惠。當時聽了父親這話,我才有些……”
“是前年的事吧?”
“是啊。”
“你對父母總百依百順嗎?”
“嗯,百依百順。”
“婚姻大事也如此?”
“嗯,目前還是這么打算。”千重子毫不猶豫地答道。
“難道就不考慮你自己,不考慮個人的感情么?”真一問。
“考慮得簡直過分,為此都苦惱不堪。”
“你想壓制自己,扼殺自己的感情么?”
“不,沒的話。”
“你盡說謎一樣的話。”真一輕輕一笑,聲音有些顫抖。他把身子探出欄外,想窺探千重子的臉色。“我要看看這個謎一樣的棄兒的尊容。”
“恐怕太暗了。”千重子這才把臉轉向真一,目光閃閃。
“怪嚇人的……”千重子抬眼望著正殿的屋頂,上面的檜樹皮葺得厚厚的,顯得又重又暗,逼仄過來,陰森可怖。
注釋
[1]舊地名,現大部分屬于京都,出產瓷器。
[2]時代祭:為紀念桓武天皇奠都京都,自一八九五年平安神宮建成以來,每年十月二十二日舉行祭祀活動,在神輿前,游行者身著各時代服飾,展示平安朝至明治年間的風俗變遷。
[3]即現在的京都。
[4]即京都北山上的鹿苑寺,寺內有三層的舍利殿一座,柱子和墻壁均飾以金箔,故名金閣。一九五〇年焚毀,后重建。
[5]祇園為京都八坂神社的舊名,也指附近一帶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