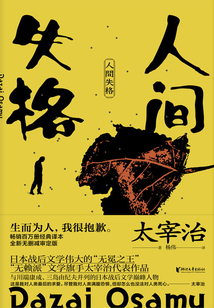
人間失格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永遠(yuǎn)的少年”——太宰治及其文學(xué)的心理軌跡
太宰治的小說第一次進(jìn)入中國內(nèi)地讀者的視野,大約是在1981年。張嘉林先生翻譯的《斜陽》出現(xiàn)在“文革”結(jié)束后不久的中國文壇,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太宰文學(xué)熱。盡管它似乎被淹沒在了罩著諾貝爾文學(xué)獎光環(huán)的川端康成文學(xué)的翻譯熱浪里,卻悄無聲息地形成了一股雖不張揚(yáng)但持續(xù)涌動的“暗流”,造就了一批癡迷得近于“狂熱信徒”的讀者群體。與川端文學(xué)和后來的大江文學(xué)不同,太宰文學(xué)不是以轟轟烈烈的方式,而是以更加個體和隱秘的,甚至是“同謀犯”的方式闖入讀者心中某一片或許是被刻意掩飾的角隅,攪動了讀者內(nèi)心深處最柔弱而又最執(zhí)拗的鄉(xiāng)愁。
太宰文學(xué)被譽(yù)為永恒的“青春文學(xué)”,被年輕的少年們(包括另一種心理狀態(tài)上的少年們)視為神明一般的尊奉,其中漂漾著的“清澄的感受性”和絕不妥協(xié)的純粹性堪稱世界上青春文學(xué)的最好范本。與此同時,太宰文學(xué)又被譽(yù)為“弱者的文學(xué)”,正如他在《蓄犬談》一文中所說的那樣:“藝術(shù)家本來就應(yīng)該是弱者的伙伴——弱者的朋友。對藝術(shù)家來說,這就是出發(fā)點(diǎn),就是最高的目的。”太宰治似乎是把懦弱作為一種出發(fā)點(diǎn),甚至是一種武器,以退為進(jìn)地向所謂的“強(qiáng)者”、向偽善的人生和社會公開宣戰(zhàn),從而彰顯出一種別樣的強(qiáng)大、別樣的高貴和驕傲的激情。
太宰治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擁有大量可以炒作的題材。他出身豪門,一生立志文學(xué),師從井伏鱒二等小說名家;大學(xué)時代曾積極投身左翼運(yùn)動,卻中途脫逃;生活放蕩不羈,卻熱心于閱讀《圣經(jīng)》;五度自殺,四度殉情未遂,39歲時與最后一位情人投水自盡。以至于他說“我過的是一種充滿恥辱的生活”(《人間失格》),“生而為人,我很抱歉”(《二十世紀(jì)旗手》),但與此同時,“上帝選民的不安與恍惚俱存于吾身”(《葉》)。而這些格言式的短句恰好成了太宰治人生和文學(xué)的最好注腳,也從某個角度勾勒出了他一生的心理軌跡。
“多余人意識”
太宰治,原名津島修治,于1909年6月19日出生在日本青森縣北津輕郡金木町一個大地主家庭。父親是一個多額納稅的貴族院議員。盡管津島(太宰治的本姓)一家是津輕這片窮鄉(xiāng)僻壤遠(yuǎn)近聞名的豪門望族,卻是依靠投機(jī)買賣和高利貸而發(fā)家致富的暴發(fā)戶。因此,“我的老家沒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家譜”,“實(shí)在是一個俗氣的、普通的鄉(xiāng)巴佬大地主”(《苦惱年鑒》)。這樣一個豪華而粗鄙的家庭使太宰治滋生了一種“名門意識”,同時又使他終生對那種真正的貴族抱有執(zhí)著的憧憬(這在《斜陽》中表現(xiàn)得尤其充分)。因此,他的一生一直在留戀、依賴這個家庭和背叛、批判這個家庭的矛盾中掙扎搏斗,以追求個人的自我價值。不難看出,太宰治作為津島家的公子,因?yàn)檫@個家庭感受到了自卑和自豪的矛盾,而這種雙重情感的分裂與太宰治一生的極度榮譽(yù)感和自我欠缺感的性格基調(diào)乃是一脈相承的。
從小在周圍和學(xué)校受到的不同于一般人的優(yōu)厚待遇和自幼的聰穎敏感以及“名門意識”,使他感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特殊人種。這種極度的自尊和優(yōu)越感發(fā)展為一種極度的榮譽(yù)感和英雄主義,導(dǎo)致了他所謂的“選民意識”。而過分的自矜又導(dǎo)致了他強(qiáng)烈的自我意識和敏銳的感受性,并必然在粗糙的現(xiàn)實(shí)中動輒受傷。在冷漠的家庭中,他近乎早熟地解構(gòu)著他人的面目和人類的本性,從少年時代起就反復(fù)經(jīng)歷了對榮譽(yù)的熱烈憧憬和悲慘的失敗,進(jìn)而是對人性的絕望。正是這種極度的自尊心和容易受傷的感受性構(gòu)成了太宰治一生的性格基調(diào)。它不難演變成一種對絕對的渴求,對至善至美的最高理想的執(zhí)著憧憬,容不得半點(diǎn)瑕疵的潔癖。這種絕對的追求因?yàn)槿狈ΜF(xiàn)實(shí)的根基和足夠的心理準(zhǔn)備,一遇到挫折就很容易蛻變成強(qiáng)烈的自卑和完全的自暴自棄。要么完美無缺,要么徹底破滅,這無疑最好地表達(dá)了太宰治一生的純粹性和脆弱性,同時亦不妨看作現(xiàn)代青春特性的集中寫照。
作為家庭的第六個兒子,加之父親的忙碌和母親的體弱多病,他是在姨母和保姆阿竹的養(yǎng)護(hù)下長大的。他生活在孤獨(dú)寂寞的世界里,渴望著熱烈的愛而又無法得到,這使他感到有一種被世界拋棄了的悲哀。外界對于他永遠(yuǎn)是一個可怕的存在,仿佛自己被排擠在社會外,不能與現(xiàn)實(shí)社會和他人發(fā)生有機(jī)的聯(lián)系。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反而使他能夠站在現(xiàn)實(shí)以外利用自己的批判意識來認(rèn)識乃至批判家庭和社會中人的冷漠、虛偽和庸俗。可以說,在社會和外界遺棄了太宰治的同時,太宰治也拒絕了偽善、鄙俗的外界社會,從而使他的內(nèi)心世界與現(xiàn)實(shí)世界的隔膜和分裂愈演愈烈,以至于發(fā)展成為一種尖銳的對抗性。因而,他對世間的認(rèn)識永遠(yuǎn)是靜止的,甚至不乏極端的成分,并依靠這種極端而成就了一種絕不妥協(xié)的純粹性。他蜷縮在自己的世界里形成了一個封閉性的自我,再加上物質(zhì)條件的優(yōu)厚使他得以在一個遠(yuǎn)離了實(shí)用性和人生操勞的超現(xiàn)實(shí)的境地中,在浪漫的主觀世界里,編織自己至善至美的理想花環(huán),并以此為基點(diǎn)去認(rèn)識現(xiàn)實(shí)和批判現(xiàn)實(shí)。而這種脫離了實(shí)際生活的批判意識因?yàn)樘幵诔髳旱默F(xiàn)實(shí)之外,所以使他能夠在剖析實(shí)際生活時變得更加犀利更加純粹的同時,也很容易變成一種不結(jié)果實(shí)的花朵,一場必然敗北的斗爭。
而當(dāng)太宰治的極度榮譽(yù)感和強(qiáng)烈的批評意識從外界轉(zhuǎn)向自我時,追求至善至美的性格又使他無法肯定自我的價值,從而對自我進(jìn)行了毫不留情甚至是苛刻的反省,迫使他背負(fù)了在常人看來大可不必的自卑意識和自我欠缺感。作為大地主的第六個兒子,太宰治有一種“家庭的多余人意識”,之后隨著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的興起,在與平民百姓的接觸中發(fā)展成了一種“社會的多余人意識”。于是,他陷入了一種現(xiàn)實(shí)的批評者和理想的追求者之間的深刻矛盾中,以至于不得不在早期作品《往事》的題首錄下了魏爾倫的詩句:“上帝選民的恍惚與不安俱存于吾身。”
無產(chǎn)階級運(yùn)動與“叛徒意識”
在這種極度的苦惱、自我意識的分裂中怎樣解決現(xiàn)實(shí)與理想之間的矛盾呢?“我終于找到了一個寂寞的排泄口,那就是創(chuàng)作。在這里有許多我的同類,大家都和我一樣感到一種莫名的戰(zhàn)栗。做一個作家吧,做一個作家吧。”(《往事》)于是,太宰治在一個遠(yuǎn)離了現(xiàn)實(shí)的地方,在一個獨(dú)自的世界里——文學(xué)中——找到了孤獨(dú)和不安的排泄口,使主觀理想與客觀現(xiàn)實(shí)在一個架空的世界里——創(chuàng)作的天地中,依靠觀念和冥想得到了暫時的統(tǒng)一。
除了在文學(xué)中尋求矛盾的暫時緩和以外,在實(shí)際生活中太宰治被迫走上了一條自我破壞的道路。對市民社會的虛偽性和陳規(guī)陋習(xí)深惡痛絕的他棄絕了那些世俗的追求自我價值的道路,而是通過確認(rèn)自己的自我欠缺感,甚至犧牲自己這樣一種貌似無賴的方式來達(dá)成舊的道德秩序的解體,以換取一種“廢墟的生命力”,實(shí)現(xiàn)一種曲折的自我肯定、自我升華,擺脫過剩的自我意識的泥沼。而大正末年、昭和初年興起的無產(chǎn)階級運(yùn)動恰好成了他確認(rèn)自我欠缺感、進(jìn)行自我破壞的突破口。
昭和初年的無產(chǎn)階級運(yùn)動直接波及了津島家,以榨取農(nóng)民血汗致富的津島家成了無產(chǎn)階級運(yùn)動的對象,這加深了太宰治的“社會的多余人意識”,并進(jìn)而發(fā)展成作為地主兒子的“民眾之?dāng)场钡囊庾R。太宰治為此抱有一種宿命的罪惡意識,在少年期所經(jīng)歷過的觀念上的敗北因?yàn)楦锩牡絹淼玫搅司唧w而實(shí)際的印證。這種階級意識上的“負(fù)的意識”壓迫著太宰治,促使他很快加入了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出席秘密研究會,并寫出了《學(xué)生群》《一代地主》等帶有無產(chǎn)階級色彩的作品,但不久他就脫離了革命。顯然這與他的思想性格,特別是他參加革命運(yùn)動的獨(dú)特方式是密不可分的。
太宰治作為絕對理想的追求者必然對相對的現(xiàn)實(shí)、僵化腐敗的現(xiàn)存道德秩序持激烈的否定態(tài)度,因而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的興起無異于一盞明燈點(diǎn)燃在現(xiàn)實(shí)的黑暗之中。他對現(xiàn)實(shí)的矛盾不加妥協(xié)、一律持拒絕、全面批判的態(tài)度,與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對現(xiàn)實(shí)社會的猛烈批判乃至對舊秩序的顛覆,從某種意義上看,無疑有著相似的一面。因而太宰治來不及仔細(xì)研究共產(chǎn)主義,僅僅由于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對現(xiàn)有制度的否定便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共鳴。“總之,與其說是那種運(yùn)動的目的,不如說是那種運(yùn)動的外殼更符合我的口味。”(《人間失格》)毋庸置疑,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是一場打倒一切剝削階級的現(xiàn)實(shí)革命,作為大地主的兒子,太宰治所抱有的宿命的罪惡意識使他不可能作為一個革命者,而只能作為革命的對象投身其中。因此,不是成為革命家,而是破壞自己、滅亡自己,清算封建家庭的罪孽,成為民眾之友,發(fā)掘自己作為被革命者的存在價值,就成了他參加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的獨(dú)特方式。這種獨(dú)特的方式?jīng)Q定了他只能稀里糊涂地投身于革命,在自己極度受傷甚至毀滅之后,便又脫離了革命。顯然,他參加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不是客觀的現(xiàn)實(shí),而是自己出身的原罪意識和過剩的自我意識。換言之,他不是作為一種社會思想,而是作為一種個人倫理來參加革命的,這決定了他在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這一改革現(xiàn)實(shí)的社會實(shí)踐中必然半途而廢。因而,他始終沒有從世界觀上信奉馬列主義,而僅僅是作為一種知識修養(yǎng)對馬列主義持理解態(tài)度。因此,不難理解太宰治在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遭受挫折、身心交瘁的情況下脫離革命的結(jié)局。在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中加深了自己的“多余人意識”,并進(jìn)行了殘酷的自我破壞之后,太宰治逃離了革命。這徹底決定了他只能以滅亡者的身份與社會發(fā)生聯(lián)系的生活道路。不是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而是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的挫折感、背叛感一直折磨著患有潔癖的太宰治,使他背上了沉重的“罪惡意識”,使其文學(xué)變成了與罪惡意識搏斗的記錄。
“如果是叛徒,就要像叛徒一樣地行動。……我等待著被殺戮的日子。”(《虛構(gòu)之春》)太宰治在確認(rèn)了自己的“多余人意識”“叛徒意識”之后,只能把叛徒的烙印打在自己的臉上,以自我破壞來追求自己作為“叛徒”的價值。“丟了性命來徹底地過所謂的不道德生活,也許這倒要受到后世人們的稱贊。犧牲者。道德過渡時期的犧牲者。”(《斜陽》)因此,太宰治自覺地也是無可奈何地選擇了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不僅徹底毀滅自己,并以此去擴(kuò)大惡,從內(nèi)部來使舊的秩序徹底崩潰,為新的時代,為他人盡自己作為破滅者的努力,求得一種“負(fù)的平方根”,進(jìn)而最終得到一種自我價值的肯定。這便是太宰治的“無賴”哲學(xué)。而最大的自我毀滅就是死亡——于是,太宰治和一個咖啡店女服務(wù)員一起相約共服安眠藥自殺,結(jié)果那個女人死了,他卻活了下來,這無疑更加深了他的“罪惡意識”。
“丑角精神”
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的挫折使他對一切思想的有效性產(chǎn)生了懷疑,也不再相信任何改革現(xiàn)實(shí)的實(shí)踐活動,因而他又重新回到了因參加共產(chǎn)主義運(yùn)動而一度中斷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他以遺書的形式發(fā)表了總題為《晚年》的一系列小說。他在文學(xué)中以觀念的形式避免強(qiáng)烈的自我破壞來解決現(xiàn)實(shí)的苦惱,達(dá)到了一種較為直接的自我肯定,使自己的行為得以正當(dāng)化。然而,每當(dāng)他的自我在文學(xué)中得到主張時,其批評意識又會即刻復(fù)活,對這種自我主張本身發(fā)起攻擊,從而形成更深的自我否定。這種自我主張與自我否定交替進(jìn)行,循環(huán)往復(fù),使他暫時在文學(xué)中得以統(tǒng)一的自我變得愈加分裂,而這給他的創(chuàng)作手法也帶來了極大的影響,比如在《葉》《丑角之花》《虛構(gòu)之春》《狂言之神》等小說中,分裂的自我在絕望的自我否定與自嘲式的自我肯定中輪番登場,而無數(shù)的主人公都不啻作者的分身。
于是,在實(shí)際生活中,背負(fù)著“罪惡意識”而又渴求自我絕對完美的太宰治只能以徹底的自我犧牲和自我破壞來謀求與他人和社會的聯(lián)系,并試圖在這種聯(lián)系中確認(rèn)自己的價值,其具體方法就是他所謂的“丑角精神”。在與外界的敵對關(guān)系中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次敗北的“多余人”和“叛徒”最后只能屈從于外界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罩上“丑角”的面殼來掩蓋自己的真實(shí)面目,用小時候起就慣用的“逗笑”“裝模作樣”等手法來偽裝自己,取悅于他人,使自己徹底地非自己化。與他人同一化,從而發(fā)展成一種“丑角精神”。但他極度的自尊心和榮譽(yù)感又不允許他完全屈從于外界社會,因此,他又開始了向人們的攻擊和報復(fù)。因而,“丑角精神”就是這樣一種復(fù)雜的心理機(jī)制的產(chǎn)物。
太宰治扮演丑角乃是為了向他人求愛,同時又保護(hù)脆弱的自我。但太宰治的文學(xué)卻力圖使自己的這種“丑角精神”上升為一種絕對的利他精神,以此來反襯社會和他人的冷漠,夸耀自己的純粹。事實(shí)上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這種“丑角精神”雖然總是力圖上升為一種利他主義精神,卻一直未能達(dá)到一種真正的利他主義,其直接的目的較之服務(wù)于他人,更注重保護(hù)自我。由于這種“丑角精神”是在絕對固守自我的內(nèi)心世界,割斷與現(xiàn)實(shí)聯(lián)系的前提下發(fā)揮的,因而“求愛”只是一個外殼,核心乃是掩藏真實(shí)的自我。即使他用虛假的自我贏得了與他人的聯(lián)系,但這種聯(lián)系也是建立在真實(shí)的自我之外的,因此必定是脆弱的、缺乏現(xiàn)實(shí)性的表面聯(lián)系,從而注定了太宰治的“丑角精神”必然以失敗告終。但是,根本否認(rèn)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之可能性的太宰治是能夠預(yù)料并且不怕這種失敗的,因?yàn)殡m然敗在了別人手里,卻戰(zhàn)勝了自己。正是在一次次慘重的失敗中,太宰治向人們、更向自己證實(shí)了自我通向至善至美境地的途徑。因而,太宰治的“丑角”越演越烈,并在《人間失格》中大談“丑角精神”的發(fā)揮和破滅。正是借助文學(xué)與現(xiàn)實(shí)的相輔相成,太宰治得到了一種心理上的自我滿足、人格上的自我升華和非同尋常的自我優(yōu)越感,使至善至美的理想之光在汗流浹背的服務(wù)中冉冉升起。
“只有具備自我優(yōu)越感的人才可能扮演丑角。”(《乞丐學(xué)生》)不難看出,太宰治的“丑角精神”既是獲取自我優(yōu)越感的途徑,同時也是因扮演丑角、屈從于他人和社會而受傷的自尊心對外界現(xiàn)實(shí)和他人的報復(fù)。“以自虐為武器試圖進(jìn)行報復(fù),這是太宰治的倫理。”[1]于是,為了獲得更大的自我肯定,他就只能加倍地扮演丑角。他的這種自我肯定有時甚至是建立在一種希望現(xiàn)實(shí)的惡、人類的惡暫時不變的基礎(chǔ)之上的,因?yàn)橹挥鞋F(xiàn)實(shí)和他人的惡不變,甚至越烈,他的高尚和純粹才越發(fā)奪目,才越能在與現(xiàn)實(shí)和他人的反襯中追求并凸顯自己的完美。因而他是靠摒棄了對現(xiàn)實(shí)社會之完美的追求來保持住了對自我之完美的追求。從這種意義上說,他是一個自我中心主義者,但他又要用自我的完美反過來教育世人,給人類以愛的榜樣,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又是一個善良的人,一個帶有悲劇色彩的英雄人物。以至于他不惜用死亡來證實(shí)并完成自己的純粹,然后再用自己的純粹來拯救世界。換言之,是企圖先拒絕現(xiàn)實(shí)以追求自我的絕對完美,然后再用絕對完美的自我來引導(dǎo)人們追求現(xiàn)實(shí)世界的絕對完美。至此,太宰治的想法明顯地向《圣經(jīng)》接近了。
太宰治與《圣經(jīng)》
怎樣使自己的“丑角精神”和自我破壞獲得真正的價值和永恒的意義呢?太宰治以文學(xué)為媒介表白自己的衷腸,證實(shí)自己的純粹,但又不免感到這種文學(xué)上的自我肯定有他自己厭惡的傲慢與矯飾之嫌。所以,他在文學(xué)上的自我肯定是相對的,顯得躲躲閃閃,時刻有被自己和他人批評的可能性。因此,太宰治迫切需要找到文學(xué)以外的一種東西來求得絕對的自我肯定,以統(tǒng)一分裂的自我。“‘你要像愛自己一樣愛你的鄰人。’這是我最初的宗旨,也是我最后的宗旨。”(《隨想(回信——致貴司山治)昭和二十一年三月》)于是,太宰治以《圣經(jīng)》為依據(jù),將自己的“丑角精神”上升為一種愛鄰人的宗教精神,從而使自己的自我破壞因?yàn)樯竦某霈F(xiàn)而獲得了絕對的道德意義。正如同為無賴派代表作家的坂口安吾所言:“在不良少年中也算是特別的膽小鬼和好哭鬼。依靠臂力不能取勝,依靠道理也不能取勝。于是,只好搬出一個證據(jù)的權(quán)威來進(jìn)行自我主張。芥川和太宰都舉基督為例證,這是不良少年里那些膽小鬼和哭鬼的常用伎倆。”[2]太宰治一接觸到《圣經(jīng)》,不需要教會和牧師,便馬上變成了《圣經(jīng)》的熱心讀者。一面扮演丑角,一面又懷疑丑角意義的太宰治通過接近《圣經(jīng)》,使“丑角精神”獲得了一種形而上的意義,一種有力的理論依據(jù),從而有可能從自我保護(hù)手段上升為崇高的宗教精神。因而,他死死攀住基督這棵樹,來使自己擺脫自我懷疑的泥潭,向基督的完美境界闊步前進(jìn),以成為一個絕對的善者。作為一個追求完美的人,太宰治對那種純粹高尚的、無報酬的行為和毫無利己之心的生活,還有這種生活的完美實(shí)踐者、基督的美感到深深的欽慕和向往。但太宰治作為一個罪人、叛徒,只能把自己投影于猶大身上,主動走向神這個絕對者的審判臺,使自我破壞和“丑角精神”在神的面前演變成一種自我贖罪,并使自我贖罪徹底化為通向自我完善的途徑,以獲取與基督相同的意義。他“不相信神的寵愛,而只相信神的懲罰”(《人間失格》)。這是他對神的獨(dú)特信仰方式,從而使他區(qū)別于一般的基督教徒。我們知道,基督教因保羅的出現(xiàn)而由律法式的宗教變成了信仰的宗教。神把他的兒子耶穌派到人間,將人類從罪孽中拯救出來。無罪的基督身著仆人的襤褸衣衫在十字架上受刑而死,以他一個人的死贖清了全人類的罪過。因而基督之死證明神不僅是懲罰之神,更是恩寵之神。只有這樣才打開了前往天國的道路。但太宰治對于神不是乞求寬恕,而僅僅是乞求一種懲罰。太宰治沒有看到,更準(zhǔn)確地說,是故意抹殺了死于十字架上為全人類贖罪的耶穌的光輝,而只是以絕對理想追求者的身份崇拜著基督的完美。他把“人間失格”的形象與基督耶穌的形象聯(lián)系起來,不斷地乞求神的懲罰,以便使自己在神的懲罰中不斷升華,最終由一個“人間失格者”過渡到耶穌式的英雄。越接近基督,也就意味著自我破壞愈加慘烈,越是喪失為人的資格,從而在這種帶有自虐色彩的行為中汲取到文學(xué)的源泉,體驗(yàn)到一種超越了凡人向神的完美過渡的快感。正如法國作家紀(jì)德所言:“我因鞭笞自己而感到喜悅,喜悅自己的無處逃避——其中有莫大的驕傲,在身處罪惡時。”[3]于是,太宰治借助神的懲罰而獲得了鞭笞自己的喜悅。但鞭笞自己的極限無疑是自殺——盡管太宰治深諳這一點(diǎn),卻依舊勇敢地向自虐尋求文學(xué)的據(jù)點(diǎn)。他的很多作品都可以稱為請求神懲罰的結(jié)果。如果失去了神的懲罰而相信神的恩寵,太宰治將作為一個常人成為教徒,從而可以得到心靈的解放而免受自我意識分裂的痛苦,但與此同時,也將失去太宰文學(xué)的本質(zhì)。因?yàn)閷ι竦男叛鲆馕吨鴨渭兊摹捌矶\”,一切行動將由神來賦予,而人也就失去了作為人本身的自我意識和主體價值,成為神的仆從。這勢必威脅到太宰治能否保持作家的主體性。至此,太宰治面臨著文學(xué)家和信徒之間的選擇危機(jī)。但他卻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文學(xué)家的立場,棄絕了神的拯救和日常生活的安定,背負(fù)著十字架,用文學(xué)家的精神來貫穿了自己的一生。“只有信仰基督的贖罪,才會得到神的義。并且,不是依靠自己的功績,而是依靠恩寵得到義的人才會得到實(shí)行基督的戒律的能力。”[4]由此一來,不相信基督之贖罪的太宰治自然不能得到神的義,從而關(guān)閉了自己通往天國的道路。既然不能得到神的義,就自己創(chuàng)造自己的義——“就跟玩撲克牌一樣,一旦把負(fù)的全都收齊了,也就變成了正的。”(《維庸之妻》)面對神的權(quán)威,他建立起了自己的權(quán)威——要是神不懲罰我,我就自己懲罰自己。從某種意義上說,神不啻是他自我懲罰的工具。神被太宰治利用后便遭到了拋棄。可以說,太宰治自始至終貫徹了人本主義,以人的勝利來戰(zhàn)勝了神,從而反過來證實(shí)了神的勝利。無疑,當(dāng)他拒絕了神的拯救時,信仰也就發(fā)生了危機(jī),注定了他自我懲罰的盡頭只能是自殺。
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盡管神暫時統(tǒng)一了太宰治分裂的自我,卻不能填平太宰治與不存在著神的外部世界之間的鴻溝。太宰治因?yàn)樯癫皇亲哌M(jìn)了大眾和現(xiàn)實(shí),反而更加遠(yuǎn)離了現(xiàn)實(shí)的人類。但太宰治活著的目的更主要是在向人類的求愛中通過他人來證實(shí)自己的存在價值,較之神的肯定,他更希求的是人的肯定,甘愿為得到人類的信賴和愛而放棄神的恩寵。所以,他只是借助了神的力量,而不可能在信仰的世界里駐足長留,必然在終極意義上拋棄神而返回人間,即便這是一個不可能獲得“信賴”和“安慰”的冷漠世間。可是,“怎么也不能對人類死心的”的太宰治一旦放眼現(xiàn)實(shí)世界,面對戰(zhàn)后假民主主義的盛行,沙龍思想在文壇上的支配地位,還有戰(zhàn)后的一片廢墟和舊有道德的全面崩潰,他不禁發(fā)出了高度虛無的嘆息:“只是一切都將逝去。”(《人間失格》)“管他是不是人面獸心,我們只要活著就行了。”(《維庸之妻》)于是,他只好用肉體的消亡來結(jié)束內(nèi)心的糾葛。但他不愿平常地死去,而必須得做一次悲壯的犧牲,來維護(hù)并成就自己英雄的聲譽(yù)。面對讓人絕望的現(xiàn)實(shí),又要拯救這個神不存在的人類世界,太宰治只好讓自己成為一個來自人間的神,換言之,像耶穌死在十字架上一樣,為了全人類他要勇敢地死去,靠死亡來最后完善自己,然后再用死亡達(dá)成的永恒、絕對、至美來拯救人類和現(xiàn)實(shí)。因?yàn)樽詺⒂兄鴧^(qū)別于自然死亡和被動死亡的英雄色彩,因此,在他看來,自殺意味著主動拋棄了現(xiàn)實(shí)的相對性而獲得了永恒和絕對。于是,1948年6月13日,太宰治投河自殺,試圖通過死亡來成為人類現(xiàn)代的贖罪者,本世紀(jì)的耶穌。“是嗎?……真是個好孩子。”(《眉山》)“我們所認(rèn)識的阿葉(主人公名),又誠實(shí)又乖巧,要是不喝酒的話,不,即使喝酒……也是一個神一樣的好孩子哪。”(《人間失格》)他留下這些自我主張的美麗希望后絕塵而去,他的死不是面對神,不是通向天國的,而是面對人間的,即希望以死亡來換取人們的承認(rèn)和贊美。不過,太宰治最終也沒能變成耶穌,倒是因其獨(dú)特的文學(xué)作品在日本文學(xué)史上甚至于世界文學(xué)史上占據(jù)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如今,太宰治和夏目漱石、宮澤賢治一樣,是日本讀者閱讀得最多的作家之一,甚至成了不少青少年的精神導(dǎo)師。
“永遠(yuǎn)的少年”
太宰治作為文學(xué)家活躍于日本文壇,只有從1933年到1948年的短短15年。太宰治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通常分為前期、中期和后期,分別與日本左翼運(yùn)動遭到鎮(zhèn)壓的戰(zhàn)前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戰(zhàn)后的迷惘時代相對應(yīng)。從空間上看,養(yǎng)育了太宰治的故鄉(xiāng),乃是津輕這樣一個處于日本本州北端的鄉(xiāng)下地區(qū)。盡管太宰治長大成人后移居到了東京的郊外,但除了故鄉(xiāng)津輕和東京之外,他也就只去過伊豆、三島、甲府、新澙、佐渡等區(qū)區(qū)幾個地方。不用說前往海外旅游,就連京都和大阪等關(guān)西地區(qū)也不曾涉足。換言之,太宰治作為一個文學(xué)家,在時間上只短暫地生活在了一個極其特殊而又異常的年代里,而從空間上說,也只是生活在了一個極其有限的狹窄地域里。不用說,這樣一個作家所寫出的作品,成為一種非常偏狹的特殊文學(xué),自有其必然性。
盡管如此,太宰文學(xué)卻具有一種超越了時空的不可思議的普遍性和現(xiàn)代性。閱讀《斜陽》和《人間失格》等作品,不能不感覺到,太宰治所直面的乃是人類,特別是現(xiàn)代人共同面對的普遍課題,描寫了現(xiàn)代社會中出現(xiàn)頻率越來越高的自閉者、叛逆者、邊緣人或多余人的悲劇。比如,就像《人間失格》中的主人公那樣,在現(xiàn)代,一旦試圖富有實(shí)驗(yàn)性地、忠實(shí)于自我地生活下去,就很可能遭到社會的疏遠(yuǎn)和異化,成為“人間失格者”。或許在所有現(xiàn)代人的心中,都或明或暗地存在著一塊懦弱、孤獨(dú)而又渴求著愛的荒地,而這塊荒地卻被太宰治的文字無聲地侵襲,而且無從回避。之所以有無數(shù)的讀者癡迷于太宰文學(xué),無疑是因?yàn)樗麄儼烟字慰醋魇亲约盒撵`秘密的代言人,甚至是具有排他性的青春密友。在太宰治自殺辭世已經(jīng)過去了70多年的今天,太宰文學(xué)迷有增無減,且逐漸跨越了國界。與其說太宰文學(xué)業(yè)已躋身于功成名就的經(jīng)典作品行列,不如說在現(xiàn)代語境里反倒越來越彰顯出歷久彌新的鮮活的現(xiàn)代性。這無疑是太宰治不惜用生命作為賭注,將自己置于實(shí)驗(yàn)臺上以曝露現(xiàn)代人的恥部,追求人類最隱秘的真實(shí)性和人類最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并表現(xiàn)為融獨(dú)特性和普遍性為一體的文字之緣故。
心理學(xué)家榮格認(rèn)為,所有人內(nèi)心的無意識深處都存在著一個“永遠(yuǎn)的少年”原型。所謂“永遠(yuǎn)的少年”,乃是奧維德對希臘少年神伊阿科斯的指稱。既然被稱為“永遠(yuǎn)的少年”,也就意味著可以返老還童,永不成年。在厄琉西斯的秘密儀式上,他又是谷物與再生之神。作為英雄,他試圖急速地上升,但時而又會突然墜落,被吸入作為地母的大地中。于是他又以新的形式再生,重新開始急速上升的過程。借助地母神的力量,他可以不斷重復(fù)死亡與再生的過程,永葆青春。他永遠(yuǎn)不會長大成人,是英雄,是神的兒子,是地母的愛子,又是打破秩序的搗蛋鬼,同時又不可能徹底定型為其中的某一角色。他絕不被習(xí)俗所束縛,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著自己的理想。他們對無意識中閃現(xiàn)的靈光,總是保持著開放的心靈,卻缺乏加以現(xiàn)實(shí)化的能力。所以,常常被認(rèn)為是心理學(xué)上的退化。但榮格認(rèn)為,退化并不總是一種病態(tài),而是心靈創(chuàng)造性過程的必需之物。依靠退化,自我得以與無意識相接觸,由此獲得的,既可能是病態(tài)的或者邪惡的東西,也可能是未來發(fā)展的可能性,或是嶄新生命的萌芽。因此,這種退化很可能是一種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退化。
或許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人們把太宰治文學(xué)稱為永恒的“青春文學(xué)”。我們總是——同時也只可能——從他的作品里找到一個主人公。一個保持了純粹性卻長不大的“永遠(yuǎn)的少年”。即便我們從封閉的自我走向了廣闊的社會,走向了成熟,而不能不向他揮手作別,但這個“永遠(yuǎn)的少年”也總是會在我們內(nèi)心深處喚起一種深深的戰(zhàn)栗和鄉(xiāng)愁般的情愫,讓我們管窺到人性的淵藪,點(diǎn)燃我們潛在的創(chuàng)造激情。這是因?yàn)椋拖窭畎舱f過,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一樣,我們每個人心中也必定潛藏著一個“永遠(yuǎn)的少年”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