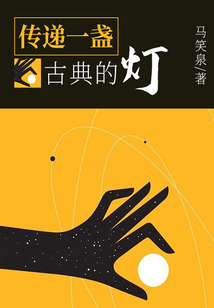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自序
漢語新詩在確立之初,急于撇清與古典詩歌的關(guān)系,臣服于歐美詩歌的腳下。脫下長袍換上西裝的新潮詩人們紛紛以成為“中國的惠特曼”或“中國的濟(jì)慈”而自豪,詩歌上的“破四舊”遠(yuǎn)比小說和散文來得徹底。在這一選擇的深層動機(jī)中是否存在哈羅德·布魯姆所言的“影響的焦慮”暫且不論,單單是作為一種“文學(xué)革命”的簡單粗暴策略,已然導(dǎo)致了新詩先天的營養(yǎng)不良和后天的聚訟紛紜。他國詩人想必對中國同行的這一集體選擇感到不可理解甚至不無鄙視。很難想象博爾赫斯否定荷馬,或者谷川俊太郎無視松尾芭蕉。盡管20世紀(jì)下半葉少數(shù)漢語詩人們已經(jīng)意識到了這一重大弊病,頻頻在詩中向古代詩人致敬,但長期浸淫于西方翻譯詩歌中所造成的“路徑依賴”,決定了這種致敬姿態(tài)可嘉但實(shí)效甚微。有的詩人喪失了直承本國古典詩歌的能力,甚至公開宣告要依靠龐德去認(rèn)識唐詩。從屈原到龔自珍,這兩千年中大批優(yōu)秀詩人共同積攢的輝煌遺產(chǎn),如果無力在轉(zhuǎn)化中繼承和發(fā)揚(yáng),那將是漢語詩人的集體恥辱,而事實(shí)上,這一恥辱已背負(fù)多年。但有人還不以為恥,反而沾沾自喜,滿足于在世界詩壇中做一個(gè)亦步亦趨的二等公民。
我無意倡導(dǎo)一種詩歌上的東方中心主義,正如我反對歐美中心主義一樣。對于任何一個(gè)國家的詩人來說,在繼承傳統(tǒng)、立足本土的基礎(chǔ)上兼收并蓄,永遠(yuǎn)是創(chuàng)作的正道和大道。多年來我同時(shí)創(chuàng)作新詩和舊體詩,并未有違和之感。因?yàn)槲覄?chuàng)作的是漢語詩歌,體式或有不同,但其精神和語感是一脈相傳的。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威斯坦·休·奧登能自如運(yùn)用從古至今的各種英語詩體寫作。東西方這兩位大詩人對傳統(tǒng)的態(tài)度和由此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永遠(yuǎn)是我所認(rèn)同和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