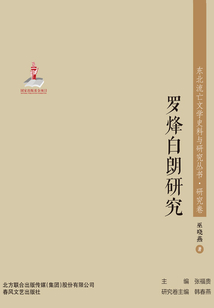
東北流亡文學史料與研究叢書·羅烽白朗研究
最新章節
- 第12章 注釋
- 第11章 羅烽作品中的精神意識研究
- 第10章 東北作家群中的羅烽
- 第9章 羅烽短篇小說創作研究
- 第8章 魯迅鄉土書寫與知識分子精神的雙重延續——羅烽小說創作研究
- 第7章 以女性寫作群體為參照的白朗創作研究
第1章 羅烽白朗創作小傳
上編 創作與研究綜述
一、靡不有初
(一)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羅烽創作經歷
羅烽,原名傅乃琦,1909年12月13日出生于遼寧省沈陽市郊區蘇家屯。家中的生計最初是靠他的父母替人糊裱布錢包、洋火盒,給裁縫店縫皮子、鎖扣眼……勉強維持。羅烽作為家中獨子,很自然地承擔了相當一部分家務,他自己也曾說“小孩子的天職就是玩耍,但母親絕對禁止我和街坊的孩子們胡鬧,母親訓練我充當家庭的小勤務、打掃衛生、跑街,除了不挑水,什么活都幫母親做”[1]。從小生活的環境使得羅烽對生存的苦難有了直觀的認識,而家庭的束縛同時也催發出他內心隱藏著的反叛與浪漫的英雄情結。他有時會違背母親的要求,去尋找一點小孩子的快樂。但是這種行為一旦被發現,隨之而來的便是嚴厲的懲罰。
“碰上六姨在,不但不拉著,還會幫助母親一起打。母親是恨鐵不成鋼啊!”[2]盡管后來的羅烽能夠明了母親的良苦用心,但這給當時的他無疑更增添了想要擺脫束縛與壓抑的渴望。這種感覺在羅烽六七歲進入私塾以后更加強烈。他不愿整天和一個糟老頭讀著老舊的四書五經,又不愿逃學,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囚禁綁縛。而此時的他所能想出的最好的宣泄方式莫過于參加征服“敵人”的“軍隊”。羅烽在孩子們的戰爭游戲中的表現極為英勇無畏,“他們的戰場是在大西關和小南關交界處的風雨臺。他們使用的武器是彈弓、袖箭、石塊和棍棒等。在數次的鏖戰中表現了他的勇敢善戰,負傷流血在所不顧”[3]。在這種游戲里羅烽的叛逆得到了宣泄,同時又收獲了玩伴的敬佩,但這是大人們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而羅烽本人在家庭環境改善,步入小學后也變得斯文而靦腆。
這一階段的情感在羅烽1936年的短篇小說《最后的一次試驗》中得到了反映。這篇作品講述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拾荒孩子阿龍在生活面前不斷探尋出路的故事。他的腦袋里是“一座都市的倉庫”,里面儲藏著他美好的幻想。他與周圍的同齡人始終格格不入,他想的是如何學好,有出息。雖然阿龍的嘗試屢屢碰壁并最終轉向認為錢才是真正重要的,且為此失去了性命,但羅烽依舊在小說中這樣評價他:“這孩子是一個傷感家,他有熱情。”[4]“他那個進取的精神,并不因屢次失敗而至于心灰意餒。這孩子可以說是知情達理的創業家,不,冒險家,他不怎樣怕失敗,他怕的卻是失敗以后想不出新的計劃。”[5]除卻反映底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外,在對主人公的描寫中,羅烽可以說是傾注了年少時自己的內心情感和對某種性格品質的不懈追求,即浪漫的英雄主義,對改變現狀的渴望以及不怕失敗、勇于探索的精神。
1926年羅烽初中畢業,在初中的所見所聞讓他清楚地認識到軍閥的殘暴不仁與官僚的腐敗無為。由于家庭再次敗落,無力支持其深造,羅烽不得不尋找謀生的道路。他本人十分抗拒擔任訥河縣縣長幕僚的生活,于1928年年初只身前往哈爾濱。在呼海鐵路傳習所的學習中,羅烽結識了三位重要的朋友。其中中共地下黨員胡起吸收他加入讀書會,介紹他閱讀《茵夢湖》《少年維特之煩惱》《苦悶的象征》,后又介紹他讀蔣光慈的《鴨綠江上》《紀念碑》,魯迅的雜文和柔石的《二月》等,影響了羅烽今后文學創作的方向以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兼備的藝術風格的形成。
1929年是羅烽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年,他于2月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3月他結束傳習所的學習進入實習階段,在實習過程中同勞動者相處堅定了他的政治信仰。他開始利用詩的形式詛咒黑暗、贊美光明,并用象征的表現方法預見未來大同世界的喜悅。這些詩以“洛虹”為筆名發表在哈爾濱《晨光報》副刊《江邊》上,“洛虹”的寓意有“樂紅”之意,羅烽的精神信仰成為他文學創作的指引與土壤,他的情感與理想也有了具體的歸宿。入黨后,羅烽擔任中共呼海鐵路特別支部宣傳委員。在哈爾濱淪陷前后,他一邊掩護黨的力量,幫助黨團結進步力量,一邊幫助愛國將領打擊日本侵略者,發動文藝運動對抗南滿漢奸文藝。他與妻子白朗,以及蕭紅、蕭軍、舒群和金劍嘯等人一起開辟了《夜哨》《文藝》以及“星星劇團”等文藝陣地。在《夜哨》的創刊號上,羅烽以筆名“洛虹”發表諷刺獨幕劇《兩個陣營的對峙》,文中借鐵路工人之口憤怒地喊出:“起來,全世界的奴隸,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羅烽還發表了小說和詩歌等。短篇小說《口供》,以淪陷后的哈爾濱為背景,在短短三千字中,揭露了日偽警察局局長以抓捕嫌疑犯為名,夜闖民宅,強行帶走民女,深夜輪奸少婦的荒淫暴行。詩歌《從黑暗中鑒別你的路吧!》和《說什么勝似天堂》揭露了罪惡統治的本質,喚醒人民的斗爭意識。“憑自己的力量,憑大家的力量,一定能把地獄變成天堂!”然而就在羅烽的反滿抗日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日偽白色恐怖加劇的1934年6月,羅烽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獄,酷刑遺留下來的身心創傷幾乎伴隨其一生。但令他無憾的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氣節清白并未因此受到損傷。
(二)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白朗的創作經歷
白朗,原名劉東蘭,1912年8月2日出生于沈陽。她與羅烽是姨表兄妹,他們的母親是姐妹,白朗的母親排行老三,羅烽的母親排行老四。白朗的童年頗為不幸,父親因病離世,母親受不住打擊而精神失常。生活的黑暗與扭曲以最觸手可及的方式在年幼的白朗心中留下印痕,但也鑄就了她堅韌不屈的性格。然而白朗同羅烽之間青梅竹馬的童年時光構成了白朗許多天真歡樂的回憶。那時白朗像假小子,但頗為崇拜表哥,佩服表哥點子多,又精通一切玩技。只要表哥來,她便前后院子跟著。童年時的玩鬧拌嘴成為二人甜蜜的回憶。后來白朗就讀于黑龍江省立第一女子師范,被自己的母親許給了表哥羅烽。這時白朗已經顯示出自己獨特的個性,爽朗、外向、品學兼優,在數學方面尤為突出,常是班級考試中的第一名。縝密的邏輯思維使后來白朗報告文學與戰地文學的創作擁有了不同于一般女性作家的大局觀和條理性。
白朗于1929年秋與表哥羅烽結為伉儷。然而新婚的甜蜜尚未退去,白朗便發現自己丈夫的異樣,在她的日記體報告文學《獄外集》中是這樣描述的:“……最使我莫解的卻是他那近乎古怪服裝的更換。勃一向是不修邊幅的,他經常遞換穿著那兩套不花錢的嗶嘰制服,即使參加什么宴會,他也不肯穿一件稍微講究點的衣服,朋友們奚落他,他自己也不覺得寒酸……可是他卻變了,每當晚間走出去的時候,總要換上一件衣服。制服、西裝、便衣,輪流在身上穿上脫下。”[6]女性的自尊、女人的嫉妒都讓白朗忍無可忍,她鬧騰著要自立謀事,甚至要效仿娜拉一樣出走。可是當她將丈夫偷偷藏起的“情書”搶過閱讀時,“我興奮,興奮得完全像一個拾得珍寶的孩子,我用責備的口氣問勃:‘這樣好的東西,為什么不早給我看?’”[7]羅烽成為白朗思想蝶變的引路人。1931年“九一八”之后,經他介紹,白朗加入了“反日同盟會”,她如同鳳凰涅槃一樣獲得了新生。
哈爾濱淪陷后,為了加強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楊靖宇指令羅烽出版“反日總會”會報《民眾報》。已參加反日同盟會的白朗成為丈夫的得力幫手,她用娟秀工整的蠅頭小楷刻蠟版。夫妻二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興奮而緊張地翻印黨內文件、傳單和《民眾報》。遇到經費接濟不上的情況,夫妻二人會自己墊付。1933年《夜哨》創刊后,白朗開始正式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短篇小說《只是一條路》寫一個未滿十四歲的孩子王家棟為生活所迫給人當聽差,在社會上受盡欺辱的故事。白朗從一開始就展現了對底層勞動人民的關注,并隨著不同的時代背景增添豐富主題的內涵。這一時期通過描寫底層人民的悲慘生活揭露淪陷時期社會的黑暗,表達了對光明的渴望。緊隨其后的短篇小說《叛逆的兒子》講述了一個同情受剝削受壓迫的勞苦大眾,憤而反抗自己封建腐朽家庭的男青年的故事。這也是白朗思想情感的生動反映,她接受了新的進步思想,致力于與一切封建的剝削的壓迫的事物進行決裂、反抗,頗有五四精神的韻味,但同樣未能給“娜拉出走之后應該如何”這一關鍵問題以回答。
為另外開辟宣傳陣地,白朗在《國際協報》擔任編輯時,將《家庭》和《婦女》兩個周刊合并,創刊《文藝》,撰稿人幾乎是《夜哨》的原班人馬。為避免引起敵人注意經常改換筆名。白朗的筆名有劉莉、弋白、莉、杜微等,羅烽的筆名有洛虹、彭勃、羅迅、克寧、kn等。她在《文藝》上發表了一系列小說作品。其中短篇小說《驚悚的光圈》,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十年來的小說界——滿洲新文學大系小說上卷導言》收獲評價:“寫作最勤快的是弋白,她的《驚悚的光圈》較比《夜哨》上的《叛逆的兒子》,無論在結構與技巧上都有相當的進步。”正當白朗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道路上不斷前進時,生活再次挑戰白朗的意志。羅烽因叛徒告密被捕,白朗除卻要以金錢活動運作,承受報社同事一些不懷好意的言論,還要時刻擔心羅烽的安危。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白朗依舊堅持出刊《文藝》到年底。這些足以證明白朗已經從一個天真的知識青年逐漸成長為一位可以獨當一面的革命戰士。
二、邦之彥兮
(一)20世紀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期羅烽創作經歷
1935年7月15日,羅烽與妻子白朗潛赴上海投奔蕭軍與蕭紅。由于生活窘迫,陷入了“一件毛衣常常典當幾次”的境地。隨后更為逼迫人的是,投出去的文章無人肯要,典當一空,借貸無門。但這并未使羅烽消沉下去,相反他積極聯絡組織關系,努力克服生活上的困難。事實上如果只為了維持生計,羅烽憑借鐵路供職七年的履歷以及東北流亡交通界的資格到南京政府交通部報到登記,即刻就可得到職業。這是國民黨對淪陷區從事鐵路、郵政的逃亡人員采取的特殊措施,并且還有東北鐵路逃出的舊同寅在此擔任重要職務。但羅烽認為這些出路都有礙于他的政治前途,所以一次次地拒絕、放棄。
天無絕人之路,1935年9月至10月,羅烽經人介紹認識了左翼作家聯盟負責人周揚。經過一番程序于11月正式接上黨的關系并加入左聯。重新與黨組織取得聯系,使得羅烽的心情明亮起來。他這時的心情在11月寫就的詩歌《他是貪婪地活著》中得到了表述,“還要將快樂造成不朽”,亦表達了羅烽高漲的革命熱情與崇高的思想覺悟,“只要是有生命的原子,在動的社會里有用,在生的群眾里有功,悄悄地死去也行”。而羅烽一生也真切地踐行了詩中的語句。在同一時期,他與妻子白朗開始在進步文藝期刊《海燕》《夜鶯》《作家》《光明》上發表詩歌、散文和小說。
羅烽的創作主張早在他替妻子為《文藝》副刊撰寫的前言中可見一斑:“文學不能規定目的,因為有目的的文學,常是失卻了文學的價值,但文學學者他不能只埋首在書齋里構思、設想,起碼應當推開窗子、睜開他的睡眼,和現實親切一下。那樣,可以明了人類在廣大的宇宙間怎樣地生存著,更可以聽見弱者的低吟是怎樣在垃圾堆上和陰溝打滾呢!”[8]羅烽的文學創作是與他的革命斗爭密不可分的,他是由革命走向文學。文學的靈感與動力根植于他信仰的精神土壤,而他的戰斗意識又源于強烈的關注現實精神。在黑土地上獨特的生活際遇使他較早地觸摸到了中國社會傷痕累累的一面,所以他的作品中又帶有深厚的人文關懷與溫情意識。
他在1936年發表的《呼蘭河邊》《獄》較為鮮明地貫徹了他的理念。《呼蘭河邊》講述了“我”在呼蘭河橋防守所見證的一個手無寸鐵的牧童的悲劇。敵軍懷疑牧童是抗日義勇軍將其逮捕,最后將牧童的小牛吃掉并殘忍地殺害了他。他的尸骨與牛的骨頭被拋在草叢中,而他的母親親眼看見了這一場景。“我”在文中時時流露出對牧童、小牛以及村婦的同情,那是人民苦難的縮影,不禁發出嘆息:“中國人哪,中國人哪,受難的中國人哪!”這種同情隱隱地鼓勵著受苦的人民進行反抗。當牧童的母親求救無門時崩潰地訴說:“我沒有炸彈,我沒有手槍!”羅烽實際上已經指出了中國人民反抗的道路。而在《獄》中描寫的是在獄中受到壓迫和不公待遇的人民,這和羅烽1934年被捕后的獄中經歷是關聯的。文中同時又暗示著未來的愛國志士的不懈斗爭。“……而且,在窗前伸出一叢搖曳著的丁香樹梢,它,告訴我,這塊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東西,并沒有死滅!雖然,那葉子已經半黃了。”
羅烽同年的短篇小說《第七個坑》承襲著揭露黑暗、鼓勵反抗的主題,被譯成英文在《國際文學》上轉載,王瑤評價它是“發表后得到過好評的”[9]作品。小說主要講述了皮鞋匠耿大被日本侵略者抓去挖坑活埋同胞。在一連挖了六個坑以后,敵人又逼著他活埋自己。耿大終于覺醒,反抗敵人,第七個坑派上了真正的用處。作品展現了對社會現實的清醒洞察,即不反抗則死亡。周立波評價這篇小說:“……他在那篇上的成功不是他關于敵人的殘忍的描寫,而是他描寫皮鞋匠耿大的恐怖心理的很少的幾筆,和他反映‘九一八’以后的沈陽的亂離的情況。”[10]
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打響。羅烽負責中國文藝家協會募捐辦公室的工作,同時擔任文藝家戰時服務團的宣傳部部長。八一三事變后上海局勢空前緊張,文藝界人士開始撤離。羅烽被迫離滬,計劃由南京北赴山西戰場。后大同失守,北上交通不通,羅烽毅然奔赴武漢。與沙汀失去聯系使得羅烽失掉了黨的關系。在武漢時期,羅烽與麗尼創辦的刊物《哨崗》被封,他托柯仲平給周揚帶口信,要求前往延安。后羅烽輾轉于西安、臨汾,最終回到武漢。其間兩次試圖與黨取得聯系均未能成功。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羅烽、白朗同為發起人之一,羅烽被選為理事。武漢戰局吃緊,羅烽轉移至重慶。在武漢的近一年中,羅烽創作了中篇小說集《莫云與韓爾謨少尉》,在《戰地》連載長篇小說《滿洲的囚徒》。抵渝后羅烽、白朗又同戰地訪問團奔赴前線,1940年羅烽擔任《文學月報》主編。這一年羅烽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糧食》,發表近百首《戰地詩草》,長詩集《碑》、雜文集《蒺藜集》在桂林出版,寫完《滿洲的囚徒》第一部。
羅烽的小說以反映時代的真實矛盾與殘酷為主題,由此產生了廣泛的題材選擇和對人物多重復雜性的揭示。有喪失民族氣節為偽警察廳打造腳鐐的鐵匠沈萬清(《生意最好的時候》);安分守己對時局漠不關心但最終被趕入殖民地屠宰場的左醫生(《左醫生之死》);為了避免孫子淪為日本侵略者走狗而在給孫子的蛋糕中放入砒霜的爺爺(《三百零七個和一個》)。中篇小說《歸來》中的知識青年黎典和同伴白騫共同加入抗日義勇軍,然而臆想中的詩意并不存在。沒有整齊劃一的服裝,威風先進的武器,他對這支隊伍的戰斗力產生了懷疑。同伴的犧牲更加深了他的孤獨與惶恐,他試圖逃回舊生活,等待他的卻是一個生死難測的明天。這些人物與命運統統指向一個內涵,即必須反抗,唯有這樣才能找到出路。
在藝術特色上,羅烽善于用對話以及人物情感的自然流露來推動情節發展。在刻畫人物心理時善于將景語與情語兩結合,環境成為外化的人物內心情感。羅烽運用詩化的語言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以增強情感。這與他早年的詩歌創作是有關的,與白朗的創作手法也是有所區別的。很多篇目結尾處的處理手法頗有特色:或是結束于富有象征意味的景色描繪中,從而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白朗在這一點上頗受羅烽影響;或是用饒有意味的敘中藏議收束動情鋪展的故事,給人思想上的啟示;也常筆鋒陡轉,于出人意料處戛然而止,讓讀者在喟嘆之余細致思索。
(二)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期白朗創作經歷
1935年,羅烽、白朗在滬生活已經陷入窘迫,所幸白朗在《申報》謀得一份打字員的工作。但羅烽、白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只能共吃一份客飯,勉強度日。1935年年底,白朗產下一名男嬰。孩子未滿周歲時患腦膜炎,因無錢醫治死亡,這已是白朗失去的第五個孩子。1936年,白朗的作品在進步文藝期刊上發表,包括短篇小說《伊瓦魯河畔》《輪下》。這一時期白朗和羅烽的作品大多以反封建、反侵略、反投降為主。
《伊瓦魯河畔》講述的是日寇統治下偽滿宣撫員在宣傳所謂的“王道樂土”時與村民之間沖突的故事。主要人物賈德和村民對前來演講的宣撫員的鬼話連篇并未相信,反而與之正面對抗。后來義勇軍及時趕到拯救了村民。這個故事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反日寇反偽滿的主題。比如頻繁在文中出現的歌謠:
“滿洲國”旗黃又黃,
一年半載過不長,
東洋虎,
滿洲狼,
一股腦兒見閻王。
在結尾處,象征投降主義的老村長投河自盡,沒有人搭救,他發出怨言或嘆息:“……在他們脈絡里,在他們四周,只有一個單純而不愿休息的而且也不能休息的興奮激蕩著……”賈德又唱起了開篇的歌謠,昭示著敢于反抗必將迎來出路。
《輪下》,一篇帶有報告文學特點的紀實小說,在中國當代紀實文學的創作中具有別開生面的廣度與深度。《輪下》以1932年秋哈爾濱大水災為背景,表現了難民與日偽當局的斗爭。揭示侵略者及其爪牙的殘暴,以及人民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慘烈反抗。其中有難民代表被押入囚車,他的老婆抱著孩子臥在囚車前被活活碾死的悲慘場面。同時這篇小說在藝術處理上頗具匠心,“后來有學者評價她的這篇作品說:‘籠罩著凄楚沉郁的悲劇氣氛,描繪了波瀾壯闊的群眾斗爭場面,并且在描寫時采用電影蒙太奇的結構手法,把人物對話、動作、心理刻畫組合成一組組電影鏡頭,平行交叉,迭復剪輯在一起,使小說文簡流暢,人物個性突出,情節跌宕,節奏明快。’”[11]。這也基本概括了白朗的創作特色。
七七事變后,懷孕六七個月的白朗依舊在戰時服務團工作。8月13日日本飛機在上海“大世界”扔下炸彈,在正在募捐的白朗身邊爆炸。9月5日,羅烽、白朗奉組織命令撤退內地。羅烽預備前往山西前線,于是待產的白朗同羅烽的母親前往武昌投奔親戚。上船時身懷六甲的白朗險些被蜂擁的人群擠下船,幸好被羅烽的母親一把抓住。11月12日白朗產下兒子傅英,而在此之前白朗仍和羅烽緊密配合幫助愛國志士進行革命宣傳。1938年3月,白朗與羅烽同是“文抗”發起人之一。后戰火逼至武漢,白朗先行轉移至重慶。在重慶,白朗克服了內心的種種情感,毅然參與了“文抗”組織的戰地訪問團奔赴前線。白朗內心的掙扎在作品《戰地日記》中表露無遺:“‘到前方去!’我也曾幾次私自下過決心,然而,那新生的孩子,我是怎樣也不忍離棄的……”
戰地訪問團的行程在艱險與歡快交相編織中度過。這段生活在1940年出版的中篇小說集《我們十四個》中得到了生動的描繪。遺憾的是,白朗因為身體原因未能完成前線之行。1940年秋冬兩季,是大后方進步文藝期刊蓬勃發展的時期。這一年里白朗在《大公報》《抗戰文藝》《東北論壇》等發表大量報告文學、散文和評論等。出版中篇小說集《老夫妻》(1940年4月)、散文集《西行散記》(1940年初版、1941年再版)等。同這一時期的羅烽一樣,白朗作品的中心內容以暴露日寇侵占東北的殘酷罪行和人民的英勇反抗為主,鼓勵人民投身于抗戰,贊美大后方人民抗日的高昂熱情,與黨每個階段的政治任務緊密相連。
白朗的作品以反映現實生活為主,對勞動人民的生活給予極大關注。這一主題貫穿白朗的創作,并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豐富,由展示被壓迫者的苦難生活,揭示日寇、偽滿的殘暴統治,贊美勞動人民的英勇反抗,到后來熱情謳歌憑借自身努力為國家做出貢獻、實現自我價值的勞動人民典型。白朗的創作也可以說是一部女性精神成長的自傳。《逃亡日記》以日記體寫一位女青年,反抗舊家庭獨自出走,可她一踏入社會就被“貧困的苦痛和彷徨的迷茫包圍了”;《四年間》的主人公黛珈蔑視舊禮教,一心求學上進,卻困頓于舊式婚姻,她懷著希望去學校任教,而學校的污濁風氣讓她難以忍受,四年間希望與幻滅周而復始;而在《生與死》中傳統了一輩子的老祖母成功踏出了反抗舊社會反抗壓迫的一步;《老夫妻》也是一位以夫為天的傳統女性抗爭成功的故事。再到1949年后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突出女性的刻畫,如《為了幸福的明天》,這些創作也反映了白朗本人思想的不斷進步。
白朗的小說善于以場景的切換來推動情節發展,這與羅烽是有所區別的。通過場景的變換與場景中人物的活動與對話來展現人物復雜的內心,使得文章節奏清晰,文筆簡練。在進行群體刻畫時,白朗運用電影化表現手法,既省筆墨又有較突出的形象特征。然而白朗的一些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刻畫上稍顯單薄,敘述多于描寫,結構顯得線條較粗。這既是受到白朗本人為了配合斗爭未能精細打磨的影響,白朗說“我寫了半輩子東西,全是‘急就章’”(見白瑩《白朗小傳》),也有缺乏此類生活實踐的深入體驗之故。
白朗的景物描寫主要是服務對比手法的一部分,越是激越的場景前越要鋪陳一種寧靜的環境氛圍,然而這種寧靜之中又壓抑著躁動。對比手法在白朗的人物塑造中是較常出現的,主要用于人物轉變中。《老夫妻》里吝嗇的老地主在經歷了和義勇軍一同對抗侵略者以后,臨終前將其悄悄藏起的鈔票全數給了義勇軍。另外,白朗的小說作品,受其散文創作的影響,常將敘述、議論、抒情融為一體。散文化也表現于抒情化,在寫景狀物或指事造形中都伴隨著情感上的抒發。在作品結尾的處理上,白朗頗受羅烽的影響,常于富有象征意味的場景中結束(如《伊瓦魯河畔》《一個奇怪的吻》),或于情節的關鍵處戛然而止(如《生與死》《輪下》)。
三、雨雪其雱
(一)20世紀40年代初期到80年代羅烽的經歷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發生后,羅烽、白朗相繼遷至延安。在重慶期間羅烽除小說、戲劇、長短詩外還發表了五十多篇針砭時弊的雜文,如《便衣漢奸》《論客之類》《盛意可感》。這些雜文不僅批判國民黨的動搖性和失敗情緒,還暴露了國民黨政治態度的逆轉。可以說羅烽無論身在何處,他的作品都是為革命戰爭而服務的,每一天都未曾忘記自己的革命職責,時時注意維護自身的政治純潔性。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虔誠的革命戰士卻遭受了他最不應承受的折辱。
在1958年關于“右派分子”羅烽的政治結論中,所謂的反黨罪行無外乎是:反右以后積極向丁玲獻策,提示丁玲在發言時注意策略,并勸丁玲趕寫反右派的文章;反對劉芝明,反對周揚,反領導即為反黨;撰寫文章誹謗黨和革命。事實上這些罪狀皆屬于無中生有、歪曲事實、斷章取義的產物。
關于丁玲一事,丁玲申訴自己對1955年處理的意見,而羅烽作為作家支部書記出于組織角度和丁玲談了幾次話。在1957年第一次黨組擴大會召開前,羅烽曾對丁玲做思想工作,勸告她在會上冷靜地聽取大家的批評,不要有情緒,不要給別人戴帽子。接著開展反右派斗爭,羅烽再次勸告丁玲,拋開個人恩怨,站在黨的立場維護黨的利益,積極寫文章投入反右派斗爭。這便是第一條罪行的由來。
關于劉芝明的問題,實際上是對劉芝明的領導作風及其落實毛主席文藝方針提出的意見。1953年3月初,按照東北局宣傳部的“認真總結東北三年來的文學工作的指示,東北文學工作者協會的全體同志即著手討論”[12]。作協全體分工進行《三年來東北文學創作工作總結》報告的撰寫,在討論的過程中關于劉芝明的作風、干部使用問題,作協全體又整理出了一份附件,供東宣部和劉芝明參考。所有的材料都是民主討論、共同定稿、公開上報,并且工作總結中關于劉芝明領導東北文藝工作犯有政策性錯誤的意見來自蔡天心而非羅烽、白朗、舒群,但后來卻被作為罪證強加于三人。1949年羅烽為了彌補劉芝明“總報告”初稿對毛主席文藝方針強調不夠的情況,在東北文代會上的開幕詞中著重強調了毛主席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針。但東北作協執行主席草明在宣讀時隨意發表了極為不負責任的言論,當晚文協同志對其進行指責,卻被演繹為舒、羅、白的秘密反黨會議。
關于周揚的問題在于,羅、舒、白等五人署名寫文章反對周揚。1941年7月17、18、19日三天,延安《解放日報》副刊連載周揚《文學與生活漫談》的文章,蕭軍認為此文章是針對黨外作家的,羅烽、艾青、白朗則是對周揚文章中有些問題的提法和影射攻訐的語調有不同意見。8月1日,白朗、舒群、艾青、羅烽、蕭軍五人署名的《〈文學與生活漫談〉讀后漫談集錄并商榷于周揚同志》在《文藝月報》上連載。發表后周揚本人沒有任何反應,也沒有人說這是反對周揚、反對黨。周揚的文章不過是“漫談”而已,并非黨中央紅頭文件,五人所做的也不過是以漫談的形式對其漫談進行補充,后來卻被認為是反黨、反周揚。
至于撰寫反動文章,所謂的反黨文章《太陽的黑點》是從五人署名的文章中的第三個小標題中杜撰而來。由于篇幅所限不將有關部分原文進行展示,而在這一部分中主要論述的卻是如何對“黑點”進行有效的處置,同時表示“黑點”不會影響人們對光明的信仰,光明也將更為純粹。羅烽的另一“反黨”文章《還是雜文的時代》,是羅烽1942年針對延安某些人私下鼓吹的魯迅雜文的文體形式可以在延安廢除了的論調撰寫的。是從文體之用的角度出發的,認為雜文作為一種文體將長期存在,“經年陰濕的角落還是會找到,而且從那里發現些垃圾之類的寶物”。
因為這些所謂的罪證,羅烽與白朗經歷了長達十余年的不公對待。然而晚年的羅烽雖身心已飽受摧折,但仍記掛著當年同自己一道被捕入獄的同志是否洗清冤屈。羅烽一生的追求在于真理,在于無愧于心。這也是支撐其創作的風骨。
(二)20世紀40年代初期到80年代白朗的創作經歷
抵達延安后,白朗先后于1942年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并擔任《解放日報》副刊文藝編輯,1945年在中央黨校入黨,1946年任黨報《東北日報》副刊部部長、東北文藝協會出版部副部長和《東北文藝》副主編。此時期,白朗小說作品取材于土改斗爭和人民軍隊的戰地生活,描繪革命斗爭的歷史場景,歌頌戰斗英雄與農民翻身運動。風格明快、平易。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牛四的故事》、短篇小說《不朽的英雄》《死角》等。
1949年后白朗進入創作的黃金時期。她以工廠和戰爭生活為題材,滿腔熱情地贊頌伴隨著社會主義建設涌現的英雄人物和一代社會主義新人,禮贊抗美援朝的志愿軍戰士。同時塑造了成長型女主人公邵玉梅的形象,她由受盡封建思想壓迫和日本侵略者欺凌的無助者慢慢轉變為投身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富有覺悟的女性形象(中篇小說《為了幸福的明天》)。還有長篇小說《在軌道上前進》。白朗的創作風格逐漸趨于熱烈、灑脫。
同時期白朗在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她代表蔡暢、鄧穎超赴索非亞參加國際婦聯執委會工作。1951年參加國際婦聯組織的“對美李匪軍在朝鮮的罪行調查團”,目睹駭人聽聞的“美李”暴行,并執筆起草《告全世界人民書》散發世界各地。1952年2月她隨中國作家代表團去朝鮮戰地訪問,歸國不久又隨“赴朝慰問團”去朝鮮。9月,奉周總理之命陪英國工黨議員費爾頓夫人再赴朝鮮。1952年冬,出席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1953年6月,去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婦女大會,會后應芬蘭邀請到赫爾辛基參加芬蘭婦女文化日。7月參加板門店停戰協定簽字儀式。1956年出席在新德里召開的亞非作家代表大會。
然而正當白朗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的時候,從天而降的污水讓今后的愿景統統化為泡影。1958年,白朗的“反黨罪狀”中,在與丁玲的關系上,認為白朗在鄧穎超同志面前做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的申訴,為丁玲的“反黨罪行”辯護。事實上,8月白朗應全國婦聯建議在北戴河寫《何香凝傳》。由于聽不懂廣東話,恰逢周總理和夫人鄧穎超也在此地,白朗便前去拜訪了解有關何先生的情況。談話間,鄧穎超主動問起關于丁玲的情況,白朗表示丁玲反黨的可能性并不大,同時不同意丁玲提倡“一本書主義”就是反黨。
在反對劉芝明反周揚即反黨的問題上,據當年參加撰寫總結報告的人說:“當時東北作協的整個氣氛——對劉芝明的文藝思想和領導作風的不滿是一致的。”[13]白朗自己也說:“會議結束以后,不但沒人指出我有反黨錯誤和小圈子情緒,作協黨內反而根據東宣部的意見把我選為副支書。當我調離東北時還給我做了一個非常好的鑒定。”[14]關于周揚的情況在介紹羅烽時已經講過,此處不再贅述。
因為這些莫須有的罪名,羅烽與白朗被清除出黨,劃為右派,撤銷一切榮譽與職務,下放到阜新礦區勞動改造。對于黨的最高處分,夫妻二人在思想上是難以接受的,而礦區的勞作也極大地摧殘了兩個人的身體。1959年7月、1960年3月中旬、1961年7月的匯報中白朗敞開心扉,請求組織的指導與監督,爭取盡快回到黨的懷抱。1961年初冬二人摘去了右派帽子。為了彌補失掉的時間,他們在短時間內寫出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白朗創作了短篇小說《少織了一朵大紅花》《溫泉》《警鐘》等,羅烽與青年學者楊烜寫了長篇報告文學《列車在前進》,還寫了短篇小說《雪天》《第九盞紅燈》以及四幕話劇《春風得意》等等。
隨后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文革”再度使二人陷入雪上加霜的境地。1968年,羅烽、白朗被送至遼西盤錦五七干校。在盤錦,白朗的精神崩潰了,她摔碎鋼筆,發誓從此不寫一個字!而她于1970年7月在精神極度錯亂下寫了長達一萬五千字的《退休(職)申請書》。這封浸透了白朗血淚的萬言書才是她真正的絕筆。
長達十年的時間里,羅烽與白朗在極度困苦不公的境地里不離不棄。一如曾經經受的諸多磨難未能將二人擊倒一樣,1979年二人最終迎來了平反與恢復名譽。

